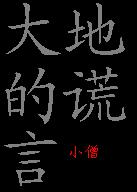鲤·谎言-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玛丽莲:你瞎编的。你就逗我玩儿吧。
卡波特:我发誓。决不忽悠你。(沉默;但我看得出来,她上钩了,再让我点根香烟……)唔,事情发生时,我才十八岁。十九岁吧。还在战时。1943年的冬天。卡罗尔?马库斯为好朋友葛洛利亚?范德比特办了场派对,那时候她没准儿已是卡罗尔?萨洛扬了。晚会就在她妈妈的公寓里开,公园大道。盛大的派对啊。大约来了五十人。半夜时分,埃罗?弗林带着密友大驾光临,那是个虚头巴脑的花花公子,叫弗雷德?麦克沃伊。他俩都喝得醉醺醺的。总之,埃罗开始和我套词儿,他很聪明,我们都说得对方哈哈大笑,然后,他突然说想去摩洛哥俱乐部,还问我想不想跟他、还有麦克沃伊一起去。我说好啊,可是麦克沃伊不想走,不想甩下派对上那些初进社交界的小妞儿,结果,到最后只有我和埃罗走了。但是,我们没去摩洛哥俱乐部。我们拦了车出租车,开到了格拉梅西公园,我在那儿有个单间小公寓。他一直待到早上再走。
玛丽莲:你觉得该评几分?十分制。
卡波特:老实说,那人要不是埃罗?弗林,我大概都记不起来这事儿了。
玛丽莲:这根本算不上一个故事。根本配不上我的事儿。你不能不择手段啊。
卡波特:侍应生,我们的香槟呢?我们都快渴死啦。
玛丽莲:而且你也没说出什么新鲜事儿啊,这不能算。我一直知道埃罗那档子事儿啊。我有个男按摩师,说起来,他还算是我的好姐妹呢,他也是狄龙?鲍尔的按摩师,他把狄龙和埃罗的私房事儿都跟我说啦。不行,你得再说个像样的。
卡波特:吃亏买卖你也得硬上啊。
玛丽莲:我还等着呢。来吧,说说你最好的那次。顺着刚才的话题。
卡波特:最好的?最难忘的?该轮到你先说吧。
玛丽莲:还说我硬上吃亏买卖!哈!(吞下一大口香槟)乔不算差。能达到全垒打水准。要是光看他这一点的吧,我们还不至于离婚。不过,我还爱着他。他很真。
卡波特:老公都不算数的。这场游戏里不能算。
玛丽莲(咬起指头来;真的在动脑筋):好吧,我遇到了一个男人,他好像和盖里?库伯沾点亲。是个股票经纪人,样子嘛,没什么看头——六十五岁,带着厚厚的眼镜片。厚得跟水母似的。我说不上到底像什么,但是——
◎美丽的女孩儿(7)
卡波特:你可以打住了。我已经从别的姑娘们那儿听过他的事儿了。那位老剑客挺能四处转悠的。他叫保罗?谢尔德,是洛基?库伯的继父。他应该挺了不起的。
玛丽莲:他是。好吧,聪明的混蛋。该你说了。
卡波特:不玩啦。我没必要再向你爆什么料了。因为,我知道你那戴面具的神秘人是谁了:阿瑟?米勒。(她放低墨镜:哦,哥们啊,什么叫目光能杀人,这就是,哇哦!)你一说他是个作家,我就猜到了。
玛丽莲(结结巴巴的):可是,怎么可能?我是说,没有人……我的意思是,几乎没有外人……
卡波特:至少三年、大概四年前,欧文?德鲁特曼——
玛丽莲:欧文什么?
卡波特:德鲁特曼。他是《先驱论坛报》的作者。他跟我说,你正和阿瑟?米勒打得火热。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之前嘛,我太绅士了,所以才没说。
玛丽莲:绅士!你个大混蛋。(又开始结巴了,但墨镜归位了)你根本不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已经结束了。这回是崭新的开始 。这一次不一样,而且——
卡波特:别忘了请我参加婚礼。
玛丽莲:要是你敢张扬,我就杀了你。废了你。我认识几个哥们,他们会很乐意为我效力。
卡波特:这我可一点儿不怀疑。
(终于,侍应生送来了第二瓶酒。)
玛丽莲:叫他拿回去。我不想喝了。我想离开这该死的地方。
卡波特:惹你生气了,很抱歉。
玛丽莲:我没有生气。
(可她就是。我买单的时候,她离开了一会儿,去洗手间了,我真希望手上有本书可以读读:她去洗手间那叫一个漫长喲,就跟大象怀孕似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百无聊赖,我开始琢磨她是在吞兴奋剂还是镇定药。镇定药,毫无疑问。吧台上有张报纸,我就拿起来看;结果是张中文报纸。二十分钟过去后,我决定该去看看情况。说不定她用了致命的剂量,或是割了手腕。我找到了女士洗手间,敲了敲门。她说:“进来。”推门一看,她正对着灯光黯淡下的镜子。我说:“你干嘛呢?”她说,“看她呀。”事实上,她刚才是在涂红宝石色唇膏。并且摘下了阴森森的头巾,梳好了棉花糖一般松软顺滑的秀发。)
玛丽莲:但愿你的钱还够。
卡波特:得看情况。要是你想让我赔偿精神损失的话,买珠宝是不够。
玛丽莲(咯咯笑起来,又回到了好情绪。我决定,不再提阿瑟?米勒了):不用。够付出租车钱就行,一长段路。
卡波特:我们这要是去哪儿——好莱坞?
玛丽莲:该死的,当然不是。一个我喜欢的地方。到了你就知道了。
(我不用等很久,因为我们刚招到出租车,我就听到她让司机开到南码头街,不禁心想:那不就是搭渡轮去斯塔顿岛的地方吗?继而我又猜想:她借着酒劲吞了药,现在准是HIGH过头了。)
卡波特:但愿我们不是去坐船远航。我身边没带晕船药。
玛丽莲(开心地笑个不停):就去看看码头而已。
卡波特:我可以问问为什么吗?
玛丽莲:我喜欢那儿。感觉像是在外国,而且,我还可以喂海鸥。
卡波特:用什么去喂?你什么也没有,没法喂。
玛丽莲:有,我带了。我的手袋里装满了幸运饼干。是从那间餐馆里偷出来的。
卡波特(取笑她):啊——呀呀。你猫在厕所里的时候,我还拆了一个看呢。里面的字条上只写了一个下流的笑话。
◎美丽的女孩儿(8)
玛丽莲:天呀。黄色笑话幸运饼干?
卡波特:我肯定海鸥不会介意的。
(我们要穿过鲍厄里。那地方尽是小当铺、卖血站、五毛钱一张帆布铺的宿舍、一美元一天的小旅店,还有白人酒吧,黑人酒吧,到处都是流浪汉,年轻的,早就不年轻的,老得掉渣的,有蜷缩在马路牙子上的,也有蜷缩在碎玻璃渣和呕吐物里的,有歪靠在门廊上的,也有像企鹅一样挤在街角的。等一个红灯时,有个鼻头发紫、衣衫褴褛的人歪歪扭扭地凑上来,颤巍巍的一只手里抓了块破烂的湿布,抹起我们的车窗玻璃来。我们的司机拉开嗓门爆出一连串意大利语脏话赶他走。)
玛丽莲: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
卡波特:他擦玻璃,想挣我们的小费。
玛丽莲(用手袋遮住脸):太恐怖了!我受不了。给他点什么。快给啊。求你了!
(可是,出租车加大油门往前冲了,差点儿把老醉鬼撞倒。玛丽莲哭喊起来。)
我恶心。
卡波特:你想回家吗?
玛丽莲:一切都毁了。
卡波特:我送你回家吧。
玛丽莲:让我缓一下。会好的。
(所以我们沿着南大街继续开,不出所料,看到渡轮停靠在那里,布鲁克林的天际线倒映在水面上,轻轻摇漾,翻飞的海鸥雪白耀眼,越发衬出深蓝色的水平面上白云翩翩,蓬松的云朵像蕾丝花边那么娇嫩——美景很快就舒缓了她的心。)
下车时,我们看到一个男人牵着一条中国狗,显然是在等船的乘客,正往渡船方向走,我们经过他身边时,我身旁的她停下来,拍了拍小狗的脑袋。)
男人(坚定,但不太友好):你不该摸陌生的狗。尤其是中国狗。他们可能会咬你的。
玛丽莲:狗狗从来不咬我。只有人咬我。它叫什么?
男人:傅满洲。
玛丽莲(咯咯笑):哦,跟电影一样。这名字真逗。
男人:你呢?
玛丽莲:我的名字?玛丽莲。
男人:我想也是。我太太肯定不会相信我的。我可以请你签个名吗?
(他掏出一张名片和一支笔;她垫着手袋写道:上帝赐福予您——玛丽莲?梦露。)
玛丽莲:谢谢你。
男人:该我说谢谢你。等下我得拿去办公室秀一下。
(我们继续朝码头边走,听着水波拍岸。)
玛丽莲:以前,我老问大明星要签名。现在有时也会。去年在查森饭店,克拉克?盖博坐在我旁边,我就请他签在餐巾纸上。
(她靠在泊船的拴柱旁,身影定格,如同加拉提亚 眺望着欲加征服的远方。微风吹拂她的秀发,她侧头看我,仿佛被轻风吹动,轻灵灵的,无忧无虑。)
卡波特:那么,我们何时喂鸟呀?我也饿了。太晚了,我们连午餐都没吃。
玛丽莲:记得吗,我问过你,要是有人问你我什么样,问你玛丽莲?梦露的真人到底什么样,你该怎么说?(夹杂着奚落、嘲弄、也乃至热诚的语气,看来,她想听到坦率的回答)我敢打赌,你会跟他们说,我是个胖傻妞儿。香蕉水果船。
卡波特:当然。不过,我也会说……
(阳光正在消隐。她仿佛也随着蓝天白云转入暗淡之中。我想提高嗓门,压过海鸥鸣嚣,大声回答她:玛丽莲!玛丽莲,为什么一切非得落到这个地步?为什么生活非得他妈的沦落成这样?)
卡波特:我会说……
玛丽莲:我听不见你说什么。
卡波特:我会说,你是个美丽的女孩儿。
◎无人生还
文/鲤编辑部
总是忍不住想象死亡,在心里揣摩很多次,会不会有白光出现,会不会疼痛,会不会漂浮在空气里以后还依然有记忆。这种畏惧感是最强烈的,就好像在灵隐寺的观音殿后面,看到那些雕刻在墙壁上的各路神仙时,再顽劣的心也会立刻产生敬畏感。小说和电影里面最糟糕的结局就是,这个人死了,因为死了便无可挽回,便努力白费,便与这个世界的失去了关系,虽无法知晓痛苦,却更无法知晓春天的柳絮或者夏天游泳池的味道,欢乐与悲伤同时消失。
而最剧烈的恐惧还是来自于未知,没有人知道是谁捧着那碗孟婆汤在桥的那头等着自己,没有人知道当身体化为尘埃的时候,灵魂的21克是否要在黑暗里游荡很久。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想要探知这永恒的秘密,来对抗无答案的恐惧。
竹林里的文人们吞着迷幻药企图长生不老,最终自我麻痹,桃花源不存在于现实生活力,只存在五石散所带来的想象力。像秦俑前世今生的传说也带给人安慰,或许灵魂真的不死,或许那些感情并不会像枯叶般腐烂。而在无数的好莱坞电影里,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了地球毁灭或者世界末日,骗自己说,这就好像是无数次的死亡预演,当真的毁灭时刻到来时,便不再簌簌发抖。
很多很多年前,恐龙们在一个慢悠悠的下午一起消失,那么很多很多年以后,这个地球大概也会像电影里演的一样,无人生还。如果最后连那堵观音殿背后雕满神仙的墙壁都要倒塌,那么所有的迷幻药,所有的催眠术,所有的灾难电影就成为了一只只千疮百孔的谎言,只是现在,它们还抚慰着我们,找不到地方安放的,灵魂的21克。
所有关于世界末日的电影都是对死亡的提前预习,紧揪着人类那些卑微而迷惘的纤细神经。
◎就让地球死在我们手里(1)
文/豆豉
在电影《直到世界尽头》里,亨利的母亲在8岁的时候就瞎了,12岁时遇见了亨利的父亲,父亲此生的唯一心愿就是让母亲复明,于是他成为科学家,带着母亲到世界尽头般的荒芜之地开始治疗,后来母亲看见了,但是她没有告诉别人,这个世界比她想象得丑恶很多,于是在1999年的千禧夜她与这个世界告别。那个晚上预言被预言为是世界末日,但是街道上的人群里,女主角克莱尔哼唱着一首歌:我会记住和你在一起的美好时光……世界末日,Tom Waits在小酒馆里唱着歌,梦境转换成了视觉,所有人都陷入不可自拔的梦境追寻中,而一切都像尤利西斯的漫游追逐般需要答案和回应。在电影里,最后地球并没有被小行星撞毁,在现实生活中,世界末日也并没有如期到来,始终存在着的,只有我们对于世界尽头的一次次追问,以及对死亡的一次次预演,导演后来拍过一套照片,取名为《地球表面的图画》,一切图像就仿佛《直到世界尽头》的语言成真,早在1999年地球就已经毁灭,四周都是荒漠,高楼大厦上爬满了藤蔓植物,停车场里堆砌着生锈了的甲壳虫汽车,没有人,太阳赤裸裸地照在沥青公路上,寂静的,孤独的,澎湃的。
1999年曾经有一个很大的预言说,地球要被毁灭了,很多电影,很多小说,都在想象着世界末日的到来。而那天会怎样,洪水淹没城市,地面崩开巨大裂缝,天际的帷幕被撩开,病毒蔓延,吸血鬼僵尸们在空荡荡的楼房,街道边,游荡,天空永远呈现出一种被蒙蔽的灰色。小时候看一本叫《世界四十九大迷》的书里提到庞贝古城,想着那些姿态保持完整的尸体灰烬,就会开始幻想岩浆突然炸开玻璃,涌进屋子的情景,害怕到起鸡皮疙瘩,却又感到光芒万丈。童年时代站在自然博物馆里,对着那副完整的恐龙骨架,会浮想联翩,那时候海洋与陆地分开,地球变得温暖而干燥,开花植物出现,食草恐龙们像长颈鹿般,温柔地咀嚼着叶子,再后来它们就都被埋在了地球深处,经历了无数次日月更迭后,骨架被挖出来陈列在破旧的博物馆里。
我们对死亡,对毁灭,对末日,对时光的更迭,始终是存着一颗敬畏之心的,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不知道如果有一天,自由女神像的头落到了大街上,电力消失,僵尸横行,是否还有如电影般劫后余生的可能性。于是好莱坞导演们抓住了这根全人类的软肋,让楼房变成废墟,让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