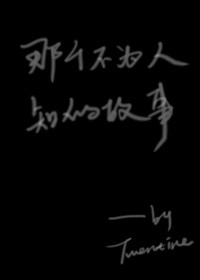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生儿的胎脂。炳璋半张了嘴,呢喃说:“放松……别压着……不要追求音量……控制,稳住……”
炳璋听了几句,似乎不满意。他停下来,起身之后点一炷香,香烟孤直。炳璋把那炷香挨到唇边,示唱“ma——”,香烟和刚才一样孤直。炳璋把那炷香提到耿东亮的面前,耿东亮刚一发音香烟就被吹散了,一点踪迹都没有。炳璋说:“你瞧,你的气息浪费了,你的气息没有能够全部变成声音,只是风,和声音一起跑了。得节约,得充分利用。声音至高无上。你听好了,像我这样。”
《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第一章(5)
炳璋让耿东亮一手提了香,另一只手摁在自己的腹部,整个上午只让耿东亮张大了嘴巴,对着那条孤直的香烟“mi”或者“ma”。
对炳璋来说,声音是这个世界的中心、这个世界的惟一。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声音”而生成、而变化的。所有的声音里头,人类的声音是声音的帝国,而“美声”则是帝国的君主。正如察里诺所说的那样,“人类的音乐就是肉体与精神,理性与非理性的谐调关系。”察里诺所说的“人类的音乐”当然只能是“美声”,别的算什么?只能是马嘶、猿啼、犬吠、狮吼、鸡鸣和母猪叫春。人类的“美声”足可以代表“人”的全部真实、全部意义。它既是人类的精神又是严密的科学。精神是歌唱的基础,而科学则又是精神的基础。他要求的声音必须首先服从生理科学,而同时又必须服从发音科学。然后,这种声音就成了原材、质地,在人类精神的引导下走向艺术。几十年当中炳璋在这所高校里头发现了好几部“好机器”,发现一部他就组装一部,整理一部,磨合一部。可是学校就是学校,所谓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最多四年,他的“好机器”就会随流水一起流走的,然后便杳无音讯。他们就会湮没在某个水坑里,吸附淤泥,生锈,最后斑驳。声乐教学可是无法“从娃娃抓起”的,你必须等,必须在这部“机器”的青春期过后,必须等待变声,否则便会“倒仓”。最要命的事就在这儿,“青春期”过后,“机器”没有修整好,而“机器”的“方向盘”都大多先行装好了,你无法预料这部“机器”会驶到哪里去。
炳璋能做的事情就是碰。说不定能够碰上的。也许的。他的激情与快乐就在于“碰”。又碰上了。
是的,又碰上了。
炳璋对耿东亮说:“你怎么能在浴室里唱那么大的咏叹调呢?太危险了,它会把你撕裂的——要循序渐进,明白了吗?循序渐进。所有的大师都这样告诫我们,察科尼、加尔西亚、卡鲁索·雷曼、卡雷拉斯。你只有一点一点地长。像你长个子,像太阳的位移。成长的惟一方式是寓动于静的,甚至连你自己都觉察不出来。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有‘大’进步了,十拿九稳得回头重来。失去了耐心就不再是歌唱,而是叫喊。只有驴和狗才做那样的傻事。叫喊会让你的声带长小结的。小结,你知道,那是个十分可怕的魔鬼。”
但耿东亮的声音始终有点“冲”,有“使劲”和“挤压”的痕迹,有“磨擦”的痕迹。炳璋跑到厨房去,抱出来一只暖水瓶,拿掉软木塞,暖水瓶口的热气十分轻曼地漂动起来了。炳璋指着瓶口,让耿东亮注视“气息”飘出瓶口时那种自然而然的样子,那种类似于“叹息”的样子。炳璋随后就要过了耿东亮的手,让它罩在自己的口腔前。炳璋又开始“ma——”。耿东亮的手掌感受到一种均匀而又柔和的气流,真的就像瓶口的热气。炳璋说:“明白吗?”耿东亮说:“明白。”炳璋一边点头一边退回到琴凳上去,说:“放松,吸气,像我那样……”
《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第二章(1)
整整一个冬季,耿东亮只纠缠在“mi”和“ma”之间。糟糕的是,炳璋并不满意。他总能从耿东亮的声音里头发现不尽如人意处。在炳璋面前,耿东亮的身体从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机体,它被炳璋的听觉解构了,总有一些要命的零件妨碍了“声音”从机体里头发放出来。不是喉头就是腹膜,不是上颚就是咽喉。这些部位不再是发音器官,而是罪人,它们破坏了声音,使声音难以臻于完美。然而炳璋不动声色。他的神情永远像第一天,专注、肃穆,带着一种“仪式”感。炳璋的诲人不倦近乎麻木,他的耐心与时间一样永恒,你永远看不到他的失望,他的急躁。他四平八稳,一丝不苟,没有一处小毛病能逃得过他的耳朵。他的耳朵炯炯有神。他守着你,对你的身体内部无微不至。
炳璋说:“声音飘。声音没有根。”炳璋说这句话的时候把耿东亮带进了卫生间。他打开了水龙头,在水槽里头贮满了水。炳璋取过一只洗脸盆,放进了水里。炳璋对耿东亮说:“把脸盆覆过去,握住它的边沿,用两只手往上拽,把它拽出水面。”耿东亮伸出手,伸进水里。把覆过去的洗脸盆往上提拉。水在这个时候呈现出来的不是浮力,相反,有一种固执的与均衡的力量往下拽;往下吸。炳璋说:“吃力吗?”耿东亮说:“吃力。”炳璋说:“这只洗脸盆就是你的横膈膜,在你吸气的刹那,它往上抬,然而,上抬的时候有一种力量在往下拽,把这拽住!——它拽得越有力,声音就越是结实有力,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随后就是“mi”“ma”,用炳璋的话说,像他“那样”。
炳璋开始喊耿东亮“孩子”了。虞积藻也一样,开始喊耿东亮“孩子”。他们喊耿东亮“孩子”的时候,不是像父亲,直接就是父亲。他们的表情、腔调全都是父母化了,很自然,很家常,耿东亮就像是他们亲生的了。炳璋的年纪可以做耿东亮爷爷,然而,炳璋的身上洋溢出来的不是爷爷性,是父性。他的刻板与固执在耿东亮的面前成了一种慈祥与无私,以那种“望子成龙”的款式笼罩在耿东亮的四周。炳璋一点儿都不掩饰自己,他像一个真正的父亲,寻找与光大“儿子”身上的遗传基因,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像自己这样”。炳璋的习惯行为越来越多地覆盖在耿东亮的身上了,耿东亮的走姿与行腔都越来越像炳璋了。耿东亮在许多时候都有这样的感觉,在他做出某一个小动作的时候,突然会觉得自己就是炳璋,仿佛是炳璋的灵魂附体了:借助于他的肌体完成了某个动作,耿东亮说不出是开心还是失落,总之,他越来越像炳璋了,不是刻意仿作的,只能称作耳濡目染,或者说,只能是炳璋的精心雕琢。同学们都喊他“小炳璋”了。同学们真的都这么叫了。这里头没有任何讥讽的意思,相反,它隐含了一点羡慕与嫉意,“小炳璋”,这完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只能说耿东亮这小子命好。
耿东亮说不出是开心还是失落。说不上来。这么说可能就准确些了,耿东亮又有些开心又有些失落。耿东亮只能用满脸的麻木打发了这样的内心追问。
炳璋为耿东亮制定了一份详尽的计划,这一份计划涵盖了耿东亮全部的大学生涯。这个计划不仅涉及了耿东亮的声乐训练,它甚至波及耿东亮的日常举止和每天的起讫时间。炳璋修正了耿东亮说话时候的面部表情,那些多余的表情在炳璋的眼里是“不好”的,时间久了,重复的次数多了,会影响人的精神,会成为一种“长相”,凝固在脸上——每一个艺术家都应当对自己的长相负全部的责任。艺术家只能是冷漠的、傲岸的、举止有度的、收放得体的。艺术家站有站相,吃有吃相。“呱叽呱叽地喝稀饭怎么能和艺术家联系在一起呢?”不能。所以耿东亮只能“像炳璋那样”,让“艺术”首先“生活化”、“生命化”。炳璋的要求只说一遍,不重复,不苦口婆心,你要是做错什么了,他就会把脖子很缓地转过来,同时把眼珠子懒懒地转过来,看你一眼。这是一种亲切的告诫,让你自律,让你自己和自己较着劲,让你没有一天能够自在,让你累。
许多夜晚炳璋会把耿东亮留下来,像俄罗斯人那样,用很考究的瓷杯喝一点咖啡。这样的时刻炳璋会把早年的录音磁带取出来,整个客厅就洋溢在炳璋年轻时的声音里了。那是他留苏的日子里留下来的歌声。机子很旧了,磁带也很旧,有一些尘埃和杂音,咝咝啦啦的,听上去好像下了雨。炳璋、虞积藻和耿东亮在这样的时候会坐在一起说些话。这时的炳璋会很健谈,说出来的话也没有太强的逻辑性,有点像自语,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他们甚至谈起一些很世俗的话题,谈吃,谈喝,谈彼得堡的咖啡与面包,谈裙子、布拉吉、头巾,还有几十年前的某一天的天气。他们还谈到生死。炳璋说,他从小就很怕死。现在也一样。死是很无奈的,会把你的歌声带到泥土的下面去。但是炳璋说,现在好多了。炳璋望着耿东亮,像真正的父亲凝视着真正的儿子。炳璋伸出一只手,拍在耿东亮的肩头,说:“你在,我的歌声就不会死。”
然而炳璋并不总是这样宁静。他在倾听自己的磁带的时候有时会毫无预兆地激动起来。他一激动就更像父亲了,有些语无伦次。他把录音机的声音开得很大,歪着脑袋,目光里头全是追忆似水年华。“你听孩子,”炳璋眯了眼睛微笑着说,“你听孩子,你的中音部的表现多么像我,柔软,抒情,你听……”炳璋干脆闭上了眼睛,张开嘴,嘴里却没有声音。但他的口型与录音机里的歌声是吻合的,就仿佛这一刻他又回到莫斯科了,正在表演自己的声音。炳璋打起了手势,脸上的皱纹如痴如醉。在磁带里的歌声爬向“High C”的时候,炳璋张开了双臂,在自己的想象里头拥抱自己的想像物……歌声远去了,停止了,但是炳璋静然不动,手指跷在那儿,仿佛余音正在缭绕,正在以一种接近于翅膀的方式颤动它的小羽毛。炳璋睁开眼,双手拥住了耿东亮的双肩。他的目光在这个瞬间如此明亮。他盯着他。“你就是我,孩子,”炳璋大声说,“相信我,孩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昨天,你就是我的今天。跟着我,你就是我。我一定把你造就成我。”炳璋满脸通红。但他在克制。他的激动使他既像一个父亲同时又像一个孩子。耿东亮十分被动地被这位父亲拥住了双肩,有些无措。无限茫然的神情爬上了他的面颊。他想起了母亲。炳璋炽热而又专制的关爱使他越来越像他的母亲了。炳璋说:“你不开心?你不为此而振奋?”耿东亮堆上笑,说:“我当然高兴。”
《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第二章(2)
耿东亮感到自己不是有了一位父亲,而是又多了一位母亲了。
星期六的晚上炳璋都要把耿东亮留下来。依照炳璋的看法,星期六的晚上是年轻人的真空地带,许多不可收拾的事情总是在星期六的晚上萌发,并在星期六的晚上得以发展的。炳璋对耿东亮的星期六分外小心,他必须收住他,不能让耿东亮在星期六的晚上产生如鱼得水的好感觉。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太如鱼得水了总不会长出什么好果子来。炳璋一到周末就会把耿东亮叫到自己的家里,坐到九点五十分。依照炳璋给耿东亮制定的作息时间表,耿东亮在晚上十时必须就寝的,到了九点五十分,耿东亮就会站起身,打过招呼,走人。炳璋在分手的时候总要关照,十点钟一定要上床。炳璋的至理名言是,好的歌唱家一定有一个好的生活规律与好的作息时间。
但是,耿东亮下了楼不是往宿舍区去。他骑上自行车,立即要做的事情是尽可能快地赶回家。耿东亮必须在星期六的晚上赶到家,母亲这么关照的。一到星期六的晚上母亲便会坐在家里等她的儿子,儿子不回来母亲是不会上床的。她守着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儿子不回来她甚至可以坐到天亮。儿子到了恋爱的年纪了,又这么帅,被哪个小狐狸精迷住了心窍也是说不定的。男人的一生只会有一个女性,亮亮要是交上了女朋友,她做母亲的肯定就要束之高阁了。这是肯定的。母亲不能允许儿子在星期六的晚上在外头乱来,这个门槛得把住。做儿女的都是自行车上的车轮子,有事没事都会在地上蹿,刹车的把手攥在母亲的手里,就好了。母亲不能答应亮亮被哪一个狐狸精迷住心窍,母亲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谁要是敢冲了亮亮下迷魂药,她就不可能是什么好货,一定得扯住她的大腿把她撕成两瓣!一瓣喂狗,一瓣喂猫。
这个世界上有“她”没我,有我没“她”。这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但是,“她”是谁,这就不好说。真正的敌人没有露面之前,谁都有可能成为敌人。做母亲的心里头就越不踏实了。母亲惟一能做的就是让儿子在周末回家,看一看,再嗅一嗅。再隐秘的事情多多少少都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的。然而耿东亮的身上就是没有。他总是说:“在老师家了。”别的就不肯再做半点解释了。亮亮回家总是在十点二十至十点半,再早一两个小时,他这个周末当然是清白的,再晚上一两个小时,做母亲的也好盘问盘问。亮亮就是选择那么一个时间,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这就让人难以省心,问不出口,又放心不下。
“亮亮,太晚了骑车不安全的,下星期早点回家,啊!”
“我不会有事的。”
耿东亮如是说。这句话听上去解释的途径可就宽了。唉,孩子越大你就越听不懂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母与子都知道对方的心思,有时候心心相印反而隔得越远了。
耿东亮在十点半钟回到家,第一件事情便是吃鸡蛋。吃下这两个鸡蛋母亲才会让儿子上床睡觉的。母亲的理论很简单,天天在学校里头唱,哪有不耗“元气”的?耗了就得补。儿子说吃不下。吃不下也得吃。“妈陪着你,当药吃。”
耿东亮知道是拒绝不掉的。母亲所要求的必然是儿子要做的。“当药吃”,还能有什么吃不下去?
耿东亮听母亲的话,童年时代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