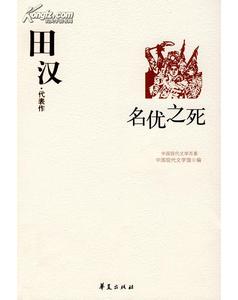矛盾文学奖提名 张一弓远去的驿站-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回春堂掌柜离开了会场,忽地看见数百名饥民已经把“回春堂”团团围住,却并不吵嚷,只 是像饿狼一样定定地瞅他,瞅得他心里发毛,却又进不了家门,就慌慌张张撵上我姨父说: “我认捐,我认捐,我捐两石粮食!”姨父好像没有听见,照旧自顾自地走着。他跟在背后 颠儿颠儿跑着说:“贺保长,我再添五斗!”姨父仍不理他。他就抽了自己一个耳光,“中 ,我不过了,我捐三石!”姨父停下脚步,向灾民们宣布:“回春堂捐粮四石!”回 春堂掌柜打了个愣怔,说:“啥,四石?”姨父说:“对,两千斤。”回春堂掌柜拱 手作揖说:“中,我认了!”灾民就“唰”地给他让开了一条去路。回春堂掌柜一边往 家里走,一边向大家弯身哈腰,“包涵,多多包涵!”
坡底镇的清锅冷灶里冒出了温柔的炊烟。
贺爷叫着儿子的小名说:“胜子,你们共产党只要这样干,能行!”
胜子说:“爹,多亏你带了个好头!”
贺爷说:“你别以为我不懂,我是跟你搞了一回统一战线。”
父子俩的统一战线迅速发展到县城,L县中学成了地下党在全县的领导中心。坡底镇变成了L 县北部山区的“小延安”。
一九三八年,三姨从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回来,也来到坡底接上了党的关系,在关帝庙小学当 了国文教员。她组织抗日剧团,发动民众抗日救亡。那时正在上小学的明表叔记得,三姨召 集歌咏队登上关爷庙的戏台,歌咏队员们耍着关爷的“青龙偃月刀”,高唱“大刀向鬼子们 的头上砍去”。三姨手中捏着一根细棍儿一晃一晃。坡底人才知道唱歌也得有人指挥,而且 ,女人也能指挥。那支歌唱遍了坡底。
那时候,姨父是地下县委的统战部长。三姨喜欢跟他在关帝庙东边的小河旁边散步 。小河两边生长着枝叶茂密的杨树林。在他俩多次逗留过的一棵白杨树下,一个富于观察力 和表现力的学生,用削铅笔的小刀在树皮上刻上了他的艺术发现,让它随着白杨树长大,那 是一支锐利的箭,刺穿了两颗叠在一起的心。
5。雨夜的逃亡
张一弓
在郾城,三姨给我留下了一支很好听的儿歌: 喔喔喔,鸡叫了,义勇军来到了。
打红旗,骑白马,雪亮的大刀腰中挎。
你送饭,我烧茶,大家都来招待他。
母亲到漯河励行中学教书以后,我就把这支儿歌从郾城唱到了漯河。
漯河油坊胡同一号的孩子们不会唱这支儿歌。在那个狭窄的长条形院子里,依次住着身分各 异的房客——一边拉风箱烧火做饭、一边向他的弟子们讲授“孟子曰”的私塾先生,无儿 无女、全靠做针线活儿养活自己的寡妇,按时上班、风雨无阻、天上掉炸弹也一往无前的银 行职员,未向官方注册而把太阳穴上的一小块“俏皮膏药”作为营业标志的妓女。他们各自 做着与那支儿歌毫不相干的事情。
一天黄昏,白胖胖的妓女照旧倚门而立,照旧用微红的睡眠不足的眼睛斜乜着小巷里的行人 。巷子那边有一个人影走过来,她就像上足了劲儿的发条扭动腰肢,胳膊交叉胸前托起了高 耸的乳峰,但她很快又松了发条,乳峰像瘪了气的布袋耷拉下来。迎面走来的是一个蓬头垢 面的汉子,一只脚上穿着张开嘴的破鞋,另一只是沾满泥巴的光脚丫子。
我正跟银行职员的孩子比赛“撞钟”——在迎壁墙上撞铜板,看谁的铜板撞得远。我有一个 杰出的铜板,在墙上“当”地反弹出去,“叮叮咚咚”地滚出门楼、蹦下台阶,绕着一只沾 满泥垢的赤脚踅了一圈,躺在一个高傲的大拇脚趾头旁边不动了。我弯腰捡起铜板时,脚趾 头向我梗了一下,脚趾头的上方有人叫着我的名字。我抬头看见一张长满了黑胡茬子的脸庞 ,黑亮的眼睛一闪,我就跳起来,叫了一声:“姨父!”
我不知道姨父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样子。大杂院里的各色人等都骨碌着眼珠转来转去地瞅他, 像瞅着一个沿途行乞的流浪汉或是发配天边的囚徒。母亲听了他的低语就骇然 变色,急忙让我 领着他抄小路翻过寨墙,到沙河里洗了澡,换上了我父亲留下的服装,又特意请来一 个剃头挑子,把他一头刺猬般的乱发变成了整齐的“寸头” ,满脸黑胡茬子也一扫而光。 母亲急急去到离漯河不远的郾城找姥爷去了。
从母亲与小姨的低语里,我知道发生了意外的不 幸:一群拿枪的人抓走了三姨,正在追杀姨父。姨父让我母亲立即转告姥爷 ,请他设法营救三姨,给母亲留下一个密闭的信封,来不及考察我是否用弹弓消灭过老鼠或 是否击中过鬼子的飞机,又在我和大杂院沉入梦境的时候悄然离去。
二十六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母亲气恼地说,“外调”人员怎么没完没了地纠缠你 姨父从南阳逃到漯河的事情?还给我拍桌子!
母亲说,姨父是从南阳石桥的一所中学侥幸逃生的。他和我三姨从郾城潜逃到那里,分别以 教导主任和国文教师的身分隐蔽下来,却与党组织断了联系。一个下着暴雨的夜晚,有人“ 咚咚”地敲门,接着又听到杂沓的脚步 “噼里啪啦”地踏着泥水急急跑开的声音,感到情况异常,没有开门。他们做对了。解放后 ,有两个落网的特务供 述说,国民党谍报机关从豫西得到了情报,急来南阳石桥抓人,还下了死命令,抓不住活的 要死的!雨夜敲门的就是这两个特务。他们听说我姨父是“双枪将”,不敢贸然破门,就把 一个班的军警埋伏在门外的小巷里,敲了门就跑,试图把姨父和三姨诱出,在街巷里抓 捕。姨父和三姨没有开门,却被堵在屋子里陷入绝境。在万分危急的时刻,姨父的眼睛盯住 了屋子的后墙。那是一面土墙,他看到墙上有一块水湿的印渍,目光就霍地一亮。那是连阴 雨泡湿了墙根脚的印渍。他急忙操起一把铁铲,在墙上捅了一个透明的窟窿,与三姨抱起不 满一岁的婴儿穿墙而出。他们没有吹灯,甚至没有忘记从屋子里拖过一个柜子,堵住了墙上 的窟窿,才悄没声儿地跑到一个菜园子的小草 庵里隐蔽下来。特务供述说,他们还在小巷两边埋伏着,“以逸待劳”呢!
姨父和三姨躲在菜园里,却听不到学校里有任何动静。姨父想,如果并没有发生变故,就这 样穿墙而逃,岂不暴露了自己?就把三姨留在菜园里,只身潜入学校看个究竟。他刚刚 进了校门,正碰上一群特务闯进来,提着马灯在学校里四处乱窜。姨父远远 地 避开马灯,在暗处与特务打转,却在黑暗中与一个工友撞 了个满怀。工友大惊失色说:“你赶紧跑吧!他们把你太太抓走了,用 鞭子抽她,我听见了!”姨父以为三姨在菜园里遭到了不幸,急忙踩着工友的肩膀,越 墙而逃。
那些天,姥爷家和我们家的人都在惊恐不安。“打红旗、骑白马”的儿歌没完没了地在我脑 瓜儿里盘旋。一天晚上,三姨却抱着婴儿令人大喜过望地来到了油坊胡同一号。她面黄肌瘦 ,披头散发,如风雨中的弱柳摇摇晃晃。当她得知姨父已经来过这里,意外的惊喜使她身子 一软,歪在母亲的怀里。母亲问,学校工友说, 你不是怎样怎样了吗?三姨说:“工友误会了,那是特务拷打我们同院的一位老奶奶, 追问我们的下落。我在菜园里,一直等到下半夜,也不见他回来, 倒以为是他出事了呢!”
母亲说,三姨又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她抱着婴儿逃出菜园,跑到从省城来石桥逃难的 堂哥家里,不料特务又接踵而至。 三姨又抱着孩子 从墙豁上跳出去,躲在寨墙底下的防空洞里。特务也紧跟着钻进了防空洞。三姨想,这次真 是插翅难逃了!却发现防空洞里柩着几 口棺材,最里边是一口早已被盗贼掏空了的棺材。三姨抱着孩子钻进棺材里进行了假装死人 的 体验。一具比特务可爱一些的骷髅,不事声张地接纳了她。特务堵严了防空洞,举起马灯晃 了几下,大概闻到了腐尸的气味 ,就骂骂咧咧地踏着烂泥呼啸而去。三姨出了防空洞,从寨墙上吐噜到了积水的寨壕里。
三姨说,还有一个奇迹哩!她怀抱中的大毛正害“百日咳”,特务敲门以前,大毛还咳嗽不 止,吃了一包“止咳灵”,此后在一连串地钻窟窿、进菜园、翻墙头、钻棺材的危急时刻, 这个可爱的小表弟竟在三姨的怀抱 中酣然入梦。当三姨抱着他从寨墙上“吐噜”到野外,终于逃出魔掌的时候,他 才为长久失去发声的自由进行报复,在黑夜笼罩的原野上放嗓咳嗽如连发的快枪。
母亲和小姨都一惊一乍抚着心口说,天哪!天哪!
母亲说,他们的生命是用一个个“偶然性”组成的奇迹。
“外调”人员合上本子说,你不要为他们歌功颂德了!
母亲说,不仅是他们,许许多多革命者在夺取政权以前都有过与死神“失之交臂”的经历。 “外调”人员说,但是,我们知道,你是右派。
母亲说,是的,是的,我得到这个称呼,只是革命者取得政权以后的事情。
“外调”人员说,你还曾经是一个语文教师,你很会编造故事!
母亲闭上眼睛说,那么,你们何必找我听故事呢?
母亲没有兴趣再向“外调”人员说明,她曾把姨父留下的一个信封交给了三姨,而且接下 来发生的事情更加接近于、或者说是十足的传奇。但是我记得,三姨撕开了那个信封以后, 就和她怀抱里的婴儿倏地没了踪影。
解放后, 三姨才对我母亲说,当她和姨父受到追杀而走投无路的时候,姨父走了一步“ 险 棋”,从漯河离开我家,就直奔国民党谍报人员绝然不会想到的一个地方——郑州警备司令 部。姨父的堂兄贺石是那里的少校机要参谋。当我追随姨父回望历史的时候,同时也追随着 一个令人怦然心跳的悬念——在势不两立的政治营垒里,将怎样容纳两兄弟的手足亲情?
6。红 项 圈
张一弓
一九一五年春天,坡底镇贺家大院老二和老三喜得贵子,生日只差一个月,是两个白胖小子 。当了爷爷的老秀才喜不自胜,请银匠打了两个银项圈,裹上红布缝好,送进关帝庙里,在 关爷手腕上戴了七七——四十九天,才把项圈取下来,给两个孙娃戴上。这是坡底的山民世 代相传的一个风俗,这意味着,“忠义千秋”的关爷已经用红项圈拴牢了两个孙娃,会 保佑小哥俩长大成人,还会把他俩调教成“千秋忠义”之士。
爷爷一手牵着一个孙娃,让他俩在关爷庙的老柏树底下蹒跚学步,还要学会在雨后的泥泞里 跟头尥蹶儿地爬坡,学不会爬坡就不是山里的娃子。六岁那年,哥弟俩又形影不离地进了私 塾,念完了《四书》、《五经》。后来,堂弟去洛阳上了高小,二伯却舍不得让独生子去外 地读书。一对堂兄弟为了短暂的分离而魂不守舍。堂弟从洛阳回坡底过寒假时,他俩就钻到 关帝庙里,跪在关爷面前焚香磕头,祈求关爷保佑他哥俩永不分离。据说,关爷的美髯如一 缕黑烟随风飘起,丹凤眼也跟着“忽灵”了一下,收下了小哥俩的美好愿望。假期过后,堂 弟又去洛阳上学时,堂兄就事先偷卷了铺盖,在村外土地庙里等着。两个十四岁的堂兄弟又 结伴去了洛阳,进了同一所学校。堂兄耽误了一年,比堂弟低了一个年级。堂弟说:“我比 你高一级,叫我当哥吧。”堂兄说:“咱俩不分谁是哥、谁是弟了,互叫小名吧,我叫你胜 子,你叫我石子。”
胜子考上了省城现代中学的次年,石子也跟着考上了现代中学。
一九三一年发生了“九 ?一八”事变。十六岁的胜子是开封市学联代表,他们组成请愿团 到火车站卧轨,要去南京面见蒋介石请愿抗日,却被军警从铁轨上四脚拉叉地抬起来,扔到 站台上,押回了学校。石子说:“胜子,你去折腾老蒋干啥?你看我的!”他抓起一个日本 造小闹钟,“我先消灭了这个鬼子再说!”遂把闹钟摔了个稀巴烂,闹钟的铃铛跳起来,“ 叮咛当啷”地逃跑。他又撵上去,一脚把铃铛踹瘪了。石子又跟胜子上街,在古城的街道上 搜索前进,寻找鬼子“派”来的一切“奸细”。他瞅见一辆“三枪牌”自行车停在一家门口 ,就举起门前的石墩砸了自行车。大门里跑出来一个穿戴时髦的小姐,喊叫说:“哪个赖皮 砸了我的车?”胜子说:“你要感谢他,他替你打倒了一回日本帝国主义!”小姐立时消了 气,说:“咦,谢谢了,我真不知道这是小日本儿的东西!”兄弟俩继续搜索前行。胜子说 :“还有一个该砸的东西,不知你敢不敢砸?”石子问:“啥东西?”胜子说:“是南京那 个不准咱抗日救国的独裁政府!”石子吓了一跳,说:“嘿,国家不可一日无主,政府是叫 咱砸的么?”
胜子组织了读书会,让石子跟他一起读书。石子一看,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 ,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瓦尔加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他 拿起一本撂一本,头摇得像拨浪鼓,“都是外国货,不服中国水土!”胜子让他看鲁迅翻译 的苏俄小说《毁灭》,他又把脸偏过去说:“我只看《三国演义》!”
学校放假时,兄弟俩一起回到豫西老家。石子发现,胜子总是背着他,去关爷庙小学找表哥 ,跟表哥有说不完的话,倒是跟他疏远了。他对表哥产生了妒忌,一天晚上,也暗暗跟着胜 子去了关爷庙。
表哥住在关爷庙偏厦的一个房间里,窗纸上扑闪着昏黄的灯光。他从窗棂上的破洞里望进去 ,只见墙上挂着一面缀着镰刀、斧头的红旗,胜子正举着右手对红旗说话。他听不清胜子说 些什么,却能看见他眼里含满了泪水。石子呆呆地站在黑夜里,听胜子和表哥小声唱一支陌 生的歌。他不知道那是《国际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