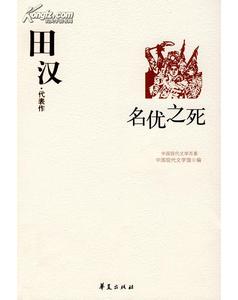矛盾文学奖提名 张一弓远去的驿站-第4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从树上跳下来,蓦地出现在父亲面前。 父亲瞪着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看戏!”
“小孩子不可以看,你看不懂的。”
“我看懂了!”
“看懂什么了?”
“拉胡胡的老头最厉害!”
“他怎么厉害?”
“他吓得那两个人躲在帐子里直打哆嗦!”
父亲点头认可了我的评论,又把他的小板凳塞给我说:“我正要去看望那位很厉害的老头, 你赶快回家睡觉。”
父亲回来时已是深夜。他兴高采烈、比比划划地对母亲说:“找到了,找到线索了!”母亲 问:“找到什么线索了?”父亲说:“‘劈破玉’呀!你能想得到吗?一个小戏班的盲琴师 竟能把明、清曲牌《闹五更》、《粉红莲》、《银绞丝》、《耍孩儿》、《打枣杆》、《节 节高》一口气串连下来,虽为表演淫秽情态所错用,也足见盲琴师身怀绝技、不同凡响呀! 我向他请教《劈破玉》,他说,知此曲牌者千无一人,只有他的师傅柳二胡琴,师从南阳李 秀才,幸得此曲,却从不示人。我问柳二胡琴现在何处?他说,洛阳保安处长请他当了家庭 琴师,教处长三姨太学曲儿。”母亲问:“这个处长现在哪里?”父亲说:“还在洛阳,离 此仅二百余里。”
我终于明白,父亲要找的“玉”是南阳鼓子曲中已经失传的《劈破玉》。 父亲说,他去燕大执教以前,宛儿姨对他讲过, 他们找到的《倒推船》固然十分难得,但宛儿姨听老父说,还有一个《劈破玉》是鼓子曲中 的“娘娘”。清代末年,此曲由江浙艺人溯长江西上而传于汉口,入汉水北上至白河而流入 南阳。五十年前,宛儿姨的老父在南阳石桥镇“曲圣”李秀才的打麦场上听过此曲,由古筝 、琵琶、三弦、笙、箫、檀板合奏,文人雅士和农夫村姑都听得如痴如醉。南阳一富商出高 价求购此曲,李秀才说:“清曲不入商贾家。”把富商拒之门外。李秀才谢世后,此曲下落 不明,只知道他在泌阳收过一个高徒,原来正是这位盲琴师的师傅柳二胡琴。
父亲又在燕大图书馆发现,明、清典籍中多次提到《劈破玉》。最早的记载见于明代举人沈 德符所著《顾曲杂言》,把《劈破玉》列为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流传汴梁的俗 曲之首,给予“可继《国风》之后”的评价。晚于此书一百二十余年的明代天启七年(公元 1627年),又有《芳茹园乐府》一书,称《劈破玉》“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情 而发,如旷野天籁,一曲百应。”再过一百六十余年,刻版于清代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 年)的《扬州画舫录》又说:“俗曲诸调以《劈破玉》为最佳。有于苏州虎丘唱是调者,苏 人奇之,听者数百人。明日来听者益多,唱者改唱教坊名曲,听者一噱而散。”
以上记载与宛儿姨所言相印证,父亲认定《劈破玉》已有四百五十年以上的历史,由汴梁而 入江浙、再由江浙入荆襄、又由荆襄入南阳,吸收了中原和长江两岸的清曲古韵,进入民国 后而不知所终,惟恐再生《广陵散》不可复得之叹,从燕大归来后,就把寻找《劈破玉》作 为他教学之余的第一要务了。
父亲打点行囊,而且找到了那一把吓退过大灰狼的雨伞,就要奔赴洛阳寻访柳二胡琴,却 忽然传来惊人消息:日本鬼子悍然占领洛阳,正向嵩县、潭头进逼。溃逃的“国军”潮水般 经过潭头,向伏牛山深处逃窜。H大学师生缺乏准备,事到临头,校本部才仓促决定,师生 各自逃生,到豫鄂陕三省交界处的荆紫关集结。
父亲暂时放弃了去洛阳寻访《劈破玉》的计划,与母亲打点逃难的行李,忽听寨墙上一声叫 喊:“鬼子进寨了!”父母亲丢掉了全部家当,带领我们五个子女连夜逃出潭头,南渡伊水 ,钻进山洼,到了一个名叫小河的村庄。寨内响起枪声时,父亲才忽地想起,过去搜集的鼓 子曲稿与讲义全部丢到了寨子里,又不顾母亲阻拦,只身掂着打狼的手杖,表现出拼死一战 的姿态,折回枪声大作的潭头去了。
惊人的噩耗不停地传到小河。逃到潭头北山上的H大学师生多人惨遭鬼子杀害。医学院张院 长夫妇和侄儿被鬼子俘虏,张院长侥幸逃脱,夫人被鬼子刺死,侄儿也被刺断食道,受了重 伤。教育系一个男学生为了保护热恋中的女友,赤手与鬼子搏斗,被鬼子刺死,女友投井自 尽。农学院王院长被鬼子抓去当了挑夫,在途中拼死跳崖。那天下着小雨,我看见王伯伯浑 身血迹,由两个农民搀扶着来到了小河。我们一家人都在鲜血带来的惊悸中等待着父亲归来 。
父亲终于出现在村头。潭头的房东用溃兵丢下的长枪挑着父亲从北平带回来的那个邮袋,一 惊一乍地跟在父亲身后。父亲说,他躲在寨外的山包上,望见第一批鬼子劫掠了潭头而后西 去、第二批鬼子正从东山向潭头进发,他抓紧短暂的空隙潜入潭头,用邮袋带出了全部文稿 。一个晕头转向的军官也随着父亲逃到了小河,喘息稍定,就挖苦我父亲说:“你为了一布 袋字纸,命也不要了啊!”父亲发火说:“你说什么?你知不知道,保卫国土是你的职责, 保卫这堆字纸就是我的职责了,你懂吗?”军官惊悚无语,急忙换了便衣,惶惶离去。
次日,我们爬上了老界岭,父亲望着脚下的云海,说:“嗨,劈破玉!”
2。荆 紫 关
张一弓
H大学师生如伏牛山上的落叶纷纷飘坠在丹江岸边。
那里有一个鸡鸣豫、鄂、陕三省的古镇荆紫关,南临江水,北依青山,帆樯如林,商旅如织 。商铺沿江而立,逶迤约三四华里。我们从山上望下去,母亲说它是玉石与江水打磨出来的 玉簪,父亲说它是被打惯了算盘的手指拨弄出毛病来的古筝,我说它是一条红烧或是醋溜出 来的大鱼,哥哥是个结巴嗑子却一鸣惊人,说是是是我想想想象中的劈劈劈劈破破破
的玉。 母亲受到父亲的奚落,父亲受到母亲的挑剔,我受到全家人协调一致的嘲笑,哥哥受到了父 母亲分寸适当的赞许同时也引起了父亲的忧虑。
我们首先遇到的是住宿困难,幸好父亲结识了一位来这里传教多年的英国牧士。他的脑袋如 同一个红亮的蛋壳,雪白的头发全部长在脸上,他还让我第一次看到了水晶般湛蓝的眼珠, 还有他的“万能牙齿”。他声称他的牙齿咬得住自己的鼻子,它果然咬住了,那是一副可以 摘下来、再装上去的假牙。他叫安格尔,人们都叫他安牧士。父亲用磕磕巴巴的英语与他进 行了亲切的对话,安牧士就用怪腔怪调的中国话请我们与他为邻,住进了福音堂里一座具有 中国大屋檐、西式百叶窗的瓦屋。墙上挂着一个半裸的外国男人吊在十字架上受刑的青铜塑 像。
刚在福音堂里住下,父亲就向一个曾在洛阳保安处供职的学生发信,打听保安处长与柳二胡 琴的下落。学生回信说,保安处已经溃散,处长作了寓公。柳二胡琴年迈多病,从洛阳战火 中侥幸逃生,落脚于南阳地区,确切地址不详。回信还说,柳二胡琴为报处长知遇之恩,欲 将《劈破玉》传给处长的三姨太,数次抚筝而怦然弦断,三姨太大惊失色,以为是不祥之兆 ,不敢再领教此曲。柳二胡琴暗对曲友说:“师傅在天上怪罪我了!处长本是狎妓的武夫, 三姨太原是青楼歌妓,此曲是沾不得秽气的呀!”
父亲说:“好,趁学校没有开课,我去南阳找柳二胡琴。”
母亲说:“不宜去!”
父亲说:“有了主耶稣的保佑,你还不放心吗!”
母亲说:“南阳属下有八个县,耶稣保佑你去哪里找到柳二胡琴?荆紫关也在南阳专署治下 ,说不定他就隐居在荆紫关呢!何不在南阳报纸上登一则启事,公布你已搜集到手的曲目, 声明愿与同好者互通有无,附言寻找柳二胡琴与《劈破玉》。好比撒出去一张大网,说不定 会找到那块‘玉’,还会捞上来更多的曲牌呢!”
父亲大喜说:“这么好的主意,我怎么没想到呢?”
后来,邮差源源不断地送来了大包小包。父亲说:“啊呀,我几乎可以汇集一部鼓子曲大全 了!”却又不时感叹:“《劈破玉》,你在哪里?”
我在关心《劈破玉》以外的事情。我十岁了,该上五年级了。H大学没有能力再办附属小学 。我与H大学的教工子弟都去到供奉着河神的“平浪宫”,上了当地的小学。
上音乐课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她第一次上课点名,点到了我的名字就顿住了,惊异地望 着我说:“张斑斑,你是张斑斑?”我也惊诧地叫她:“小李姨,你是小李姨?”是的,她 是张集幼稚园那个让我吃了不少茶叶蛋的小李姨。
“你长大了!”她说。
“你也长大了!”我说。
同学们嘻嘻哈哈笑起来。
小李姨说:“六年了,六年了!”
那一堂音乐课上,小李姨有些心神不定。我暗暗打量她的面容、她的身姿、她的表情而忘了 她教唱的什么歌。小李姨真的不小了,乌黑油亮的两条大辫子变成了浓密的剪发,眼睛依旧 清澈明亮而眸子更加幽黑。幽黑的眸子使她露出有了心事的样子。她的笑也不再无畏地炫耀 洁白晶亮的牙齿,只是轻抿一下嘴唇,露出一双浅浅的酒窝。我在心中用加法计算,六年以 后的她也只有二十四岁。
我想起了小李姨的男朋友——我给他送去很多只“小燕子”、他也给我刻了一个“橡皮图章 ”的何杰。我在潭头看见过何杰,他又成了父亲的学生,是H大学国文系的才子。一个偶然 的机会,在潭头的小戏楼后边,在寨墙上伸出来的歪脖柳树的浓阴下,我看见他跟教育系的 “系花”拥抱亲吻,那是一个使知了不再鸣叫、太阳急速下沉的长吻,不是张集小树林里的 “点发的快枪”。我懂事了,开始学会为小李姨难过,看到茶叶蛋的时候也会引起我早熟的 感伤。
父亲说,小李姨曾经带着一个小包袱,包袱里装着她的嫁妆,去潭头找到了何杰。何杰却带 着教育系的“系花”,请她在“小小饭庄”吃饭。小李姨放下筷子,哭着离开了潭头。父亲 来到平浪宫看望小李姨的时候,避开了与何杰有关的话题,只是表示惊讶说:“小李老师, 你怎么流落到这里来了?”
小李姨说:“这里离内乡张集只有百十里路,还在家门口哩。倒是你们转了一个大圈儿,又 转回来了。可我不知道你在H大学,她……她也不知道你在H大学,她……她以为你还在北平 ,怕你回不来了,还在挂念你哩!”
我一时不能确定小李姨说的“她”是谁。
父亲却露出伤感的样子不再说话。
小李姨怪罪说:“怎么,你把她忘了吗?我是说我宛儿姐呀,她还在她的母校K女师教音乐 ,K女师还在内乡夏馆,离这里很近的呀!”
父亲说:“宛姑娘不是去了老河口吗?”
小李姨说:“她跟那个稽查科长早分手了。宛儿姐其实是很勇敢的,她跟他实在过不下去, 就毅然决然跑回来,在报上发表了一个离婚声明,就拉倒了。再复杂的事情,只要一咬牙, 就变得简单了不是?”
父亲避开小李姨的目光,半晌说不出话来。
小李姨又说,“我跟宛儿商量好了,我们俩这一辈子就一个人过了!”
父亲问:“为什么?”
小李姨瞥了父亲一眼,“女人的心有多重,你们男人是掂量不出来的!”
我作为一个未满十岁的男人当然也是掂量不出来的,但我十分想念宛儿姨。她颤颤的手指, 她哀婉的表情,她脸颊一红陡然发窘的样子,她抚筝而泣的侧影,她的痣。还有那本沉重的 厚书。父亲很久没翻过那本厚书了。
父亲见到小李姨以后,我就像暗探一样盯着父亲。当天晚上,我就发现父亲从破皮箱里拿出 了那本厚书,放在手中抚摸着、抚摸着,却没有翻开,又把它换了地方,装进了邮袋。父亲 说过,“万国公约”规定,这是一个受到保护的邮袋,就是在打仗的时候,谁也不可以侵犯 邮袋。
小李姨开始教我们唱歌。她说,她曾去女师音乐科进修,宛儿姐就是她的老师。她要我们学 会用心灵唱歌,不要扯着嗓子干唱。她教的歌儿不再是《小白兔乖乖》,而是《我的家在东 北松花江上》。她是眼含泪水教唱这支歌的,唱到“流浪、流浪”的时候,她哭起来了,全 班同学都跟着哭起来。“爹娘啊,爹娘啊……”我记得,我们是唱到这里的时候由哽咽不止 而齐声痛哭的。战争时期的孩子会为失去家乡和家乡的亲人而落泪,却不会为失去生 日蛋糕而哭泣。我所以哭,是因为想起了薛姨。请原谅,写到这里,我的心又在颤栗。我不 得不摘下老花眼镜,拭去没有苍老的热泪。
小李姨教我们唱了好几支歌,除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有《大刀进行曲》、《兵 农工学商一起来救亡》,还有一个在风雨中流浪的《难童歌》,一个农夫要“ 多打些五谷送军粮”的《二月里来》,一个漂泊异乡的大姑娘思念家乡、梦见爹娘、又做了 一身寒衣送给情郎去打仗的《四季歌》。然后,小李姨就扯下她的红缎子被面,在火红的被 面上写下了墨黑的大字:“抗日募捐队”。
我开始对父亲的鼓子曲和他整天念叨的《劈破玉》表示不敬,而且盯住了父亲存放鼓子曲稿 的邮袋,感到那是一个很好的募捐袋,几乎是用最后通牒的语气讨要那只邮袋。出乎意外的 是,父亲听我说明了用途,用一种终于发现了“吾家千里驹”的眼神对我刮目相看,毫不犹 豫地掂起邮袋,“吐吐噜噜”把曲稿和那本厚书都倒了出来,又跟我母亲小声嘀咕了几句话 ,把一叠细心查点了两遍的纸币和铜板塞到邮袋里,才把邮袋交给我说:“这是一个极好的 募捐袋,我和你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