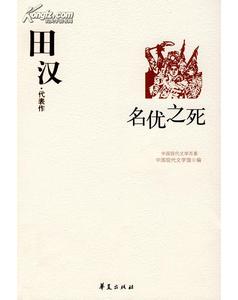矛盾文学奖提名 张一弓远去的驿站-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支学 生游击队住进了客房院。杞地的《地方志》告诉我,那是杞地第一支抗日游击队,共产党杞 地中心县委书记和县委委员都隐蔽在这支游击队里。《地方志》也馈赠给我大舅几个公正而 不乏热情的标记:世家子弟、进步知识分子、富有正义感的国民党员。于是,隐蔽在游击队 里的共产党杞地中心县委就得到了一个国民党员同时又是“民运指导员”和他的家族的庇护 。三姥爷从“看家队”拿了一支手枪给了我大舅。他一转身,就把它别在了共产党地下中心 县委书记的腰带上,只给自己留下了一个空枪套,塞进去一支木头枪。他把右手按在空枪套 上来去如风,俨然是一位面临决战的将军。
在紧挨客房院的大同花园里,游击队员们也在用木枪操练。喊杀声蹿到杨树叶儿上,受惊的 幼蝉就发出一声刺耳的鸣叫,扯出一条响亮的弧线,飘飘悠悠落在我身边的一棵白杨树上。
那是一棵高大挺直的白杨树。风从树梢上掠过,树叶儿飒飒地拍着巴掌。我总是站在白杨树 下寻找大舅的身影。六十年以后,我又在一位将军的“回忆录”里找到了他。他正奔走在兵 荒马乱的大平原上,寻找另一支下落不明的红色武装。将军当时是共产党杞地中心县委的军 事部长,拉起了一支只有十二个农民、四条枪的游击队,却与中心县委失去了联络,找不到 落脚的地方。大舅找到这支游击队时,游击队却遭到国民党保安团的袭击,刚刚被解除武装 。身穿国民党军装的大舅,把右手按在空枪套上,亲率游击队闯进了国民党流亡县衙,指着 县长的鼻子说:“你是日本人的汉奸,还是中国人的县长?”县长说:“孟大公子,有话好 好讲,不要乱扣汉奸帽子!”大舅拍着空枪套说:“我不是公子是武夫。你若不是汉奸,为 什么要解除抗日武装?”县长说:“我有可靠情报,他们是赤色分子。”大舅说:“现在国 共合作抗日,他们就是赤色分子,你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县长翻脸说:“现在,土匪都打 着抗日旗号招兵买马,一下子冒出了几十个司令,你能分清楚谁是真正的抗日武装?”大舅 指着胸前的徽章说:“我奉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招兵买马,这支游击队就是我刚刚组 建的抗日武装。”大舅又拍了一下空枪套,“请你跟我去长官司令部走一趟?”县长慌忙改 口说:“误会,误会!”立即发还了游击队的全部武器。将军回忆说,游击队还趁机多要了 二百多发子弹。大舅的枪套却因为他接连不断地拍打而张开嘴来,赫然露出了假冒伪劣的木 头枪。刚从流亡县衙里出来,将军就慌忙替他合上了枪套。大舅埋怨说:“你怎不早点提醒 我?我就说保安团抢了我的勃朗宁,让他加倍赔偿,再掂走他那挺重机枪!”
大舅刚刚把这支农民游击队带到客房院与学生游击队会合,齐楚就戴着一顶筒形草帽、穿着 教书先生的蓝布长衫,罩住他中共豫东特委书记的身分,只身一人,来到他阔别十一年之久 的客房院。大舅拍着巴掌叫他的小名:“殿章哥,我总算把你盼来了!你看,你的同志都在 客房院等你哩!”三姥爷也高兴地说:“小殿章,你赤手空拳地回来,不怕鬼子啊?” 齐 楚说:“三老师不怕,我就不怕。”又叫着我大舅的小名说,“诚弟不怕,我就不怕。我是 来请教三老师,建立豫东的抗日武装。”三姥爷说:“好,我这客房院里又要有新故事了! ”
齐楚无论是作为豫东农民暴动的领军人物和豫东特委书记,还是作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的H省 省长、中共H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委员,始终是一个令人惊叹、也令人惶悚、伴随着悬 念、也产生着激烈争议的人物。这个出生在杞地一个乡村医生之家、一九二五年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的造反者,以他学究式忠厚谦恭的微笑和他游侠般波诡云谲的身影笼罩着姥爷和他老 哥仨的整个家族 。
一九五六年,在齐楚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以前向党中央所写的《自传》里,特意提到了我 姥爷、二姥爷的“新私塾”,说他是在这个“新私塾”里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启蒙。我姥爷不 胜惶恐地对我说:“哪里哪里?我和你二姥爷只是在各种‘主义’之间,为小殿章他们提供 了进行选择的可能性罢了。归根结底,小殿章是润之先生的好学生,我知道的。”姥爷总是 在私下谈话里称毛主席为“润之先生”,这个称呼开始于一九二六年小殿章亦即后来的齐楚 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成归来之后。他对我姥爷说,润之先生问他:“你这个杞人 ,忧天倾么?”齐楚用杞地口音说:“咋能不忧哩?夜不能寐。”润之先生说:“天要塌, 是扶不起来的。杞人勿忧,回去改天换地就是了。”临别时,润之先生又吟咏江淹的《别赋 》与弟子话别。姥爷隔窗远望,拈须吟诵:“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又眼含 泪光 ,向我批讲说:“这就是说,神情极度悲伤以至于灵魂消散的,只有离愁别绪呀!由此可见 ,润之先生与其弟子之间的情感有多么深厚了!”
姥爷说,一九二七年,齐楚又去武汉开会,听了润之先生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才毅然回到杞地发动了农民暴动,一举拿下了杞地县城,接着又去陈留县与奉系县长朱建 中谈判,只带着随员王复兴和四五个起义军士卒进了陈留县衙。朱建中接到密令,要借谈判 之机,捕杀齐楚于县衙大堂。齐楚进了县衙,偌大一个院子里寂无人踪,却看到偏厦里刀光 闪烁,肃杀之气森森然扑面而来。王复兴示意速逃,县衙大门却在身后关闭,几个冷面枪手 蓦地堵住了后路。齐楚不动声色,一边与王复兴含笑低语,一边摇着芭蕉扇直入大堂。朱建 中将手伸过来虚意寒暄,齐楚接住他的手紧握不放,王复兴也死死抓住朱建中一条胳膊,用 刀刃抵住了他的咽喉。朱建中大惊失色。齐楚说:“对不起,你以谈判为名,要我引颈受戮 ,不够朋友,只好让你‘引颈’送我,请喝退你的枪手。”起义军士卒紧紧裹胁着朱建中出 了大堂。暗中埋伏的枪手纷纷跃出。朱建中急忙喊叫:“不要开枪,千万不要开枪!”王复 兴用刀尖逼着朱建中,起义军士卒护着齐楚直奔后门。朱建中奋力挣脱,翻墙欲逃,被王复 兴一刀刺死在墙头上。县衙内一片混乱。齐楚随士卒越城而出,隐入青纱帐中。姥爷叫了我 一声“小!”叹息说:“从此,对小殿章就不可以书生视之了!”
姥爷还问过我:“小,你知道那个写了《别赋》的江淹是哪里人么?”我摇了摇头。姥爷说 :“他就是杞地的近邻考城县人,考城现在与兰封合并为兰考县了。说来也巧,齐楚领导农 民暴动后,受到通缉,在我这里隐蔽了数月,又跑到江淹的家乡考城县隐蔽下来,当了高小 校长。没多久,他又跑到省城找我。我看他愁眉苦脸,问他,怎么,江郎才尽了么?他说, 不妙,跟他一起隐蔽在学校里的四位同志叫县长一窝抓了,听说就要贴杀人告示,请老师设 法营救。我说,事不宜迟!但我还要考一考你的国学底子,你以我律师名义,写一份辩护词 如何?他熬了一个晚上,写好了一篇绝妙文章,开头就是:‘呜呼!窦娥之冤将重现于考城 矣!’痛陈此案是考城地方派别争权夺利加上多角恋爱之宗派兼男女之争,四位仗义执言的 教师遂成祭品。我说,好了,我给你九十分,剩下十分,就看省法院给不给面子了。省法院 院长是我在北京高等政法学堂同窗,他收下辩护状,急把案子调到省法院审理,未出半月, ‘考城窦娥’得以昭雪。齐楚偕同四位男‘窦娥’,急匆匆逃往豫西造反去了。”姥爷拈须 大笑,“那年大旱,我说,小殿章休逃,你欠了我一场‘六月雪’,何时还我?他鞠了一 躬说,冬天,冬天!”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姥爷抚须自问,“我怎么与共产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呢?一刀刺 死了朱县长的王复兴,也是‘新私塾’里的好学生,生性腼腆,却没有想到他也加入了共产 党,乱军阵中取县长首级如探囊取物,我真的不敢以弟子视之了!我不过让他们读一读马克 思的共产学说,看一看太史公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罢了。”姥爷又摇头叹息说, 暴动失败后,王复兴惨遭劣绅杀害,他的妻女流落开封街头。女儿小名白妮,品貌兼优,是 杞地的美人儿。姥爷看她娘儿俩衣食无着,又见时任河南省财政厅厅长的南汉宸清正廉洁且 风度翩翩。姥爷就安排白妮与南汉宸相识。他俩一见钟情、二见倾心、三见而定了终身。齐 楚见了我姥爷鞠躬便拜,说:“多谢四老师!”姥爷说:“为何谢我?”齐楚说:“多亏四 老师作伐,让烈士的女儿嫁给了烈士信得过的同志。”姥爷才知道南汉宸也是中共地下党员 ,就是建国以后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南汉宸。姥爷感叹说:“时也,命也!既然我和你 二姥爷把‘共产幽灵’请到了杞国,命中注定我要为它的弟子们玉成其事。”
5。夺枪
张一弓
在一九三八年那个遥远的夏季,齐楚所以能够进入一个四岁幼童的记忆,仅仅因为他手中 “噼里啪啦”地摇着一把破芭蕉扇。堂舅告诉我,在他摇着芭蕉扇的时候,他和大舅已经盯 住了国民党一个排的溃兵,准确地说,是盯住了四十多个溃兵的四十多条“捷克式”步枪, 再加上两挺特别诱人的重机枪。这群溃兵像蚂蚁搬家一样从徐州战场上惶惶地爬过来,到了 杞地就把一个村庄里的祠堂当成了老巢,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有人捎信说,土匪头子大 老李给这群溃兵的麻排长捎话,让他把溃兵拉过去,许给他一个副司令。麻排长正跟
大老李 讨价还价,眼看就要随大老李落草了。
晚上,齐楚与我大舅在客房相对而坐,芭蕉扇“噼啪”作响,一直扇到了鸡叫 头遍。我三姥爷来了,问他:“小殿章,你的扇子扇得急,你是有事瞒着我了!”齐楚说: “我和诚弟盯上了一群溃兵的武器。”大舅说:“愁的是没有那么大的荷叶,包不了那么大 的粽子!”三姥爷坐下来,说:“我这里有荷叶,先礼而后兵么!”三个人又唧唧哝哝说了 一阵“鸟语”,齐楚的破扇子就“啪”地一响,说:“好,就听三老师的!”
次日下午,大舅和齐楚陪着麻排长和一个排的士兵来到了客房院。兵们用枪托赶来了一头 一蹿一跳的黄牛,枪刺上挂着鸡的叫声。山羊却表现着一如既往的温顺,一声不吭地被拴 在那棵拴过骆驼的牲口槽上。大舅脸色阴沉,齐楚却忽闪着芭蕉扇,向麻排长赔着笑脸,像 一个惟恐丢了饭碗的教书先生。
三姥爷在这时走进了我的记忆。但我想不起三姥爷身上有前清“拔贡”或是高等法政学堂留 下的任何痕迹,只记得他长得像杞地农民一样墩实健壮,有一张棱角分明的四方脸庞,两鬓 霜雪而红光满面,只是他那双圆环眼里的内容与农民不同,有牛的善良,也有虎的威风;有 黑沉沉的智慧,也有闪亮的锋芒。我望见他走出客厅,向满院子士兵打着招呼。周奶就连忙 把我抱走了。
周奶的老伴——当年在客房院当差的老人告诉我,三姥爷迎上前说:“辛苦了,麻排长!” 兵们轰然大笑,说:“我们排长脸皮麻姓氏不麻,他姓孙,是孙排长。”孙排长骂骂咧咧说 :“这里的野百姓耍贫嘴,张口闭口叫我麻排长,把我的军威也给叫跑了!”三姥爷说:“ 对不起,误会了,请孙排长原谅!”麻排长斜睨着齐楚和大舅,说:“我姓孙可不是当孙子 的孙,是国父孙中山的孙!”三姥爷说:“好,我就喜欢孙中山先生的孙。听说孙排长要带 着弟兄参加游击队,留在杞地抗日,这是杞地的幸事!请贵部在这里安营扎寨,我为弟兄们 接风洗尘。”麻排长说:“那好,弟兄们这辈子的给养就全靠你老庄主了!”三姥爷说:“ 一言为定,只要你们留下来抗日,给养我包了。”
客厅里摆了酒席,麻排长却不落座,让大舅和齐楚领着他进了游击队居住的二进院。他望见 游击队员们手中没有枪支,兜里却插着钢笔,就露出啼笑皆非的样子,“这哪像部队?一群 留着小分头的学生仔加上几个穿长衫的教书匠,打仗都是好样的肉靶子!”又说,驻防怎 么 没有驻防的样子?就在游击队驻扎的二道门外和客厅门前各派了两个岗哨,才走进客厅说: “好了,二位,咱喝着说着,就说说小蛇怎样吞大象!”
那一天,大舅表现了从未有过的耐心,为了表示真诚合作的愿望,特意解下武装带挂在身后 的衣架上。三姥爷陪了三杯酒,说:“你们年轻人吃着喝着说着热闹着,我老了,不胜酒力 ,就不坐在这里碍事了。”齐楚忙着给孙排长斟酒夹菜,三姥爷丢下一个眼色出了客厅。
院子里也摆好了几桌酒席,兵们把枪支架在树下,就一哄而上,等不及当差的倒酒,已经在 自斟自酌,猜拳行令。客房窗口里,学生们的眼睛像乌溜溜的弹丸瞄准了士兵。三姥爷又在 院子里转了一圈,向兵们敬了酒,就进了堂舅屋里,说:“不能大意,要侍候好这群‘丘八 ’,这是一群坏孩子!”
院子里,一个满嘴油腻的“丘八”斜睨着学生们住的客房,唱道:
“南边来了个洋学生,
嘴里噙着‘哈德门’。
有心问他要一根,
就怕丢了人!”
兵们大笑。
当差的慌忙对堂舅说:“当兵的要烟吸呢!”
堂舅就拿了几盒香烟跑出去,给兵们散烟。
三姥爷始终用悲悯的目光望着窗外的士兵,自言自语说:“不要流血啊!”
从正门出去的堂舅,却从屋后通向花园的暗道里匆匆走来,“爹,大老李回话说,三老师给 我打招呼是看得起我,麻排长那四十多条枪我就让给游击队了,算我大老李也‘爱国’一回 。”
三姥爷感叹说:“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