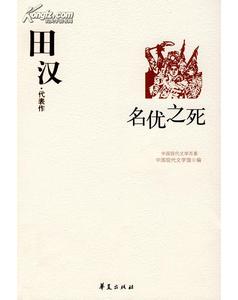矛盾文学奖提名 阎连科:日光流年-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三九说:要了我也卖,卖了我也买件洋布做的衣裳穿。
女人们便都对着三九笑起来,说你不想嫁人了?从大腿上割一块皮就留下一块疤,那疤好了粗糙得连猪皮都不如。三九姑娘就把脸盘红起来,望着远处不再说啥儿。顺着三九姑娘的目光望过去,一村人就都看见蓝四十既没有去围看车轮子,也没有来围看这洋布蓝袄衫。她倚在田头的一棵槐树上,痴痴地盯着这儿的女人们,直到都把目光扫过去,她才把自己的目光软下来,不言不语,弯腰挑起自己的一对箩筐,忽然就独自往田外走去了,烂袄里的棉花白在她的后腰上。
她收工了。她走过的田角上,坐了孤雁似的杜柏。杜柏看了她,她也看了杜柏,问了一句啥儿,杜柏一欠身子,就又孤孤地坐下了。
天色已淡将下来。日光薄薄的,暧意退得干干净净。
蓝三九冷了司马蓝一眼,说,你没给我姐捎衣裳?
司马蓝从自已的后腰取下了那个干粮袋,从中取出了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红洋花布,递给蓝三九,说这是给你六姐买的花布,又取出一双光亮的洋袜子递过去,说这是给你买的洋袜子,还取出了一包盒上画了一片烟叶的香烟,说这是给你爹的;最后就抓出一包小糖,花花绿绿的糖纸,在落日中闪着五颜六色的光彩。村人们分吃着小糖时,就都最终明白了,蓝百岁家的六闺女蓝四十到底成了司马蓝的媳妇了。就都有些愕然,又似乎猛地明白,不是这样,司马蓝会去卖他的皮子吗?会给村里买回有史以来的第一辆车轮吗?
都收工去了。
太阳急急切切地缩了它最后的光色。要回村里时,司马蓝从田里站了三次没能站起来,右大腿上的疼忽然间咯咯卡卡传遍了他全身。蓝百岁拆了那一包香烟,自己抽了一根,也给自己同辈份的三十往上岁数的男人各发了一后走到司马蓝面前问:
“多大一块?”
看女人们都已离了田地,司马蓝解开了裤带,把棉裤脱下来。男人们围过来,便看见他右大腿上缠了一层又一层的纱布,纱布上浸出了一块血水。他把那纱布一圈一圈地解下来,到最后又露出了巴掌大一块方棉纱。司马蓝在那棉纱上用手指划了一个圆圈儿,把头抬起来。
“和核桃树叶差不多。”
杜柏、杜楠、蓝柳根、蓝杨根、及司马鹿、司马虎,和他们后邻的杜柱,这一茬少年都在心里哗啦一下,如猛地推开了一间暗屋的窗,当的一声灵醒到,原来在大腿上割去核桃叶样一块薄皮儿,不仅能买一个车轮子,还能买一件洋布衫,一双洋袜子,一斤小洋糖。那要割去两块呢?割去三块呢?卖掉一条大腿上的整皮呢?不要说买这么多东西,怕是连姑娘媳妇也由自己随意买去了。落日后的静谧,在山梁上铺天盖地。走在梁路前推着车轮的大人们的脚步,由高至低,由粗至细,渐次地远去。三姓村这一代已是少年的大孩娃,簇拥着司马蓝,就都商量着结伙去卖一次人皮的事,商量着卖了人皮,各自要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杜桩说:“我卖了皮子。得很快合铺成亲哩。”
蓝柳根说:“我除了讨媳妇,也得买一条斜纹洋布裤子穿。”
杜柱说:“我不买衣裳,我买二斤肥肉吃。”
轮到最年幼的司马虎,他乜斜一眼司马蓝,说等我卖了皮,我不讨媳妇,也不给村里买车轮,买箩筐、铁锨啥儿的,我给我娘买样东西,剩下的我都存起来。就都明透这话是说他哥司马蓝给蓝家大小都买东西了,竟没给自家买下一丁点。
少年们都瞟着司马蓝。
司马蓝拄着一杆锨把立下了。他望了一群人的脸,最后把目光落在五弟司马鹿和六弟司马虎的脸上,忽然把手插进裤里边,从棉裤裆里的哪儿取出两包儿葵花子和一条深红色的方围巾。那围巾和葵花子上的体温都还白白淡淡,在黄昏的寒冷中几丝炊烟一样扩散着。司马蓝抖抖围巾,对两个弟弟说,没有咱爹了,活着的我是老大,我能不孝母亲吗?又把一包葵花子儿扔给少年中的一个人,说这包本来我想到家后再给鹿弟的,现在大伙分吃了吧。又把另一包丢给司马虎,说我是你哥,大哥如父,连走到家里你都等不及。说完这些,司马蓝就不再和少年小伙们一道了,他拄着那根锨把,从一条岔道往村里走过去。
岔道的前边,他的表弟杜柏,正默默的低头在走着。相距老远的路,就能看见他遗落在身后的心思,如开败的黑花样一片一片。杜柏说“蓝表哥,你没给我买回一根笔?”司马蓝说:“你家做好吃的给我家端过吗?你爹还是我的姑夫哩。”两个少年瞪眼时,蓝百岁不知从哪儿走了来,扛着一柄镢头,把司马蓝的脚步声唤落在一块田头上。
他说:“镇上那儿真的人山人海在翻地换土吗?”
司马蓝说:“都不是镇上人,是三邻五村的劳力汇在那。”
蓝百岁的眉毛结起来,闷了半晌道:
“要都来咱村就好了,我和你娘这辈人就准能吃到新粮啦,就不用连三赶四死得这么早。”
司马蓝盯着蓝百岁。他看着他的脸,像看着一本花花绿绿、有许多卦爻的农家历。
蓝百岁说:“明天你把我引到镇上看一看,看看是哪村也得喉死症,外村劳力咋就给他们干活儿。”
二
所有的转机就是这样冷不丁儿到来的。
蓝百岁和司马蓝去了一次镇上,果然看见成百上千的人们,云集在镇西的一道山梁上,用车推,用担挑,把田地高处的土运到凹地去,把种了上百年的坡地平整得湖面一样,还随着地势,遇物赋形,将所有平整好的地边要么用石头垒起来,要么用锨削得半陡半直,光滑得如行云流水。且那山梁上都还四处荡着红旗,贴了标语,鼎沸的人声,暴雨样哗哗啦啦。看着那么多的人干活,新翻的土地,一片连着一片,蕴含了千年的地气浸着人的心肺,如油烟熏着一样,刺鼻而又开胃。不消说,这不是一个村落的干活人。天下没有这么大的村。男女劳力盖着一面山坡,如河滩上一个挨一个来回跳动的黑黄色的鹅卵石。
司马蓝领着蓝百岁就到了那面山梁上。蓝百岁去问了一位干活人,那人说这是全公社在集中劳力修建梯田试点村,说领着他们来干活的是公社的卢主任,然后蓝百岁就捡一个人隙之处立住了。蓝百岁说,啥是试点村?司马蓝说管他啥是试点村,只要别人能去咱村白干就行了。蓝百岁蹲在地埂边儿不动了,他对面地里有十余辆架子车,车队一样把挖出的土推到一个凹坑里,凹坑里堆满了茶色的光。再往远看,山坡的一块平地上,有几个棚帐,炊烟从棚下挤出来,蒸腾在半空里,白浓浓一会就散散淡淡,溶在冬日的青天白云下。公社的那个卢主任在那棚前说了一阵话,就有人从那棚帐下挑一担开水走出来,好像是去给哪儿干活的农民送茶水。再把目光投得更远些,看见这样的棚帐还有好几处,都有炊烟袅袅,只要卢主任走到那里,那里就有人挑着两个饭桶走出来。
司马蓝闻到了一种白浓浓的香味。
他说:“日他们祖先,渴了还喝大米稀饭哩。”
他说:“这人要都去给咱干活,一年二年就把四百亩地土换完了。”
他说:“百岁叔,谁是卢主任?”
蓝百岁只是不答,叹了一口长气,就沉默得无边无际,把手端在下巴上,直到挑担送饭的人又把空桶从哪儿挑回去,直到头顶的太阳慢慢西沉时,已经有零星的干活人,扛着家什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才自言自语说,要这人都去咱村该多好。
司马蓝盯着蓝百岁的脸。
蓝百岁说:
“回家去吧。”
司马蓝说:
“叔,我能让这人都去咱村干活哩。”
蓝百岁说:
“笑话哩。赶日头不落回村吧。”
司马蓝说:
“真的,叔。我要让这些人都去村里干活了你说咋办儿”
蓝百岁说:
“孩娃,你想干啥你干啥。”
司马蓝说:
“我想当村长。”
蓝百岁笑了笑:
“你才十六就和你爹当年一样儿。”
司马蓝说:
“你不同意?”
蓝百岁不笑了说:
“除了这个,孩娃。”
司马蓝说:
“我今年就娶四十,娶时你不能让我们家花上一分钱。”
蓝百岁大声说:
“行。你说吧,你说咋样儿能把这些人请到咱村去干活。”
司马蓝说:
“找着卢主任,就说我们三姓村这地已经修了五六年,修得比他这儿好,让他到耙耧山里看一看。他到哪儿要不把这些人马往咱村里调,就让全村人给他跪下来。”
蓝百岁脸上没有要走的意思了,看着司马蓝,像看一个不认识的人。
“这样能行吗?”
司马蓝往蓝百岁的头顶瞟了瞟,
“这法儿不行,我娶四十时你就还要彩礼嘛。”
蓝百岁不再说啥儿,他看见人家说的卢主任,从一个棚帐走出来,朝另一道山梁走过去,影子在梯田地里显出浅红色,又韧又长如一挂马鞭子。蓝百岁从地上站起来,说咱们去试试,把卢主任说动了,今年底四十过完十五岁我就让她和你合铺儿。
他们就一前一后朝梁顶走过去。
翻地的农民们都让温热的目光在他们身上潺潺漫漫流。
卢主任迎面走过来,又要往哪儿拐过去。
蓝百岁远远站住了,额门上出了细细一层汗。
他说:“孩你叫他一声。”
司马蓝说:“你是村长。”
他说:“你叫他一声,后边的话我说。”
司马蓝急走了几步,追上去:“卢主任。”
卢主任站住了。
卢主任转过了身,扭得日光在他衣服上打折子。
卢主任还没有蓝百岁的年龄大,三十零几岁像三十还缺几,单瘦如麻,却透了几分白净,因为他年轻,又早早地统领了一个公社的人,他就在工地上这儿走走,哪儿看看,要把双手总是背到身后去,脸上总要凝着惊天动地的深思和熟虑。卢主任转过身时,他周围的日光发出细滑的声音从他身上落下来。他朝司马蓝这儿打量着,像打量一棵叫不出名的树。
“你唤我?”
司马蓝立马道:
“该你去说了。”
蓝百岁便硬着头皮朝卢主任那走过去。落日在他对面照得他有些睁不开眼。到卢主任面前时,他朝卢主任弯了一下腰,看见卢主任穿的是一双最好的黑胶深口的部队上的解放鞋,又看卢主任穿的是部队上的斜纹绿裤子,再看见卢主任的上衣是蓝布中山装。然后他就说,卢主任呀,你领着全公社的人在这修梯田,这人要都到三姓村去,三姓村人会向你和全公社的人跪下来。说我们三姓村春夏秋冬不停歇地干,五六年过去,十面山坡才修了一面半,可那地比这翻得好,比这还像梯子田块哩。说要一个公社都帮着干,不到一年也就干完了四百亩,那时候梯田村才惊天动地呢。
卢主任惊怪地盯着蓝百岁和司马蓝,看了月余年满才开口:
“你说你们梯田已经修了五、六年?”
司马蓝朝前走几步:“这种地已经弄了整六年。”
卢主任说:“谁让你们修的梯田地?”
司马蓝说:“我们自己修的呀,我们说修,村里一敲钟村人就修了。”
卢主任把目光死盯在司马蓝的身上去。司马蓝听见了卢主任的目光迟缓地从蓝百岁身上移到他自己身上后,他感到那目光就柔和温暧了。卢主任把背在身后的手拿到前边来,去口袋摸出一盒烟,让了蓝百岁,他不吸卢主任也没吸。山梁上有风,卢主任把挂在还远处树上的一件部队上的大衣取下来,披在身上,他人就立马显得几分富态了,几分威风了。
“你们是哪个村落的?”
“三姓村。”
“没听说公社还有这么一个村。”
“在耙耧山的最里边。”
卢主任如准备好似的,当即从大衣口袋取出一张公社的行政区域图,问了他们村落在耙耧山脉哪一边,就把地图铺在上层梯田地边上,人在梯田下,正如趴在一张硕大的桌子沿,用指头在花花绿绿的地图上,大海捞针地移动着。有许多修梯田的人朝着这儿看。卢主任的专心好像一位先生一定要在学生的卷子上找出差错来,连有人来汇报各村修梯田的人数他都没抬头。他把指头从地图的下边移到上边去,又从西边移到东,那指头就在地图的边上将要走出图框的东角呆下了。
他终于在地图上一条山脉的尾部找到了一粒小黑点,问你们属那个大队的?答我们村就是一个大队呀。问有多少人口?答说多呢,二百多口哩。卢主任就说那你们不仅是全公社最小的大队,怕还是全县最小的大队了。
问:“你们平素和公社啥来往?”
答:“我们过年时赶集就到公社的镇子上。”
问:“没有到公社开过啥儿会?”
蓝百岁说:几十年间,就没有人通知我们开过会。”
卢主任怔了怔,说我刚从别处调过来,不知道公社里还有这么一个三姓村。不知道你们自发修梯田竟有几年了。说你们是被埋没的典型哩,你们先回去,半月内我一定到你们那看一看。
三
卢主任是一个好干部。当司马蓝老至将死时,还和村人们提到过这干部。说卢主任做事如风如雨,三天后果然到了三姓村,坐着一辆吉普车,把车停在山梁上。这是三姓村有史以来开到村头的第一辆车,和司马蓝给村里买了第一辆架子车的车轮一样有意义,在村史上占着辉煌不朽的一页呢。
那一天,天阴无日,沟沟壑壑都堆积着沉闷的寒冷和冬气。吉普车停在梁顶上,村人们从村里疯着跑到梁顶去,孩娃们惊喜的尖叫,如穿越窗口的光亮样把冬天的积郁照亮了。十四岁以上的男娃女娃和有家有口的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