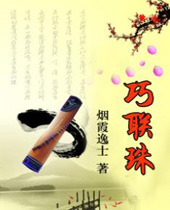我爱黑眼珠-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七等生/ 文
' 编者按:七等生本名刘武雄,於一九三九年出生,苗栗通霄人,台北师范学校艺术科毕业。曾任教於瑞芳镇
九份国民小学、万里国民小学,现已退休,专事写作。一九八三年八月接受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之
邀赴美,年底回国。曾获第一届、第二届台湾文学奖、中国时报文学推荐奖、吴三连先生文艺奖。台湾《联合报》
等发起评选的“台湾文学经典”的共10本小说类中,七等生的《我爱黑眼珠》入选。相关研究'
李龙第没告诉他的伯母,手臂挂着一件女用的绿色雨衣,撑着一支黑色雨伞出门,静静地走出眷属区。
他站在大马路旁的一座公路汽车亭等候汽车准备到城里去。这个时候是一天中的黄昏,但冬季里的雨天尤其看
不到黄昏光灿的色泽,只感觉四周围在不知不觉之中渐层地黑暗下去。他约有三十以上的年岁,猜不准他属於何种
职业的男人,却可以由他那种随时採着思考的姿态所给人的印象断定他绝对不是很乐观的人。
眷属区居住的人看见他的时候,他都在散步;人们都到城市去工作,为什么他单独闲散在这里呢?他从来没有
因为相遇而和人点头寒暄。有时他的身旁会有一位漂亮的小女人和他在一起,但人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夫妇或兄妹。
唯一的真实是他寄居在这个眷属区里的一间房子里,和五年前失去丈夫的寡妇邱氏住在一起。李龙第看到汽车
彷彿一只冲断无数密佈的白亮钢条的怪兽急驶过来,轮声响彻着。
人们在汽车厢里叹喟着这场不停的雨。李龙第沉默地缩着肩胛眼睛的视线投出窗外,雨水劈拍地敲打玻璃窗像
打着他那张贴近玻璃窗沉思的脸孔。李龙第想着晴子黑色的眼睛,便由内心里的一种感激勾起一阵绞心的哀愁。隔
着一层模糊的玻璃望出窗外的他,彷彿看见晴子站在特产店橱窗后面,她的眼睛不断地抬起来瞥望壁上挂钟的指针,
心里迫切地祈望回家吃晚饭的老闆能准时地转回来接她的班,然后离开那里。他这样闷闷地想着她,想着她在两个
人的共同生活中勇敢地负起维持活命的责任的事。汽车虽然像横扫万军一般地直冲前进,他的心还是处在相见是否
就会快乐的疑问的境地。
他又转一次市区的公共汽车,才抵达像山连绵座立的戏院区。李龙第站在戏院廊下的人丛前面守望着晴子约定
前来的方向。他的口袋里已经预备着两张戏票。他就要在那些陆续摇荡过来的雨伞中去辨认一只金柄而有红色茉莉
花的尼龙伞。突然他想到一件事。他打开雨伞冲到对面商店的走廊,在一间麵包店的玻璃橱窗外面观察着那些一盆
一盆盛着的各种类型的麵包。
他终於走进面包店里面要求买两个有葡萄的面包。他把盛面包的纸袋一起塞进他左手臂始终挂吊着的那件绿色
雨衣的口袋里。他又用雨伞抵着那万斤的雨水冲奔回到戏院的廊下,仍然站在人丛前面。都市在夜晚中的奇幻景象
是早已呈露在眼前。戏院打开铁栅门的声音使李龙第转动了头颅,要看这场戏的人们开始朝着一定的方向蠕动,而
且廊下刚刚那多的人一会儿竟像水流流去一样都消失了,只剩下纠缠着人兜售橘子的妇人和卖香花的小女孩。那位
卖香花的小女孩再度站在李龙第的面前发出一种令人心恻的音调央求着李龙第摇动他那只挂着雨衣的手臂。他早先
是这样思想着:买花不像买面包那么重要。可是这时候七时刚过,他相信晴子就要出现了,他凭着一股冲动掏出一
个镍币买了一朵香花,把那朵小花轻轻塞进上衣胸前的小口袋里。
李龙第听到铁栅门关闭的吱喳声。回头看见那些服务员的背影一个一个消失在推开时现出里面黑雾雾的自动门。
他的右掌紧握伞柄,羞热地站在街道中央,眼睛疑惑地直视街道雨茫茫的远处,然后他垂下了他的头,沉痛地
走开了。
他沉静地坐在市区的公共汽车,汽车的车轮在街道上刮水前进,几个年轻的小伙子转身爬在窗边,听到车轮刮
水的声音竟兴奋地欢呼起来。车厢里面的乘客的笑语声掩着了小许的叹息声音。李龙第的眼睛投注在对面那个赤足
褴褛的苍白工人身上;这个工人有着一张长满黑郁郁的鬍髭和一只呈露空漠的眼睛的英俊面孔,中央那只瘦直的鼻
子的两个孔洞像在泻出疲倦苦虑的气流,他的手臂看起来坚硬而削瘦,像用刀削过的不均的木棒。几个坐在一起穿
着厚绒毛大衣模样像狗熊的男人热烈地谈着雨天的消遣,这时,那几个欢快的小伙子们的狂诳的语声中始夹带着异
常难以听闻的粗野的方言。李龙第下车后;那一个街道的积水淹没了他的皮鞋,他迅速朝着晴子为生活日夜把守的
特产店走去。李龙第举目所见,街市的店铺已经全都半掩了门户打烊了。他怪异地看见特产店的老闆手持一只吸水
用的碎布拖把困难地弯曲着他那肥胖的身躯,站在留空的小门中央挡着滚滚流窜的水流,李龙第走近他的身边,对
他说:「请问老板──」
「嗯,什么事?」他轻蔑地瞥视李龙第。
「晴子小姐是不是还在这里?」
他冷淡地摇摇头说:「她走开了。」
「什么时候离开的?」
「约有半小时,我回家吃饭转来,她好像很不高兴,拿着她的东西抢着就走。」
「哦,没有发生什么事罢?」
「她和我吵了起来,就是为这样的事──」
李龙第脸上挂着呆板的笑容,望着这位肥胖的中年男人挺着胸膛的述说:「──她的脾气,简直没把我看成是
一个主人;要不是她长得像一只可爱的鸽子吸引着些客人,否则──我说了她几句,她暴跳了起来,赌咒走的。我
不知道她为了什么贵干,因为这么大的雨,我回家后缓慢了一点回来,她就那么不高兴,好像我侵佔了她的时间就
是剥夺她的幸福一样。老实说我有钱决不会请不到比她漂亮的小姐──。」
李龙第思虑了一下,对他说:「对不起,打扰你了。」
这位肥胖的人再度度伸直了身躯,这时才正眼端详着李龙第那书生气派的外表。
「你是她的什么人?」
「我是她的丈夫。」
「啊,对不起──」
「没关系,谢谢你。」
李龙第重回到倾泻着豪雨的街道来,天空彷彿决裂的堤奔腾出万钧的水量落在这个城市。那些汽车现在艰难地
驶着,有的突然停止在路中央,交通便告阻塞。街道变成了河流,行走也已经困难。水深到达李龙第的膝盖,他在
这座没有防备而突然降临灾祸的城市失掉了寻找的目标。他的手臂酸麻,已经感觉到撑握不住雨伞,虽然这只伞一
直保护他,可是当他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挣扎到城市中心的时候,身体已经淋漓湿透了。
他完全被那群无主四处奔逃拥挤的人们的神色和唤叫感染到共同面临灾祸的恐惧。
假如这个时候他还能看到他的妻子晴子,这是上天对他何等的恩惠啊。李龙第心焦愤慨地想着:即使面对不能
避免的死亡,也得和所爱的人抱在一起啊。当他看到眼前这种空前的景象的时候,他是如此心存绝望;他任何时候
都没有像在这一刻一样憎恶人类是那么众多,除了愈加深急的水流外,眼前这些怆惶无主的人扰乱了他的眼睛辨别
他的目标。李龙第看见此时的人们争先恐后地攀上架设的梯子爬到屋顶上,以无比自私和粗野的动作排挤和践踏着
别人。他依附在一根巨大的石柱喘息和流泪,他心里感慨地想着:如此模样求生的世人多么可耻啊,我宁愿站在这
里牢抱着这根巨柱与巨柱同亡。他的手的黑伞已经撑不住天空下来的雨,跌落在水流失掉了。他的面孔和身体接触
到冰冷的雨水,渐渐觉醒而冷静下来。他暗自伤感着:在这个自然界,死亡一事是最不足道的;人类的痛楚於这冷
酷的自然界何所伤害呢?面对这不能抗力的自然的破坏,人类自己坚信与依持的价值如何恒在呢?他庆幸自己在往
日所建立的暧昧的信念现在却能够具体地帮助他面对可怕的侵掠而不畏惧,要是他在那时力争着霸佔一些权力和私
欲,现在如何能忍受得住它们被自然的威力扫荡而去呢?那些想抢回财物或看见平日忠顺呼唤的人现在为了逃命不
再回来而悲丧的人们,现在不是都绝望跌落在水中吗?他们的只睛绝望地看着他(它)们漂流和亡命而去,举出他
们的只臂,好像伤心地与他(它)
们告别。人的存在便是在现在中自己与环境的关系,在这样的境况中,我能首先辨识自己,选择自己和爱我自
己吗?这时与神同在吗?水流已经昇到李龙第的腰部以上,他还是高举着挂雨衣的左臂,显得更加平静。
这个人造的城市在这场大灾祸中顿时失掉了它的光华。
在他的眼前,一切变得黑漆混沌,灾难渐渐在加重。一群人拥过来在他身旁,急忙架设了一座长梯,他们急忙
抢着爬上去。他听到沉重落水的声音,呻咽的声音,央求的声音,他看见一个软弱女子的影子扒在梯级的下面,仰
着头颅的挣扎着要上去但她太虚弱了,李龙第涉过去搀扶着她,然后背负着她(这样的弱女子并不太重)一级一级
地爬到屋顶上。李龙第到达屋顶放她下来时,她已经因为惊慌和软弱而昏迷过去。他用着那件绿色雨衣包着她湿透
的冰冷的身体,搂抱着她静静地坐在屋脊上。他垂着头注视这位在他怀里的陌生女子的苍白面孔,她的只唇无意识
地抖动着,眼眶下陷呈着褐黑的眼圈,头发潮湿结黏在一起;他看出她原来在生着病。雨在黑夜的默祷等候中居然
停止了它的狂泻,屋顶下面是继续在暴涨的泱泱水流,人们都忧虑地坐在高高的屋脊上面。
李龙第能够看到对面屋脊上无数沉默坐在那里的人们的影子,有时黑色的影子小心缓慢地移动到屋簷再回去,
发出单调寂寞的声音报告水量昇降情形。从昨夜远近都有断续惊慌的哀号。
东方渐渐微明的时候,李龙第也渐渐能够看清周围的人们;一夜的洗涤居然那么成效地使他们显露憔悴,容貌
变得良善冷静,友善地迎接投过来的注视。李龙第疑惑地接触到隔着像一条河对岸那屋脊上的一对十分熟识的眼睛,
突然昇上来的太阳光清楚地照明着她。李龙第警告自己不要惊慌和喜悦。他感觉他身上搂抱着的女人正在动颤。当
隔着对岸那个女人猛然站起来喜悦地唤叫李龙第时,李龙第低下他的头,正迎着一对他相似熟识的黑色眼睛。他怀
中的女人想挣脱他,可是他反而抱紧着她,他细声严正地警告她说:「你在生病,我们一起处在灾难中,你要听我
的话!」
然后李龙第俯视着她,对她微笑。
他内心这样自语着:我但愿你已经死了:被水冲走或被人们践踏死去,不要在这个时候像这样出现,晴子。现
在,你出现在彼岸,我在这里,中间横着一条不能跨越的鸿沟。我承认或缄默我们所持的境遇依然不变,反而我呼
应你,我势必抛开我现在的责任。我在我的信念之下,只伫立着等待环境的变迁,要是像那些悲观而静静像石头坐
立的人们一样,或嘲笑时事,喜悦整个世界都处在危难中,像那些无情的乐观主义者一样,我就丧失了我的存在。
他的耳朵继续听到对面晴子的呼唤,他却俯着他的头颅注视他怀中的女人。他的思想却这样地回答她:晴子,
即使你选择了愤怒一途,那也是你的事;你该看见现在这条巨大且凶险的鸿沟挡在我们中间,你不该想到过去我们
的关系。
李龙第怀中的女人不舒适地移动她的身躯,眼睛移开他望着明亮的天空,沙哑地说:「啊,雨停了──」
李龙第问她:「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你抱着我,我感到羞赧。」
她挣扎着想要独自坐起来,但她感到头晕坐不稳,李龙第现在只让她靠着,只膝夹稳着她。
「我想要回家──」
她流泪说道。
「在这场灾难过去后,我们都能够回家,但我们先不能逃脱这场灾难。」
「我死也要回家去。」她倔强地表露了心愿。「水退走了吗?」
「我想它可能渐渐退去了,」李龙第安慰说:──「但也可能还要高涨起来,把我们全都淹没。」
李龙第终於听到对面晴子呼唤无效后的咒骂,除了李龙第外,所有听到她的声音的人都以为她发疯了。
李龙第怀中的女人垂下了她又疲倦又软弱的眼皮,发出无力的声音自言自语:「即使水不来淹死我,我也会饿
死。」
李龙第注意地听着她说什么话。他伸手从她身上披盖的绿色雨衣口袋掏出面包,面包沾湿了。
当他翻转雨衣掏出面包的时候,对面的晴子掀起一阵狂烈的指叫:「那是我的绿色雨衣,我的,那是我一惯爱
吃的有葡萄的面包,昨夜我们约定在戏院相见,所有现在那个女人佔有的,全都是我的……」
李龙第温柔地对他怀中的女人说:「这个面包虽然沾湿了,但水份是经过雨衣过滤的。」
他用手撕剥一小片面包塞在她迎着他张开的嘴里,她一面咬嚼一面注意听到对面屋顶上那位狂叫的女人的话语。
她问李龙第:「那个女人指的是我们吗?」
他点点头。
「她说你是她的丈夫是吗?」
「不是。」
「雨衣是她的吗?」
他摇头。
「为什么你会有一件女雨衣?」
「我扶起你之前,我在水中检到这件雨衣。」
「她所说的面包为什么会相符?」
「巧合罢。」
「她真的不是你的妻子?」
「绝不是。」
「那么你的妻子呢?」
「我没有。」
她相信他了,认为对面的女人是疯子。她满意地说:「面包沾湿了反而容易下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