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1]_派派小说-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绽开着南瓜似的花朵,花朵里满是蜜糖,等待着早晨蜜蜂的来临,但是过不了多久,你看见的将是一条条甜瓜,而不再是这些花朵了。啊,在这无边无际的宁静中,生命——这种神秘的东西,它既摸不着,也听不见。只有大自然那无所不能,温柔可爱的手在抚弄着它——正在活动着,它在生长,它在壮大。
一个八岁的孩子当然不会想得那么多,也许他还不知道自己正沉浸在这无边无际的宁静中。不过,当他看见一颗星星挂在雪松的树梢上时,他也被迷住了;当他听见一只模仿鸟在月光下婉转啼鸣时,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当他的手触到母亲的手臂时,他感到自己是那么安全、那么舒坦。
生命在活动,地球在旋转,江河在奔流。这一切对他来说也许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也许已经使他模糊地意识到: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最美好的时刻。
雨巷和雨巷诗人
…
戴望舒是20年代后期步入文坛的诗人。因发表脍炙人口的《雨巷》一诗,而有“雨巷诗人”之称。
《雨巷》全诗是这样的: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静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像梦一般的
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
一支丁香地,
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她静静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这首诗写于1927年,是一首象征性的诗。诗中的“雨巷”,狭窄破旧,阴暗潮湿,断篱残墙被迷茫的凄风苦雨笼罩着。从这雨巷我们可以联想到当时令人窒息的时代气氛,“风雨如磐”的社会面影。诗中那个“我”,一腔愁绪,满腹哀怨,正是当时被环境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们的精神状态的写照。他们带着心灵上的创痛在思索着,追求着。而那梦幻般出现又幽灵一样地消逝的丁香姑娘,不就是作者热切追求而实际上不可能得到的希望的象征吗?
戴望舒前期的诗师法象征派,法国的魏尔伦,中国的李金发,对他都有影响。《雨巷》表面上是言情,写的是思慕追求一位有着丁香素质的少女而不可得,实则是象征在生活的重压下一部分人的精神状态。它是一幅想象画,一幅象征性的写意画,是诗人想象中的一个场面,意识流动中的一个境界。在诗的内容上他注重诗意的完整和明朗,在形式上不刻意雕琢。《雨巷》幽微精妙,意境也多少有些朦胧,但可以读懂,且耐人寻味。
《雨巷》这首诗情调是低沉了一点,境界是灰暗了一点,但构成的是具有诗情画意的意境;“我”和丁香姑娘的形象是过于哀伤了一点,但能引起读者的美学感应和共鸣;诗的韵律是不够爽亮匀称,但清新空灵,耐人吟咏。《雨巷》不失为一首好诗。
知心的礼物
…
我第一次跑进魏格登先生的糖果店,大概总在4岁左右,现在时隔半世纪以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间摆满许多1分钱就买得到手的糖果的可爱铺子,甚至连它的气味好像都闻得到。魏格登先生每听到前门的小铃发出轻微的叮当声,必定悄悄地出来,走到糖果柜台的后面。他那时已经很老,满头银白细发。
我在童年从未见过一大堆这样富于吸引力的美味排列在自己的面前。要从其中选择一种,实在伤脑筋。每一种糖,要先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决定要不要买,然后才能考虑第二种。魏格登先生把挑好的糖装入小白纸袋时,我心里总有短短一阵的悔痛。也许另一种糖更好吃吧?或者更耐吃?魏格登先生总是把你拣好的糖果用杓子舀在纸袋里,然后停一停。他虽然一声不响,但每一个孩子都知道魏格登先生扬起眉毛是表示给你一个最后掉换的机会。只有你把钱放在柜台上之后,他才会把纸袋口无可挽回地一扭,你的犹豫心情也就没有了。
我们的家离开电车道有两条街口远,无论是去搭电车还是下车回家,都得经过那间店。有一次母亲为了一件事——是什么事我现在记不得了——带我进城。下了电车走回家时,母亲便走入魏格登先生的商店。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可以买。”她一面说,一面领着我走到那长长的玻璃柜前面,那个老人也同时从帘子遮着的门后面走出来。母亲站着和他谈了几分钟,我则对着眼前所陈列的糖果狂喜地凝视。最后,母亲替我买了一些东西,并付钱给魏格登先生。
母亲每星期进城一两次,那个年头雇人在家看小孩几乎是未之前闻的事,因此我总是跟着她去。她带我到糖果店买一点果饵给我大快朵颐,已成为一项惯例。经过第一次之后,她总让我自己选择要买哪一种。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我只是望着母亲给人一些什么,那人就给她一个纸包或一个纸袋。慢慢地我心里也有了交易的观念。某次我想起一个主意。我要独自走过那漫长的两条街口,到魏格登先生的店里去。我还记得自己费了很大气力才推开那扇大门时,门铃发出的叮当声。我着了迷似的、慢慢走向陈列糖果的玻璃柜。
这一边是发出新鲜薄荷芬芳的薄荷糖。那一边是软胶糖。颗颗大而松软,嚼起来容易,外面撒上亮晶晶的沙糖。另一个盘子里装的是做成小人形的软巧克力糖。后面的盒子里装的是大块的硬糖,吃起来把你的面颊撑得凸出来。还有那些魏格登先生用木杓舀出来的深棕色发亮的脆皮花生米——1分钱两杓。自然,还有长条甘草糖。这种糖如果细细去嚼,让它们慢慢融化,而不是大口吞的话,也很耐吃。
我选了很多种想起来一定很好吃的糖,魏格登先生俯过身来问我:“你有钱买这么多吗?”
“哦,有的,”我答道,“我有很多钱。”我把拳头伸出去,把五六只用发亮的锡箔包得很好的樱桃核放在魏格登先生的手里。
魏格登先生站着向他的手心凝视了一会,然后又向我打量了很久。
“还不够吗?”我担心地问。
他轻轻地叹息。“我想你给我给得大多了。”他回答说,“还有钱找给你呢。”他走近那老式的收款计数机,把抽屉拉开,然后回到柜台边俯过身来,放两分钱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母亲晓得我去了糖果店之后,骂我不该一个人往外跑。我想她从未想起问我用什么当钱,只是告诫我此后若不是先问过她,就不准再去。我大概总是听了她的话,而且以后她每次准我再去时,总是给我一两分钱花,因为我想不起有第二次再用樱桃核的事情。事实上,这件我当时觉得无足轻重的事情,很快便在成长的繁忙岁月中给我忘怀了。
我六七岁时,我的家迁到别的地方去住。我就在那里长大、结婚成家。我们夫妇俩开了一间店,专门饲养外来的鱼类出卖。这种养鱼生意当时方才萌芽,大部分的鱼是直接由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输入的。每对卖价在5元以下的很少。
一个艳阳天气的下午,有一个小女孩由她的哥哥陪同进店。他们大概五六岁。我正在忙着洗涤水箱。那两个孩子站着,眼睛睁得又大又圆,望着那些浮沉于澄澈的碧水中美丽得像宝石似的鱼类。“啊呀!”那男孩子叫道,“我们可以买几条吗?”
“可以,”我答道,“只要你有钱买。”
“哦,我们有很多钱呢。”那个小女孩极有信心地说。
很奇怪,她说话的神情,使我有似曾相识之感。他们注视那些鱼类好一会之后,便要我给他们好几对不同的鱼,一面在水箱之间走来走去,一面将所要的鱼指点出来。我把他们选定的鱼用网捞起来,先放在一只让他们带回去的容器中,再装入一只不漏水的袋子里,以便携带,然后将袋子交给那个男孩。“好好地提着。”我指点他。
他点点头,又转向他的妹妹。“你拿钱给他。”他说。我伸出手。她那紧握的拳头向我伸过来时,我突然间知道这件事一定会有什么下文,而且连那小女孩会说什么话,我也知道了。她张开拳头把3枚小辅币放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在这一瞬间,我恍然觉悟许多年前魏格登先生给我的教益。到了这一刻,我才了解当年我给那位老人的是多么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及他把这个难题应付得多么得体。
我看着手里的那几枚硬币,似乎自己又站在那个小糖果店的里面。我体会到这两个小孩的纯洁天真,也体会到自己维护抑或破坏这种天真的力量,正如魏格登先生多年前所体会到的一样。往事充塞了我的心胸,使我的喉咙也有点酸。那个小女孩以期待的心情站在我面前。“钱不够吗?”她轻声地问。
“多了一点,”我竭力抑制着心里的感触这样说,“还有钱找给你呢。”我在现金抽屉中掏了一会,才放了两分钱在她张开的手上,再站到门口,望着那两个小孩小心翼翼地提着他们的宝贝沿人行道走去。
当我转身回店时,妻正站在一张踏脚凳上,双臂及肘没入一只水箱中整理水草。“你可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她问,“你知道你给了他们多少鱼吗?”
“大约值30块钱的鱼,”我答,内心仍然感触无已,“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于是把魏格登老先生的故事告诉她。她听后双眼润湿了,从矮凳上下来,在我颊上轻轻一吻。
“我还记得那软胶糖的香味。”我感叹着说。我开始洗净最后一只水箱时,似乎还听见魏格登老先生在我背后咯咯的笑声。
伟大的平凡
汽车停在从巴黎去科龙贝—双教堂路上一家花店门前,我们下车选购了一盆洁白的菊花,捧上车,继续这往返千里的旅程。
车在田野间平坦的公路上疾驶。10月中旬的这一天,秋阳朗照,法国的农村,恬静美丽。地里庄稼已经收割,不时看见猎人携枪漫步搜索,一条小狗前后欢奔。庄稼地里和边缘上的丘陵丛林中,不知哪里会窜出一只野兔来哩。
然而,我的思绪不太能够使我欣赏田野风光。上了年纪、生于忧患的人,看见这种安适景象,反而容易勾起往事,产生对比。更何况我们此去是专程瞻仰戴高乐将军的墓地。
初次知道戴高乐将军的名字,早在抗战时期,在四川重庆。那时我在报馆工作,天天接触到国内外战局的发展。祖国半壁河山,沦于敌手,前方节节败退,后方物价飞涨,谣传蜂起,人心浮动。只有西北、华北,人民抗战的烽火遍地燃烧,越烧越旺,鼓舞全国人民打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在欧洲,希特勒侵占波兰,在积极准备后,突然发动西线战事,以强大的机械化部队,绕过马其诺防线,突入法国。法国军方昏庸无能,指挥失当,兵败如山倒。巴黎的政府惊惶失措,屈膝求和,在维琪成立贝当政府。半个法国被纳粹占领,另外半个被压得透不过气来。法国人民奋起反抗,其中突出的代表就是戴高乐。他当时不过是个陆军部的副部长,毅然决然,挺身而出,高举民族抗战大旗,发动“自由法国”的抵抗运动。
这是战火纷飞、风雨晦冥的日子啊!
车窗前,远处是一座树木葱茏的小山头。翠绿之中,一个棕色的双十字架高耸入云,那是“自由法国”的徽号。戴高乐将军之墓快到了。
司机没有在小山脚下停车,而是绕向前去,直驶附近一个小村落,停在一座教堂前的小小空地上。教堂可能是上个世纪留下来的建筑物,屋顶墙壁,饱经风雨,有一点败落景象。一道半圆形的短垣,拱绕着教堂。教堂周围是一个个小小的墓地,埋葬着本村的人。墓,一个挨一个,稍稍隆起地面,是石头砌的,上面竖着或者浮雕着一个十字架,墓碑上写者死者的姓名。戴高乐将军的墓在哪里呢?我们捧着菊花,沿着墓丛中的小径,缓步寻觅。
真使我惊呆了。戴高乐将军的墓,就在小径尽头,也是以石头砌的,高出地面不到半尺。墓呈长方形,中间有一道浅浅的分线,分线左侧的石面上写着:“安妮·戴高乐,1928——1948”。右侧的石面上写着:“夏尔·戴高乐,1890——1970”。墓首有一个以同样的石头琢成的十字架。父女二人的遗体,在这教堂的坟场上,真正是只占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在角落里。墓前一个花瓶,插着杂色的花朵,大概是从本村中采撷来的。那白色稍带灰色的墓石,是最普通的石头,多半是用来镶马路边的。就在这小小坟场中,有好几个墓是大理石砌的。比将军父女之墓,讲究多了。
我默默站在墓前,低头看那朴素、简单到感人肺腑的墓石,思潮澎湃,只觉得面前是一个新的境界:原来一个人的尊严、一个人的品德,是可以用这样简朴、平凡的安排来表达的
!说惊呆了,是由于我对戴高乐将军安葬的情况略有所知。他在1970年11月9日溘然长逝。噩耗传出,全法国一片悲声。将军生前遗言葬在他女儿身边。女儿生来有病,20岁夭折,作为父亲,是十分痛心的。将军的葬礼俭朴,不吹号,也没有乐队奏哀乐,教堂举行弥撒时,没有讲话。将军的棺木,由一辆战车运到
![[网王同人]colorless wind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noimg.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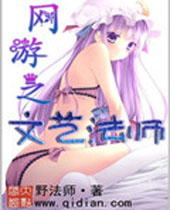

![[末世]镇山河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14/14275.jpg)
![[星际]奋起吧,地球人!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14/1454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