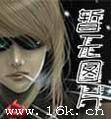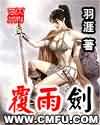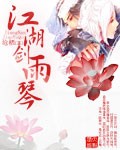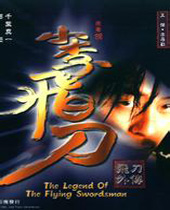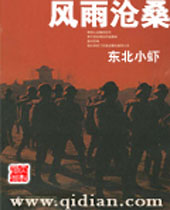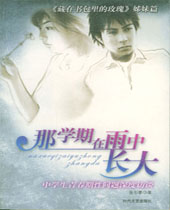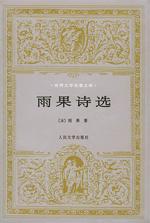吾师余秋雨-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观看了莎士比亚戏剧节上所有的演出,刚好多数的演出都安排在上戏实验剧场。那些日子几乎每晚都有演出,许多早就熟读过的莎翁剧本中的人物和声音,一下鲜活在了舞台上。每天都是一次期盼。记得一位导演系的女孩对我说,真好,学校就像在过节。
就是那样的感觉,有好戏看的日子像在过节。那样的氛围令我无比怀念上戏。
那段日子又翻出余秋雨要求我们必读的《莎士比亚戏剧评论汇编》,再读,再次加入进自己的审美经验,收获巨大。对于西方人怎样评论一出戏剧,尤其怎样用一双后来人的眼睛,去研究几百年前的莎翁剧作,真是让我折服之余又有了嫉妒,觉得人家搞莎翁研究都搞成这样,中国人还搞什么搞。
那样的文艺评论才真正是我喜欢的,像100年前的英国学者昆西的那篇《的敲门声》,麦克白与麦克白夫人借助黑夜在城堡里杀人夺权后,城堡里突然响起清脆的敲门声。这敲门声,把麦克白两口子吓得惊恐万状,也把历来观看此剧的观众搞得心惊肉跳。为什么?这事儿让昆西想了好多年,最终找到了原因:清晨敲门,是正常生活的象征,它足以反衬出黑夜中魔性和兽性的可怖,它又宣布着一种合乎人性的日常生活有待于重建,而正是这种反差让人由衷震撼。
还有许多,几乎每一篇都有让我要跳将起来的“新”发现,记得那是惟一一次我作摘录最多的读书经历,总是撞到那些放不下的说法与结论,恨不能整段、整篇文章都摘抄下来。那么多好文章归放在一起让我来自学,也是有一次就已经很幸福了。
后来还在余秋雨的一篇文章里,也读到他议论“麦克白的敲门声”的文字,那是相同的阅读经验了。
可惜那两大本给过我那么多快感与幸福的书,也在毕业离开上海时被我当废品卖掉了,再找不回来了。想想都要跺脚;
我们看了那一时期上海人艺的所有话剧演出,而他们又总是演外国优秀剧目,大开了眼界。那时奚美娟、焦晃、野芒这些人在上海的话剧舞台上个个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现在大多数人要从电视剧上才能领教到他们的演技。
最记得看上海人艺演出的张晓风的诗剧《自烹》《桃花源记》,惊叹陌生的台湾还有那么一位“腕挟风雷,出古入今”的“大”女人。害得我好几年里一直在托人从台湾捎点张晓风的剧本回来,心里也曾起过“宏愿”:要写就写张晓风这样的话剧。还因为这个张晓风,我还想着研究研究台湾那边的戏剧的,可惜那时就连上海戏剧学院这样的戏剧高等学府,也鲜有这方面的资料。后来一直也没能得到张晓风的剧作选本,倒是直到九十年代,在书店看到一本作家社出的《晓风吹起》,是她的散文随笔选本,巴巴地买了来,想找点蛛丝马迹。
向讲台上的余秋雨致敬(4)
很多人都以为港台那地方出不了什么大作家,尤其是出大气的女作家,而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剧作家张晓风和电影剧作家李碧华,就是挺大气的两位女性作家。香港的李碧华,她的电影《胭脂扣》《秦俑》《霸王别姬》《诱僧》《青蛇》,与张晓风的剧作一样,都是大气而极有现代意识,我一直都在留意。她们都是非常有力地闯入一段古代生活,但绝对不会是“去而忘返”,一去不回。她们最擅长把现代观念深埋进作品的大结构中、人物关系的编排上,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从容,真正是“出古入今”,并且还“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反倒是观众这边,爱看故事的尽可以津津有味去看故事,而爱琢磨点事儿的,立刻两眼亮亮,如醍醐灌顶。完全可以两不耽误。
相对于另一些大叫大喊的作家,我更喜欢这种自自然然、融会贯通的创作姿态。我一直都想把她们作为自己创作的追求目标;魏明伦的《潘金莲》,也是在学院实验剧场看的,他对潘金莲的重新定位,在当时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恨不得引起轩然大波。后来知道余秋雨老师还专门有言行援助过他。不过对于年轻的、不谙世事的我,并没有意识到个中的种种背景与艰难有多么了不得,只是觉得:呀,这个人想到了这一点,他还写出来一出戏,他很聪明,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印象最深的一次外国戏剧艺术交流,是澳大利亚艺术家演出的《蝴蝶夫人》,记得他们处理巧巧桑杀子的情景,他们让巧巧桑一边歌唱着抒发情绪,一边把一只小孩人形木偶拆卸掉,先是揪下它的胳膊,腿,再揪下头,且唱且揪,直至整个木偶解除。那样的感觉,不是让你流串眼泪什么的,是叫你的心一下一下地难受。
其中的震撼,把我嫉妒坏了,在当时中国戏剧形式花样百出的招数里,我还没有见识过如此具有表现力的——后者总是形式大于内容,两张皮扯来扯去的,总也合不到一块儿去,把自己和观众弄得累死了;从没间断过看学院表演系学生排演的各种大戏小戏,总是吃过晚饭,趿着双拖鞋,就晃悠进红楼或是实验剧场,用挑剔的目光,看表演系那帮家伙入戏入得怎么样。印象中上戏倒是很少排中国戏,大多是外国优秀剧目,总能让学生把才华与天赋发挥到淋漓尽致。现在看尤勇在电视里演的那些粗汉子,比不上他舞台上魅力的十分之一。最看重的是萨日娜和潘军,好像天生为舞台而生,可惜他们毕业后渺无音讯。萨日娜倒是演过一个种树的电视剧,非常地投入和到位,即使这样,也再没见过她有更多表现自己的机会。潘军演的一个电视,更是把他当小孩了。后来活跃点的郭东临,留下的印象只是我们背地管他叫“郭胖子”。小陈红被认作是小林青霞,刚刚学会在电话里跟导演讨价还价;马晓晴见人就问是不是最近感觉她瘦了点儿。
甚至有表演系进修生听说我在大学里演过话剧,要约我一道排戏,急得我乱摆手,我说我普通话都说不利落,哪敢和你搞表演的同台,我演方言话剧差不多。
有一段时间在心里其实很羡慕表演系的学生,至少还有那么多的世界一流剧作可以让他们去投入地体验一番。看他们在舞台上的状态,如痴如醉,好让我艳羡,还有嫉妒。我以为他们完全可以在演戏的幌子下,把自我宣泄得一干二净,把自己调理得十二分的通透。只是多年后才醒悟得到,他们也会有他们的迷惘和失落吧,离开了学校这块纯净的艺术土壤,发配前往各处的话剧团、文研所,不要说没有好戏可演,就是连排一出戏也不知多久才有一回。那样的日子里,想起上戏的舞台和老师们的庇护,肯定要掉眼泪的。
一位邀我陪他一起写剧本的表演系学生,有点白俄血统,长得不中不洋,用那时的话说叫“奶油小生”。我们在一起时他总要大骂外面的导演,因为他们只给那些长相粗糙的同窗演戏出镜的机会,他说有些长得粗的人其实心细如针,性格也极柔弱,内在根本就没什么狗屁硬汉气质,可人家天生就长那么张脸,就老能有戏演。现在也是拉开了距离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髦,甚至流行的脸蛋,我们的身边其实到处都潜伏着一些优秀的人才,不要因为未被他的时代认可,就看低了他。而另一些喧哗一时的人与事,也不必盲从和迷信。风云际会,一切都只是瞬时的不期而遇;还有就是三毛从台湾来了,住在张乐平先生家。有人在校园里问我,三毛来了,你不去张乐平家看看她吗。我说我干嘛要去看她。我那时心里还是蛮喜欢她的,在南大读书时,所有人都不知三毛是个什么怪物时,我是第一个在南大书架上发现她的,一下就迷得不得了,到处跟人说三毛和她的荷西。但这次她跑来一口一个要认张乐平作爸爸什么的,被媒体弄得一惊一乍,我就不喜欢了,觉得这不是我喜欢的那个三毛。两年后她自杀了,我又后悔那次没去看她。一个那么热闹的人突然就去自杀,肯定不是我以为的那么简单。谁知道呢。女人本来是很容易成为朋友的;那年张艺谋携刚完成的《红高粱》去西柏林参赛,途经上海,特意在上戏实验剧场首映。那时全国人民都还不知张艺谋何许人也。我们因为看过他的《一个和八个》,知道他特牛。
向讲台上的余秋雨致敬(5)
电影里还有我们上戏的一个学生,他混在一堆抬轿的汉子中出现,剧场里立刻就鼓掌欢呼起来,还有人狂吹口哨,为上戏加油。
《红高粱》放完,大家疯得巴掌都拍疼了。张艺谋披件军大衣,站在台上粗声粗气说:我们的片子拍得很糙。大家也都粗着嗓子跟他学:“很糙。”散场后交流,会议室的窗台上都塞满了人,张艺谋一下就成了上戏学生眼里的大师,校园里成天都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
走”“上下通气不用愁”;
还有有一阵不知怎么回事,学校剧场里每晚都在演各种戏曲折子戏,我吃过晚饭就会晃到剧场去。那些唱腔,突然就触动了我,有时汩汩地从心尖上滑过去,有时又像要把我的心喊出来,好舒服。我差一点就掉了进去。但是戏曲的内容我不喜欢,满处都是糟粕。到后来我不允许自己再去听戏,我怕被它麻醉了。
那时对戏曲有点又爱又怕的意思,好多回都是在快要沉迷的时刻撒腿后撤的。戏曲对于我,就只是适合远看看的景色而已;
只要有要求,余秋雨也会介绍他的学生跟剧组。我们有一位学友就在余老师的推荐下进了《红楼梦》剧组,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年轻气盛,又缺少应对方方面面的经验,没多久就又见那位学友打道回府转来。没有多问,只是听人说和剧组的人处不来,看不太上人家的那一套,自己不想呆了。
其实余秋雨是很希望我们多出去参与艺术实践,积累阅读与观摩之外的艺术经验的,但是大家还是没能迅速适应,一方面毕竟还是学生,不可能采取那样强有力的行动去影响一个剧组接受你的见解与想法,另一方面可能也缺少艺术实践的积累,缺少把观念或者思考转化为戏剧结构的能力。像我们毕业后,余老师与安徽黄梅剧院合作完成的黄梅戏《红楼梦》,他是以艺术顾问的身份参与进去的,整个的剧作与演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红楼情结”与戏剧追求,那是一种很投入的、像孕育一个自己的孩子那样的创造与实践,是我们这帮学生要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才可能争取得到的机会。
对我们那位学友的行为,他也并没有任何责怪或是不悦,熟知一切的他,当然也猜得到自己学生在外面会碰到些什么样的情形,回来就回来了吧,没关系的。下次谁还想去,他还一样介绍去。他只是鼓励、支持大家向外打开,并不过多干涉细节与结果;
二年级的暑假,余秋雨老师安排我们这批研究生前往敦煌朝圣。那年夏天我们随尾而去,他请好的专家和权威人士在等着给我们介绍敦煌的历史与艺术成就。借着导师的庇荫,我们得以看到莫高窟壁画的全部,讲解员一边打开几扇难得打开的洞门,一边强调“这是专家才看得到的,普通游人想都别想”。那时最让我想不通的是,外国人能看到的洞更少,比普通游人的还少,是最低级别。
从莫高窟出来,我们在沙漠里疯玩到深更半夜,完了饿得不行,放风的放风,盯梢的盯梢,潜入驻地食堂偷了几个大馒头分吃。第二天听专家介绍时我又困又累,一直都在打瞌睡,完全不知所云。我猜别的学友们比我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这帮徒弟,也不知是不是给余秋雨丢脸来着。
我只是被鸣沙山绵延的沙漠蛊惑住,时空错乱。后来跟余老师说起在沙漠里的恍惚与迷失,他喜欢得不得了。但是对敦煌艺术的感觉和与余老师的对话,却还是要等到十几年以后才会到来。
而余秋雨老师,敦煌之行后,写了著名的《道士塔》《莫高窟》。
现在想想,三年里上戏的环境和导师们的护卫,曾有那么多的艺术活动与实践机会,为我们打开着一扇大门,我也只是站在门口,让风吹拂了一下我的脸,扬起了几根刘海,却没有抬起腿来跨进去。只是止于大门之前。
再给我一次机会呢?
有人说怎么样经历都是一种经历。我也安慰自己,怎么样做学生都是余秋雨的学生,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主要的,别的都不重要。
写作让他有了非常严肃的责任感(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余秋雨的形象开始更多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他。有知道我们师生关系的,总忘不了说一声,那天在电视里见到你的老师了。
开始的时候,我很不高兴。当时我正在闭门看书和写作,大多时候坐在地毯上面发呆,完全把自己封闭了起来。我一厢情愿以为自己被人养了起来,可以逃班,可以不怕扣工钱,不必穿最好的不必吃最好的,只要有书读有字写就好。余老师在电话里问你怎么总不在家,
你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一直都在家,只是不想接电话,不想单位找到我。他会关心地问我你很忙吗。我嘻嘻哈哈说根本不忙,我正在发呆呢。他便在电话里笑起来,哦,马小娟正在发呆啊。
我总把这当作再一次的理解和容忍。
你的小说我都看了,他说,总是让人兴奋,写得很不老实,还有点黄,但是很明朗,很干净,不过它们总像是一幅幅很好的油画,却没有上框子。他说。
我马上嘻嘻笑。我把一大堆发不出去的小说寄给他,大言不惭在信里告诉他,没人肯发表这些小说,给他看也根本不是想要他干什么的,就是想让他看,看看我写的小说。
他说我的小说没上框儿,我竟越发地高兴,因为我房间的地上刚好就随意立着几幅朋友画的油画,又刚好是没上框儿的。我就喜欢这感觉。我受不了给它们套上框框再装模作样高挂在墙上。
我才不需要上什么框儿,小说发不发表的无所谓,反正我写了,发泄了高兴了就行了。发表不了不就是少两个稿费嘛,我有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