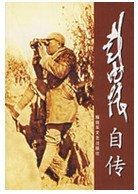富兰克林自传-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七三三年我派遣我的一个职工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查理斯敦去,那里需要一家印刷铺。我供给了他一架印刷机和一些铅字,跟他订了一个合伙合同,我将获得三分之一的盈利,担负三分之一的开支。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诚实廉洁,但不懂会计。所以虽然有时候他汇款给我,我总不能从他那里取得会计报告,在他生前我也不能取得关于我们合伙情况的一个令人满意的报告。在他死后,他的寡妇继续管理印刷所的事务。她在荷兰生长;据说在那里,簿记是妇女教育的一部分。
她不但对以往的收支作了一个尽可能地清楚的报告,并且以后每季按时继续寄来十分精确的报告,她管理业务是如此成功,她不但把一家孩子都养育成人,颇有令誉,而且在合伙期满以后,能够把印刷铺从我手里买了过去,叫她的儿子去经营业务。
我提这件事,主要是为了向我们的年轻妇女们推荐这门学科,万一结婚后守了寡,簿记大概会比音乐或跳舞对她们本人或她们的子女更有用,它使她们不至于受坏人的欺骗而遭受损失,或许使她们能够靠着已经建立起来的通信关系继续管理一家赚钱的商店,直到她们的儿子长大后能够经营和继续事业时为止,这样对于家庭既有益又有利。
约在一七三四年一个叫做韩泼希的年轻传教士从爱尔兰跑到我们这里来了。他声音洪亮,而且讲起道来,显然未经准备也能讲得天花乱坠,他的说教吸引了相当数量属于不同教派的人在一起,他们同声赞美他。
我跟其他人在一起,经常去听他讲道;我喜欢听他的说教,因为他不作教条式的阐述,而是热烈地劝人为善或是用宗教术语来讲所谓积功德。但是我们会众中有一些自命为正统派长老会信徒的人,他们反对他的看法;大多数年长的教牧师都参加了这一派,并且向长老会的宗教议会提出控告,指责他为异端,想要禁止他传教。我成为他热烈的拥护者,并且尽我的力量协助他把拥护他的人组织起来,我们为他战斗了一个时期,我们倒颇有胜利的希望哩!双方都在这时候进行了不少笔战。我发现虽然他是一个极能干的传教士,他的文章却写得不行,因此我替他执笔,代他写了两三本小册子和一篇一七三五年四月在《公报》发表的论文。这些小册子,像普通其他争论性的文章一样,虽然当时风行一时,事后却很快地无人问津了。我猜想恐怕现在连一本也找不到了。
在论争中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件,大大地损害了他的事业。我们的敌方中有一个人,在听他讲完了一篇大受人们赞美的讲道以后,觉得他以前在什么地方读到过,或是至少一部分曾经见过。经过搜索以后,他在一本英国的评论中找到了那段说教的详细引文,原来这是从浮士德博士的讲道文中引来的,这一发现使我们当中许多人看不起他,因此不再支持他了,这样就使我们在宗教议会中的斗争很快地失败了。但是我始终支持他,因为我宁可听他念别人写的优秀的讲道文,而不愿听他自己杜撰的恶劣的说教,虽然我们普通的传教士都是自己写讲道文的。以后他向我坦白说他的说教全都不是他自己写的,他还说他的记忆力很强,任何讲道文一经过目,他就能背诵不忘。我们被击溃以后,他就离开了我们,到别处去碰运气去了,我也离开了这一会众,以后再也不加入这一教会了,虽然我继续捐献维持这一教会的牧师达许多年之久。
在一七三三年我开始学习外国语了。不久我获得了足够的法语知识,使我能够顺利地阅读法语书籍。接着我学习意大利语。我有一个朋友,当时也在学意大利语,他常常怂恿我和他下棋。当我发现下棋过多地占用了我原定学习的时间时,我终于拒绝再跟他下棋了,除非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那就是:每盘棋的胜利者有权指定一种作业,不论是语法部分的背诵或是翻译,失败的一方要保证在我们下次会晤之前做好作业。因为我们的棋艺不相上下,这样我们就相互地把意大利语灌输到各人的头脑中去了。以后我化了一点苦功去学西班牙语,我也获得了阅读西班牙语书籍所需要的知识。
我在上文中已经提过,我在幼年时曾在拉丁学校中学过一年拉丁文,以后我就完全把它置之脑后了。但是当我熟悉了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以后,翻阅一本拉丁文圣经时,我出乎意料地发现,我所懂得的拉丁文远较我想像的为多,这就鼓励了我再去专心学习拉丁文,我的收获很大,因为以前学过的几种语言替我大大地铺平了道路。
从这种情况看来,我认为我们普通教外国语的方式有些不合理的地方。有人说我们应当先从拉丁文开始,在学会了拉丁文以后,再学习由拉丁文演变出来的现代语言就容易得多了。但是为了更顺利地学习拉丁文,我们却为什么不从希腊文学起呢?当然,假如你能不用阶台而攀登到顶点,然后再下来时就更容易走了。
但是无疑地,假如你先从最低的梯级开始,那就更容易达到顶点了。有许多人学拉丁文,学了几年后就毫无成绩地把它丢弃了,他们过去所学的几乎完全无用,因此他们的光阴是白化了。既然如此,我请主管我们青年教育的当局考虑是否应当先从法语开始,然后学意大利语等等,因为即使在学习了同样的年数以后,他们不再学习外国语因而从未达到学拉丁文的阶段,但是到那时他们已经学会了一种或两种外国语,因为这些是现代通用的语言,所以它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有用。
我离开波士顿已经十年了,现在我的生活也优裕了,因此我到波士顿去旅行了一趟,去探访我的亲戚,在这以前我没有充裕的财力来作这样的旅行。在归途中,我到新港去看我的哥哥,他这时已经把他的印刷铺搬到那里去了。我们过去的旧嫌已经冰释了,我们的会晤是十分热烈和恳挚的。他的健康正在很快地衰退中。他请求我在他死后(他恐怕他的死期不远了),把他当时仅十岁的儿子领到我家里来,使习印刷业。这个我照办了,我先送他上学校读了几年书,然后叫他学印刷业。他母亲继续经营印刷所的业务,直到他成年时为止。他成人后,我送给他一套新铅字,因为他父亲的铅字有点磨损了。这样我充分地赔偿了我哥哥由于我提早离开他而所受的损失。
在一七三六年我的一个儿子,一个四岁的很好看的孩子,因感染了天花而夭折了。我在一个长时期内十分痛心地悔恨,并且到现在我还后悔我没有事先替他种痘。我提这件事是为了那些不替孩子们种痘的父母。他们以为万一孩子因种痘而死,他们将永远不能饶恕他们自己。但是我的实例表明不种痘也同样有危险,因此他们理应选择一条危险较少的道路。
我们的社团(密社)成为一个非常有益的组织,它使会员们觉得十分满意,有些会员就想介绍他们的朋友来入会,但是假如这样做,那就会超过我们早先决定的适当限额,那就是,十二人。从开头我们的社团一向就是秘密的,这一点我们都信守不渝。这样做是为了免得坏人来申请入会,其中有些人可能会使我们觉得难以拒绝的。我就是反对放宽限额的人之一,但是为了不放宽限额,我作了一个书面建议,提议每个会员应该分头设法组织一个附属社团,拟订相同的讨论规则,但是不泄露它与密社的联系。我指出这个办法的优点是:更多的青年公民可以利用我们的社团获得提高,在任何时候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一般居民的意见,因为密社的社员可以在分社中提出我们讨论研究的题目,并且把各分社讨论的经过向密社报告;通过更广泛的推荐和介绍,我们可以增进我们各人事业上的利益;我们可以把密社的主张和看法散播到分社中去,这样可以加强我们的政治影响和我们为社会服务的力量。
这个计划是通过了,每一个社员就着手组织他的社团,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成功的,只有五六个分社组织了起来,它们的名称五花八门,像“葛藤社”,“协会”,“群社”等。它们不但对社员自己有益,而且给了我们不少的消遣、消息和教益,同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符合了我们原先的期望,在某些特殊的事件上影响了公众的舆论,我以后在适当的时候还要举出一些这类的实例。
一七三六年我当选为州议会秘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获得升迁。那年我倒是一致通过了,但在第二年,当我的名字又一次提出来时(秘书的任期,跟议员的任限一样,是一年),一个新议员,为了赞助另一个候选人,发表了一篇长篇演说反对我。但是我还是当选了。
我自然很高兴,因为除了秘书职位本身的薪给以外,这个职位使我有很好的机会与议员们维持联系,这种关系又替我招揽了印刷选举票、法律、纸币和其他零星的公家生意。这些生意,大体说来,利润是很厚的。
我不喜欢这位新议员反对我,因为他不但是个财主,受过教育,而且很能干,过一些时候他很可能成为议会中一个很有势力的人。后来事实果然如此。但是我不打算卑躬屈膝地去奉承他,以期获得他的青睐;过了一段时间我却采用了另一个方法。我听说他的藏书中有一本稀有的珍本书,我就写了一张便条给他,表示我很想看那本书,希望他能借给我看几天。他立刻把它寄来了,大约过了一星期我把书送还给他,附了一张便条,热烈地表示我的谢忱。当下一次我们在议会中见面时,他跟我招呼了(他以前从不如此),而且十分殷勤有礼。从此以后,他在任何时候总是愿意帮我的忙,因此我们成为知己的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死为止。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从前听到的一句古老的格言是对的。这句格言说:“假如一个人帮了你一次忙,那么以后他会比受过你恩惠的人更乐意帮助你”。同时,这件事也表明了与其怨恨、报复和延长私人间的冤仇,倒还不如审慎地把它消除更为有益。
在一七三七年施保茨乌上校(维基尼亚的前任州长,当时的邮务总局局长)因不满意费城邮务代办在处理账册方面的疏忽失职和账目不明,把他革了职,就提议叫我继任。我欣然接受了,后来发现这个职位对我大有裨益,因为虽然它的薪给很小,但是它便利了信件的来往,间接改进了报纸,因而增加了它的发行数,同时也招徕了更多的广告,结果是这一职位大大地增加了我的收入。作为我多年劲敌的那家报纸却相应地衰落了,我对他在当邮务代办期间不允许骑师递送我的报纸的举动不采取报复手段,因为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这样,他因不注意适当的簿记术而受累无穷。我提起这件事作为对年轻人的一个教训,他们若是将来替别人办事,他们就应当永远把账册弄得清清楚楚,而且要规规矩矩地把款额上缴。假如能够做到这个地步,那么一个人的品德就成为他最有力的推荐书,能够替他谋得新的职位和招徕更多的生意。
现在我开始把我的思想稍稍转到公共性质的事务上去了。但是我从小事着手。费城的巡夜制度是我认为亟须加以整顿的事项之一。防夜原由各区的警官轮流负责,警官预先通知若干户主在夜里跟他去巡夜,那些不愿意去巡夜的人每年出资六先令,就可以免去这项差役。这笔钱原定是用来雇用替代人的,但是却大大地超过了实际的需要,这就使得警官这一职位成为一个肥缺。警官们常常收罗一些乞丐无赖,给他们喝一点酒,就叫他们一起去巡夜,但是有相当地位的户主却不愿与他们为伍。巡夜工作也常常被忽略了,大多数的夜晚是在喝酒中度过的。因此我写了一篇论文,准备在密社宣读,指出这些不正常的情形,特别强调警察在课税时不问纳税人的经济情况,一律征收六先令,因而造成了不平等,因为一个穷苦的寡妇户主的全部需要保护的财产也许不超过五十镑的价值,而她所付的巡夜税却和一个仓库中贮藏着价值几千镑货物的大富商完全一样。
从整体来讲,我提出了一个较有效的巡夜制度,那就是雇用适当的人经常从事巡夜工作;我也提出一个较公平的摊派巡夜费用的办法,就是按照财产的比例课税。经过密社的同意以后,这一计划就传到各分社去,作为各分社自己提出的一个计划,虽然这一计划并没有立刻实行,但是我们在人们的思想上替这一变革作了准备,替几年后通过的那条法律铺平了道路。当那条法律通过时,我们社员的社会地位已经日渐重要了。
大概就在这时候我写了一篇论文(先在密社宣读,但后来却发表了),论及酿成火灾的各种疏忽和事故和防火须知,并劝人小心火烛。大家认为这是一篇有益的文章,因此,为了迅速扑灭火灾以及在发生危险时相互协助搬运和保管货物起见,就产生了组织消防队的一个计划。不久就有三十人愿意参加这一组织。根据我们的合同,每一队员必须经常保持一定数量适用的皮水桶和结实的袋囊和筐子(以便装运货物),一有火灾就必须把它们运到现场。我们决定每月开一次联欢晚会,讨论和交换我们想到的有关防火的看法,这种知识在发生火灾时或许对我们有用。
消防队的效用不久就很明显了。愿意加入的人大大地超过了我们认为每队应有的适当限额。我们劝他们另外组织一队,他们就照办了。这样新的消防队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地组织起来,直到后来它的数目十分众多,大多数有房产的居民都加入了。现在当我写本文时,我最初建立的叫做“联合消防队”的组织,虽然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五十多年,它还存在着,还是很活跃,虽然第一批队员中,除了我和另外一位年纪较我长一岁的人以外,其余的人全都过世了。队员因不出席每月例会而缴纳的小额罚金就用来购置救火机、云梯和其他对消防队有用的器械。结果是我猜想世界上没有其他城市比费城更能迅速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