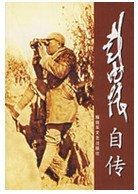富兰克林自传-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一事件使雷夫立意要成为一个诗人。我尽我之所能劝阻他,但是他继续写诗,直到蒲柏治了他。但是,他后来成了一个相当好的散文家,以后我还要提到他。
但是因为也许我以后不再有机会提到其他两个,我在这里交代一下:过了几年,华生躺在我的怀抱里死去了,使我大为悲痛,他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一个人。奥斯朋到西印度群岛去了,在那里他成了一个著名的律师,赚了钱,但是早年夭折了。我和他曾经认真地订了一个合同:谁先死,如果可能的话,就应当向另外的一个人作一个友好的探访,告诉他死后的情况如何。但是他从来没有履行他的诺言。
那位州长表面上好像很喜欢和我来往。常常叫我到他家去。在谈到他帮我开业这件事的时候,总是当作已经议定的题目提出来的。除了银行汇信,使我获得购买印刷机、铅字和纸张等所必需的款项外,他说他将给我一些给他朋友的介绍信。他好几次指定了写好这些信件的日期,叫我去领取,但是到了时候总是指定一个更远的日期。这样几次三番的延宕着,直到那只船,也经过了几次延期以后,快要启航了。那时,当我去辞行领取信件时,他的秘书拜耳博士出来见我,说州长正忙于写信,但是在开船之前他会到纽开色来,在那里他会把信件交给我。
雷夫,虽然已经结了婚,有了一个孩子,还是决定陪我出洋。据猜度他是想去建立通信联系,获得可以代销的货品,抽取佣金,但是后来我知道由于他对他妻子的亲戚不满,他打算把他妻子交给他们,自己永不再回来了。我辞别了我的朋友,跟李得小姐交换了海誓山盟以后,我就坐船离开了费城,船不久就停泊在纽开色。州长果然在那里,当我到他住所去的时候,他的秘书出来接见我,传达了他的口信,措辞的谦恭是世界第一,说他那时因有十分重要的公务羁身,不能见我,但是他会把信送到船上来的,他衷心地视我一路顺风,早日归来等等。当我回到船上时,我有点迷惑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怀疑。
费城的一个著名律师安得烈·汉密顿先生带了他的儿子乘坐同一只船,他跟一个教友会的商人田纳先生和马里兰一家铁工厂的两个老板安宁先生和赖叟先生包了正舱,这样我和雷夫就不得不坐三等舱了。船上我们一个熟人也没有,所以他们把我们当作普通人。
但是汉密顿先生和他的儿子(是詹姆士,以后当了州长)从纽开色回到费城去了,老汉密顿为了替一只被没收的船进行辩护被人用重金请回去了。在我们刚要启碇前,富兰契上校上船来了,对我颇器重。因此他们注意了我,那些绅士邀请我和我的朋友雷夫住到正舱里去,因为这时候有地方空出来了。因此,我们就搬入了舱中。
因为我猜测富兰契上校已经把州长的公文送到船上来了,所以我就向船主要那些委托由我保管的信件,他说所有的信都一起放在信袋里了,这时候他一时没法拿出来,但是在我们到达英国前,他会给我机会把他们拣出来。这样我就暂时安心了,我们继续向前航行。
舱中的乘客很爱交谈,同时我们的饮食特别丰盛,因为除了普通的伙食外,我们还额外有汉密顿先生的饮食必需品,汉密顿先生原来贮备了很丰富的伙食的。在这次旅途中田纳先生跟我结成了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继续到他死为止。但是在另一方面,这次旅程是不舒适的,因为有许多日子天气太恶劣了。
我们驶入英格兰海峡后,船主实践了对我的诺言,给我一个机会在信袋里寻找州长的信件。我找不到一封委托我保管的信,我挑出了六七封信,按照信上的笔迹,我猜想可能是那些约定的信件,特别是因为其中有一封是写给皇家印刷所巴斯吉的,另一封是给一个文具商的。我们在一七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达伦敦。我去拜访那个文具商,他离开我的地方较近,我递送了那封信,说是从基夫州长来的,“我不认识这样一个人”,他说,但是一面拆信,“哦,这是李德斯田的信。近来我发现他完全是个骗子,我将与他断绝来往,我不收受任何他的来信。”这样,把信放在我的手中,转过身去,离开我去接待一个顾客去了。我很惊奇,发现这些信并不是那位州长写的,经过回忆和比较先后的事实,我开始怀疑他的诚意了。我找了我的朋友田纳先生,把这件事的经过全部讲给他听了。他告诉我基夫的性格,他说他绝对不可能替我写了任何信,无论哪一个知道他的人都不会对他有任何信赖,他听说州长会给我银行汇信,笑了起来,因为他说他根本没有账款可汇。
当我担心我今后当怎么办时,他劝我设法在我的本行中找一工作。“在这里的印刷铺里工作,你可以提高你自己。以后你回到美洲去时,那你开业的条件就更好了”。
我们两人,像那个文具商人一样,碰巧知道这个律师李德斯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他唆使李得小姐的父亲拜他为师,订立师徒合同,几乎使得李得先生破了产。从这封信里看来,好像有人正在酝酿着一个不利于汉密顿的密谋(他们假定汉密顿是跟我们一起到英国来的),而这一阴谋又牵涉到基夫和李德斯田。田纳是汉密顿的一个朋友,认为我应当告诉汉密顿这封信的内容。这样,当他不久到达英国时,一则是为了发泄我对基夫和李德斯田的愤怒和憎恶,二则是为了对汉密顿表示好感,我去拜访了他,并把这封信给了他。
他诚挚地感谢我,因为这一消息对他是很重要的。从此以后,他成了我的朋友,他的友谊后来有许多次都是对我极有利的。
但是一个州长玩这种卑鄙的把戏,那样下流地欺骗一个可怜无知的孩子,我们又将如何理解呢!原来这是他的一个已经形成了的习惯,他想讨好大家,但又没有东西可以给人,所以他就给人希望。除此以外,他倒是一个聪明、懂事的人,文章写得不坏,对老百姓来说他是一个好州长,虽然对他的选民有产阶级来讲,他并不如此,因为他们的指令他有时候置之不理。我们有一些最好的立法是他规划的,并且是在他任期内通过的。
我和雷夫是不可分离的伴侣。我们一同寄宿在小不列颠,每周租金三先令六便士——这是我们当时所能支出的最高租金。雷夫找到了一些亲戚,但是他们很穷,无力协助他。这时他告诉我他想留在伦敦的意图,他说他一开头就没有回到费城去的意思。他没有带来钱财,他所能筹措的款项全部都用在船票上了。我身边有十五块西班牙币,所以,在他寻找工作的时候,有时他偶尔向我借一点去维持生活。他起初力图进入戏院,相信他自己适宜于充当演员。他向威尔克申请剧场工作,威尔克坦率地劝他别再在这种工作上转念头,因为他不可能在这方面有所成就。接着他向圣父街的一个出版商罗伯茨提议替他编一份像《旁观者报》一样的周报,他提出了一定的条件,但是罗伯茨不赞同这些条件。以后他就设法寻找作家助手的工作,替出版商或是法学院的律师们抄写,但是这方面他也找不到空缺。
我立即在帕麦的印刷铺里找到了工作。这是当时开设在巴士罗米巷的一家著名的印刷所,在这里我继续工作了近一年的时间。我工作相当勤勉,但是我把我工资的很大一部分化在与雷夫同去剧场和其他娱乐场所。我们一起把我的十五块钱都用完了,现在我们仅仅能够勉强糊口。他好像完全忘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而我也逐渐地忘了我跟李得小姐的约言。我只写给她过一封信,在那封信里我告诉她我大概一时不会回来。这是我一生中另一重大错误,假如我要重演一生,我愿意纠正这一错误。事实上,由于我们的开支,我一直没有钱支付我的旅费。
在帕麦的印刷所里,我被指定替胡拉斯顿的《自然的宗教》的第二版排字。因为他的理论有些地方在我看来没有充分的根据,所以我写了一篇短短的哲学论文批评这些理论。论文的题目是《论自由和必然,快乐与痛苦》。我把这篇论文献给我的朋友雷夫。我印刷了一些。这使得帕麦对我较为重视,以为我是一个有些聪明才能的年轻人,虽然对于这本小册子所包含的那些理论,他严肃地告诫我,他认为是十分讨厌的。印行这一小册子又是我的一个错误。当我住在小不列颠时,我结交了一个书商,叫做威尔考克,他的书铺就在我住处的隔壁。他拥有大量的旧书。当时流通图书馆还不存在,所以我们达成了协议,我出一笔合理的费用,数目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可以借阅他的任何书籍。我把这看作是莫大的便利,因此我就尽量地利用它。
我的小册子不知通过某种方式被一个叫做赖英斯的外科医生看到了,他是一本叫做《人类判断的不谬性》的作者,因此我们就相识了。他很重视我,常常来看我,同我讨论这类问题,带我到一家在契泼赛的一条某某巷里叫做荷恩斯的淡啤酒店里去,把我介绍给《蜜蜂的童话》的作者曼得维博士,他在那家酒店里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因为他是一个十分幽默风趣的伙伴,所以他成了这个俱乐部的灵魂。赖英斯也替我介绍了在巴脱生咖啡馆的宾柏顿博士。宾柏顿答应早晚替我找一个机会见见爱瑟·牛顿爵士。我是极想有这样的一个机缘的,但是这件事从未实现。
我从美洲带来了几件珍品,其中最主要的是一个用石棉制成的荷包,这个荷包要用火来洗涤。汉斯·司隆爵士听到了这件事,就来看我,邀请我到他在泼鲁姆斯保利广场的府上去,在那里他给我看了他所搜集的全部珍品,并劝我把荷包出让给他,使他能把它收入他的珍藏。为此,他慷慨地付给我一笔很高的代价。
有一个年轻的女帽商人住在我们的寄宿舍里,我想她在修道院街有一家铺子,她受过贵族式的教育,通情达理,举止活泼,谈吐很风趣。在晚间雷夫读剧本给她听,他们逐渐地亲昵起来了。她搬到另外的一个寄宿舍去,雷夫也随她同去。他们同居了一些时候,但是由于他仍然失业,而她的收入又不足维持他俩和她孩子的生活,所以他就决心离开伦敦去试做乡村教师。他认为他自己很有资格做教师,因为他的字迹清秀而又擅长算术和簿记。但是他认为这是一种跟他不相称的下贱职业,他深信他在将来会飞黄腾达,到了那时候他会不愿意人家知道他过去曾经干过这样卑微的工作。
所以他改换他的姓氏。为了表示对我尊敬起见,他冒称我的姓。因为不久我接到他的求信,告诉我他住在一个小村庄里(我想是柏克夏),在那里他教十一二个男孩读本和算术,每周薪金六便士,要我照顾T夫人,希望我写信给他,上面写明寄给那地方的教师富兰克林先生。
他继续不断地来信,寄来他当时正在写的一首史诗的冗长的实例,要我批评和指正。这些我不时地都照办了,但是我却劝阻他继续写诗。那时候杨的一篇《讽刺诗》刚发表了,我抄写了一大部分,寄给他,这首诗鲜明地指出那些毫无希望地追逐诗神的人的愚行,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无用。诗稿不断地在每封信里寄来。
同时T夫人由于他的关系失去了她的朋友和生意,常常因此而穷困潦倒,常常叫我去,向我借贷一点多余的钱以救燃眉之急。慢慢地我喜欢与她来往了,由于这时候我不受宗教的约束,同时利用她对我的依赖,我竟试图与她发生关系(又一错误),但是她正当地表示了愤怒,拒绝了我,并且把我的行为通知了雷夫。这就使我们绝了交。当他回到伦敦时,他让我知道他认为我已经勾销了一切过去我对他的恩惠。这样我知道我永远不能希望他偿还我借给他或是替他垫付的款项了。
但是在当时,这还无关紧要,因为他完全没有能力来还债,而且失去了他的友谊以后,我倒发现我解除了一个重负。这时我开始想预先积蓄一点钱了。为了得到较优越的职位,我离开了帕麦,到林肯协会广场的瓦茨印刷所去,这是一家规模更大的印刷所。我在这里继续工作直到我离开伦敦时为止。
当我初进入这家印刷铺时,我开始在印刷机旁工作,因为我以为我缺少我在美洲所习惯的那种体力锻炼。在美洲印刷工作跟排字工作是不分开的。我只喝水,其他工人,约有五十名,都是酒鬼。遇必要时,我能够两手各提着一版铅字上下楼梯,其他工人需要两只手捧着一版铅字。从这个和其他的实例中,他们看见了这个“喝水的美洲人”,因为他们这样称呼我,倒比喝浓啤酒的他们自己来得强壮有力,他们感到惊奇。在我们印刷所里经常有一个啤酒店的小厮替工人们送酒。跟我在同一架印刷机上工作的一个朋友每天在早餐前要喝一品脱啤酒,吃早餐时跟着面包和乳饼喝一品脱,在早餐和午餐之间喝一品脱,吃中饭时一品脱,下午六时左右一品脱,当工作完毕时又一品脱,我以为这是一种极可恶的习惯,但是他认为,为了使得他在工作时有力气,他必须喝强烈的啤酒。我设法使他相信啤酒所能产生的体力只能与制造啤酒所用的溶解在水中的谷物或大麦粉成正比例,价值一便士的面包所含的粉比一夸尔的啤酒还多。因此,假如他吃一便士的面包和一品脱的水。他所得的力气多于喝一夸尔的啤酒。但是他还是继续喝啤酒,每星期六夜里要从他的工资中为那泥浆水支付出四五先令。这种费用我倒是没有的,这样这些可怜的家伙永远使他们自己处于从属地位。
几星期之后瓦茨要我到排字房去了,所以我离开了印刷工人。排字工人却要我重新付一笔陋规或是一笔五先令的酒费。我认为这是一种敲诈,因为我在下面印刷房里已经付过了。老板也是这样想法,不许我付这笔钱。我坚持了二三个礼拜,因此被认为是一个被驱逐出会籍的人,他们私下对我作了许多小小的恶作剧,假如我稍稍出去一忽儿,他们把我的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