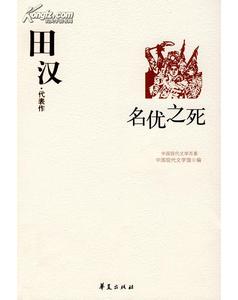矛盾文学奖提名 周大新:第二十幕-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倒也是。只这把女儿卖人做童养媳的事,名声终不好听,好歹我们也是有点产业的人家。
失小保大是古理!只要我们把机器买回来,机房兴旺起来,让尚吉利大机房的丝绸再称起霸王,国内国外的客商不断涌到咱尚家门前,哪个于尚家名声有好处?再说,到那时有钱了,把女儿赎回来也不是不可,她今年不是才六岁?
那就——
达志回了一下头,远远地又看一眼贴有启事的那棵树。
回到家,达志蹲在锅台前喝顺儿给他盛的包谷糁稀粥时,双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身旁的女儿,六岁的小绫正拿着一个旧梭子玩,她把那梭子放在一块木板上,左右两只小手把它来回扔,显然是学娘平日在机上的动作,她玩得十分专注,根本没注意到爹的目光。
“小绫,”达志停了喝粥,声有些发抖地喊,“想吃糖人么?”
“想!”小绫抬起那双极像达志的眼睛,意外而惊喜地答。她还特别看了一眼娘,小脸因为高兴而变得通红。
“给,拿钱去大门西边刘爷爷的摊子前自己买。”达志从衣袋里摸出一张小票,向女儿递去。
“他爹,不年不节的,给她买糖做啥?”顺儿在一旁低声阻止。
达志没有理会顺儿的话,聪明的小绫大约怕娘的阻止能够生效,从爹的手上拿过钱便向门外跑,边跑边撒一路笑。
“银子,够了么?”顺儿从锅上拿了一个红薯面饼,边递给丈夫边轻了声问。
达志摇了摇头,低下眼喝粥,呼噜噜,喝得很响,好像在跟稀粥赌气。
“还有法子么?”顺儿仍低低地问。
达志停止喝粥,目光缩回到粥碗沿上,弱了声答:“万良街明伦巷有一家,想娶一六岁童媳,允官银四十五两。”
“这与咱家有何相干?”顺儿不解地问,“他家——”但是陡地,她双眸极高地一跳,满脸罩上了惊慌,“你是说小绫——?”
达志的目光缩回眼眶,木木蹲在那里。
“不,不!”顺儿突然扑通一声跪到了达志面前,“不能卖她,她太小,要卖就卖我吧!卖我吧!看在我进了尚家从没求你的份上,答应我吧!她长大了好给咱尚家织绸缎,我反正是个残疾人,活长活短都没大用处,再说,我身上红的已有年把总是来得断断续续,恐怕也已经不能生了,求你留下个闺女,日后你老了她也好给你端汤送药,卖了我吧……”她扑上去摇了下丈夫的胳膊,达志手中的粥碗啷一声落到了地上,稀粥即刻在地上蛇一样分头爬开。
达志没动,也没吭,仍木然蹲在那里。
屋里只有顺儿的低声啜泣。
“买到了,买到了,大糖人!”大门那儿传来了小绫喜极了的叫声。
“起来吧,她回来了。”达志低微地说了一句,伸手把烂碗拣开。
顺儿强抑住啜泣,站起了身。
“爹,看,买来了,大糖人!”小绫这时举着糖人已奔进了门,达志勉力在脸上浮一丝笑说:“买来了就快吃吧。”
“爹,你先吃,来,你咬糖人这只胳膊,咬,咬呀!”小绫把糖人举到了达志嘴前。
“爹不吃,你吃吧。”达志去推女儿的手。
“咬,咬呀!甜得很哩!”小绫硬把那糖人朝达志嘴里塞去。
达志只好轻轻地咬了一点。
“甜吗?”小绫忽闪着眼睛问。
“甜。”达志几乎是哽咽着答出这个字,当小绫转身向娘身边跑时,两滴豆大的泪珠猛蹿出他的眼眶,急切地向地上坠去……
8
周大新
云纬的手轻轻在那两匹绸缎上抚着,这上边印着达志的指纹,摸着绸缎就有一种触住了他手指的感觉。回到家以后,云纬一直在为头晌对达志的那种态度后悔,不该那样刺他、骂他、噎呛他,他活得也不轻快呀!他那额头上,竟已满是皱纹了,他今年多大?二十八吧?二十八的男人脸上不该有那么多横纹!而且他是那样瘦,眼窝有点陷,颧骨凸了出来;他像是也没睡好,眼泡显出虚肿,左眼里有三道血丝;还有,他的衣襟上的扣子有一个没有扣上,可见他忙;他有几个娃儿了,两个?三个?……
“夫人,你的贴身衣裳。”草绒捧着几件叠好的内衣推门进来。
云纬闻声,急忙把脸上的那层因遐想而起的柔和隐起,换上了平日的那副冷峻。
草绒经过那次事件,虽然人仍有些憔悴,但精神显然已恢复过来,仍如往常那样快嘴快语,一见头晌买的那两匹绸缎摆在夫人的梳妆台上,就开口问:“夫人是想剪裁么?要不我去叫魏家缝纫铺的老大来,给你剪件旗袍,你头晌在王府山没看到,肖家夫人和陈家小姐穿那旗袍,多漂亮!像你这腰身,穿旗袍定能——”
“好了,去忙别的吧。”云纬淡声说道。她如今已把草绒母女重新要回身边,她不容许晋金存再把她们关起来,为此,她还同他吵了一架。她知道,晋金存虽然答应让草绒母女回到自己身边,但她们母女并没真正离开危险,每天晚上,都有兵在院里埋伏,以准备诱捕来救这母女的栗温保和他的手下人。
草绒出去了,暮色越见变浓,屋里又恢复了静。云纬没有点灯,仍坐在那儿,微闭了眼,让手在那绸缎上轻轻移动。这儿该是他的指印了吧?当初他去验查我织的绸缎,手指常在绸缎上触摸,那时他的指头是那样嫩长浑圆,而如今,竟满是茧了……
“咋不点灯?”伴随着嗵的一记踢门声,晋金存进了屋。云纬哦了一声,假装着打了个哈欠说:“嗨呀,我坐着坐着,竟打盹睡过去了。”边说边就擦亮火柴点上蜡烛。
“把这个给下人拿去煎煎。”晋金存把一摞纸包放到云纬手上,“一次一包。”
“啥东西?”云纬眉头一皱。
“桐柏知县送来的,一种涩精固肾的药食,每次煎一包,说是从朱元璋的《御药秘方》里弄来的,喝了立竿见影!”晋金存笑道。
“这不是蜻蜓么?”云纬打开一包,鼻子鄙夷地耸起。像所有贪色纵欲过度的男人一样,晋金存也已不得不朝那个专门折磨男人的深渊里栽去,他害怕在那个深渊里扑腾,他急切地想抓住深渊壁上所有可以抓住的东西。这些天,他不断地从外边弄些这药那药来。可惜没有一样有效,他害怕恐慌极了,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哪怕是渊壁上的一棵草他也要抓住试试。对此,云纬一直在冷眼看着。
“对,对,就是蜻蜓,”晋金存急忙点头,“这药食的名称就叫‘蜻蜓汤’,每包蜻蜓四只,锁阳、肉苁蓉中药各三钱,做法是将蜻蜓去翅,微炒,加入锁阳、肉苁蓉一同煎汤。《名送别录》书上载:蜻蜓味甘,性微凉无毒,可以强阴止精;《日华子本草》上说:蜻蜓壮阳,暖水脏。我估计会有效果!”
云纬将一个讥笑隐入眼底,拿起一包药出门交待草绒去煎。
“唉,如今烦心的事实在太多!”云纬又进来时,晋金存点燃了水烟袋,边吸边叹。
“还有啥事值得你叹气?”云纬又把鼻子不屑地耸起。
“嗨,你是不知哇,如今反叛朝廷的人实在太多,防不胜防呀!日他奶奶,后晌在知府那里听说,一个叫胡鄂公的同盟会会员,在保定成立共和会,入会的竟有三千多人,他们表面上说宗旨是发展实业,实际上是要推翻大清江山!他们是孙中山的人呐……”
云纬没再应声,她又把目光移向那两匹绸缎,用手轻轻抚触着它们。
草绒把“蜻蜓汤”煎好了,双手捧着送进来,晋金存迫不及待地起身接过,趁热哈着气响亮地喝着,边喝边吧唧着嘴唇。云纬在一旁厌恶地把嘴角撇撇,她听到这种喝汤的声音就有些肉麻,为了分神,她拿起一本书,凑到灯前去看。
那种响亮的喝汤声停下不久,云纬眼前的蜡烛突然被晋金存一下子吹灭了。
“做啥?”云纬不高兴地扭过脸。
“甭看了,咱们睡吧!”晋金存在黑暗中笑着。
“这么早就睡?天才黑。”云纬恨恨地把手中的书一推。
“嘿嘿,我想试试这蜻蜓汤的效力。”晋金存嬉笑着抓住了云纬的手。
云纬的牙立刻咬起,她努力把一句怒骂压灭在唇内。
杂种!
一切都是老一套。云纬仰躺在那里,在黑暗中瞪了眼,冷冷看着他在自己身上忙乎,但最终还是瞎忙,当他失败之后噢地叫一声“天哪!”滚到一边趴那里捶着枕头时,云纬唇上浮出一丝冰冷的笑意。杂种,老天爷还是有眼!
“看来,我这身子和大清朝的江山一样,要完了!”晋金存终于平静下来之后,坐起身拿过镶银水烟袋,边吸边叹了一句。
云纬没有应声,只把两眼望向黑暗中的屋顶。
“连南阳城里也有人想反叛,”晋金存仍在自言自语,“今后晌把左营的一个千总杀了,妈的,砍了他的头看他还能反?”
云纬依旧没吭声,只是伸手拉过被子,盖上自己那赤裸的身子。
“保江山可以杀人,可要保我的身子咋着办?说呀,咋着办?”晋金存边叫边猛扯掉云纬身上的被子,“你为啥不说话?你是不是在暗暗高兴?”
云纬闭上眼睛,呼吸平稳而安恬,照旧没有应声。赤裸的身子在窗外挤进来的星光里显出一个淡白的轮廓。
“这么好的东西,老子竟不能享用!”他边忿忿地说边抓紧云纬的一只乳房狠劲向上提着、攥着,似乎存心要把云纬弄疼,见云纬仍然无声,便又去抓拧云纬的臀部。
“我竟然不能享用!”他还在咬了牙说。
云纬白色的身子一动不动,房里再无别的动静。
夜,正无声无息地向深处潜行……
街面上市声喧嚷,这又是一个热闹的集日。轿 ? 不时要吆喝让路才能往前走,但云纬无心去看轿外的街景,只是在轿子的轻微颠簸中,默默翻着刚从府立中学堂图书室借来的那本《镜花缘》,一心想让自己尽快沉入到书里去。
如今,只有读书能让云纬觉出活在这世上还有一点意思。隔一段日子,她总要来这学堂的图书室里借本书,读完,再来换。云纬小时就识字,到了晋府以后,府内设有家馆,专门请了一位五十开外的老塾师,起先是给几位前房夫人生的女儿讲授;云纬的儿子承银五岁之后,便主要是给承银讲了。老塾师讲的内容,除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龙文鞭影》、《幼学琼林》之外,还有四书五经。云纬起初是因心中苦痛想找排遣,继是感到新奇,再是要照应儿子,便常到家馆里走动听讲,渐渐地,竟成了家馆中成绩最好的学生。
小轿在街道一侧缓缓移动,书页在云纬手中慢慢翻着,一阵尖利的孩子的哭叫声就在这时扑进轿中:“放我回家——”那声音里含着无限的惊恐和哀求,云纬隔了轿帘缝往外看,只见前方不远处有一男子背着个五六岁的女孩向这边走,那女孩正在背上死命挣扎着叫:“放我回家——我不跟你走——你放开——”
“唔——”那男子身后跟着的一个女人此时突然上前,用手捂了那女孩的嘴,女孩的叫声顿时变成了含混的“唔”,小脸憋得通红,身子仍在挣扎。
这男女肯定不是这孩子的爹娘,可他们强背这孩子做啥?会不会是白日横抢拐卖?如今这世道拐卖女孩的可是不少!“停轿!”云纬向轿礪叫了一声,同时隔帘对随轿走在一边的草绒说:“去,问问那背孩子的男人,那小姑娘是从哪儿背来的?”片刻后,草绒跑回来回答:“那男人姓董,说女孩是尚吉利掌柜尚达志的女儿,他用四十五两银子买了做童养媳的。”
“尚达志的女儿?”云纬一惊。
“我看这像是假话,尚吉利的掌柜还能卖女儿去当童养媳?前些日子我们不是还在王府山见他卖绸缎,光他那一天卖得的钱就不少,他会缺四十五两银子?”草绒飞快地说着自己的见解。
云纬心中一动:就是,尚达志眼下还没有穷到卖闺女的地步吧?莫不是这对男女趁尚家大人忙活的当儿,把孩子偷拐了来?这事不能不管!她转对草绒:“去,叫他们别走,让他们跟我们一块去尚吉利问问清楚!”
草绒跑到那对已走到轿后的男女身边说了,那男女先是不愿理睬,后看见云纬轿上的那个“晋”字,才不得不过来。女孩见背她的人往回走了,立时停了哭和挣扎。
“夫人,这孩子确是我们花四十五两银子买的,这里有字据!”那男的走到轿旁,高了声对轿中的云纬说,同时去怀里摸出一张纸。
“我不看什么字据,字据谁都可以假造,你跟我们走一趟,咱们当面问清楚!”云纬厉声说。
“好的,好的。”那男人只得点头,跟在轿后走。
小轿在尚吉利大机房门前停下之后,云纬让轿礪们看住那对男女,自己和草绒向院门走去。看见那块写有尚吉利大机房的牌匾,走近那道又高又厚的枣木门坎,云纬的心陡然觉出一股疼痛,一种类乎沸油溅上皮肤而起的那种灼痛。在这一刹那,当年和达志相拥在一处说起的关于这个院子的那些话又一齐在耳边响起。“你将是尚家大院的女主人!”这是达志那些话语中让她记得最清的一句。噢,女主人!
她默默地用目光打量院中的东西:那块立着的怪形石头,一架拆开来正在修的老织机,一把放在院中的木椅,几只正在地上觅食的鸡……当年,即将成为尚家媳妇的她,曾多少次在梦里走进这个院子,那时候她对这个院子怀有怎样甜蜜的想象,她曾想象着在每个早晨,睡在达志身边的她,都要第一个起床,扫地、喂鸡、做饭、上织机;她曾想象在那些星斗满天的晚饭后,她揽着孩子,和达志一块坐在这院子里,轻轻地给孩子讲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可这些想象终究只是想象,没有一桩变成真的。今天,我是以一个与尚家完全不相干的身份走进来的。
一阵酸悲攫住了她的心,这是一种手上东西被生生夺走而起的那种酸悲,此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