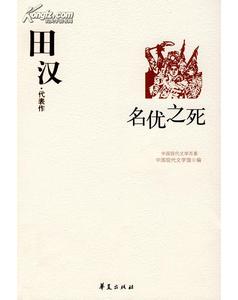矛盾文学奖提名 周大新:第二十幕-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晋金存,你这个狐狸!你的圈套玩得还真行,你派人打入我的内部给了我假情报,想把爷们一网打尽,手可真狠!这次让你占了上风,可你甭高兴得太早,爷们早晚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这次欠我十三条人命、三十一条腿和二十二只胳膊!这些账爷都在给你记着!……
草绒、枝子,我的亲人,这次让你们受了惊吓吃了苦头。你们冒着砍头的危险救了我和民军,这份恩情我永不会忘!你们咬咬牙再坚持一段日子,我一定要把你们母女救出来!前半辈子我欠你们的太多,后半辈子我一定要还上!我要让你们享尽荣华富贵!……
不远处的营棚里传来一阵挺响的喧哗,把温保的默想冲断。“你骂呀,骂呀……”“饶了我,饶了我……”断续的话语飘过来,仿佛还杂有哭音。
“啥子事?”温保不高兴地问门口的保镖。
“那边三队的几个弟兄在揍一个老头,那老头八成是一个坏货!”
“唔?”温保闻言踱出门,向三队的营棚看去,果然见一个老头正跪地求饶,几个兵在踢他,另有一群兵或站或蹲地在那里笑。
他便大步向那边走去。兵们见温保过来,都起身停住笑;那嘴角被打出血的老头看见温保,猜出他是头头,忙又朝他跪下作揖叫道:“饶了我,饶了我,我不该骂不该骂……”
“咋回事?”温保低沉地问显然刚才动手打过老头的兵。
“俺刚才从他的房后过,见他种的几沟萝卜挺好,便拔了两个,就两个,萝卜都不大,嗨,叫他看见了,他就日亲尻娘的骂开了,我一气,就叫了几个弟兄过去,把他弄过来揍了几下,我要让他知道咱民军的厉害!”一个粗矮的兵说得理直气壮。
“你起来!”温保这当儿朝那老头轻声说道,“你刚才咋样骂的他,再骂他一遍我听听!”
“不,不敢,我刚才是心疼萝卜还没长成,我真混,我不该——”
“不!你该骂!”温保突然高了声叫:“你应该再骂他一遍!”
那老头一惊,兵们也都怔住。那个拔萝卜的兵开始着慌。
“骂,大伯,你现在再骂他一遍!我给你撑腰!我看谁敢再动你一根汗毛!”温保走到老头身边鼓励道。
那老头不知所以地慌慌倒退着双脚:“不,不,我不骂……”
“既然你不骂,那我就替你骂了!”温保猛然转脸瞪着那个拔萝卜的兵,咬了牙骂道:“畜生!你才从农民中出来几天,可也学会欺负农民了?!你不知道农民种个萝卜要费多少艰难?那萝卜没长成你就拔下来吃你就不觉得良心不安?狗东西,骂你几句你竟敢把人捉来踢打,你的胆量可真大!你出来干民军是为了啥?就是为了吊打农民?就是为了欺负这个差不多跟你爹一样大年纪的农民?我日你个八辈先人,老子就是农民,你欺负他就是欺负我!日你奶奶,大清皇帝和他的那些贪官污吏欺负我们农民还不够,还要再受你欺负?!我日你——”
“大哥!”一声低低的招呼打断了栗温保的怒骂,他回头一看,见是派出去多天的肖四汗水淋淋地站在一旁,才强抑住恼怒,朝直直站在四周的那些民军士兵们叫道:“今后我要再见到有谁敢欺负农民,我就崩了他!”……
“咋样?”一进三有堂,温保便迫不及待地问。
“你交待俺们办的两桩事都有了着落。”肖四边答边用碗舀了门后水缸里的凉水猛喝,“先说和同盟会联络的事,俺们通过老七的弟弟,和南阳府公立中学堂的一个姓罗的老师接上了头,这罗老师也是同盟会的头头,他答应和咱们联合起来干,里应外合夺下南阳城,不过他说要找时机,不能贸然动手,具体时间再和咱们联系。”
“好!”温保高兴地拍了一下膝盖。和同盟会联络是那次失败后他的动议。因为那次失败后不久,报纸上出现了同盟会也在组织暴动的消息,这使他心里一动:既然同盟会也同大清不共戴天,咱何不同他们联合起来干?于是就要肖四进城暗中联络,他听说过同盟会在全国各地都有人。果然,联络上了!
“弄洋枪的事,”肖四得意地笑笑,“也成了,十二支,是通过南阳镇总兵谢宝胜的小舅子买的,那小子贪钱,我们给了他一些‘白的’,他就给送到了客栈,后来我们把枪分装在两个木箱里,转移到了小柱他远房叔叔卓远家里,那卓远如今改做了南阳师范传习所学监,一般不会有人去他那里搜查,我们对卓远也没说真情,只说箱里装了点贵重东西,先寄存到他家里。俺们打算过几天,生个法子再把枪弄回来。”
“行,四弟!”温保砸一下肖四的肩膀,拳头里攥满高兴,“只要有了洋枪,咱跟他们干心里就不慌了,娘的,真不明白,洋人咋会那样精,造出这等厉害的东西!”
“还有,我见着了草绒嫂子一回,她跟在那个叫云纬的夫人轿旁,我站在街边人群里看,嫂子胖瘦还行,就是气色不太好,脸有些苍白。我不敢过去搭话,她们轿后跟有衙役。”
“我日他晋金存的姐!”温保心里的怒气又被肖四这话燃起,跺了脚低叫,“早晚有一天,我要像拎兔子那样把晋金存拎到我手上!”
屋里静了一霎,骂过以后的温保,终于又渐渐平静下来,这才又含了关切地问:“见没见到弟妹?她和孩子咋样?”
“我趁黑夜回去过两回,他们母子还好。如今监视他们的人去得也不经常,我有心想把他们母子弄出来,可又担心晋金存对我爹妈两个老人下手,后想想也罢,就让他们先住那里,反正咱们早晚要打回去!”
“对!”栗温保挥拳在桌上砸了一下,“他们不会再苦多久了!……”
11
周大新
送走来南阳巡视的新任河南巡抚,晋金存一回到府中,便招来一个贴身随从不放心地问:“哎,你帮我想想,昨晚咱们去巡抚下榻处送礼时,巡抚见咱们把礼物呈上后,是不是笑了一下?”
“嗯,是笑了一下。”那随从回忆道,“他的两个嘴角这样一提。”随从学了学巡抚笑的样子。
“要是这样就好,昨晚灯有些暗,我没看清,我总觉得他没有笑,为这事我昨夜一夜没有睡好。”晋金存沉吟着说。
“他反正把礼物收下了。”随从仿佛对这笑与不笑没有看重。
“嗨,那你不懂!”晋金存摇了摇头,“他要是没笑,那就证明知府和总兵他们送的比咱的礼物要重,而且送在了咱的前面。送礼也有讲究,几个下官给一个上司送礼,你的礼不仅要重,而且要先送,先送,给人的印象深刻!人家送的礼重而且送在前边,你的就差不多等于白送!”
“噢,”随从点着头。
“你再回忆一遍,你确实看见巡抚大人笑了?”晋金存仍有些不放心。
“是的,我确实看见了。”那随从再次肯定地点头。
“好,这我就放心了。”晋金存靠回椅背吸了几口烟,顷刻,又扭过身问那下属:“从他的随从那里听到什么口风没?”
“听到一点,负责巡抚大人贴身侍卫的那个马官人,今早我在馆外碰见他,我俩寒暄几句后,他说:你们晋大人不错,是个可以干大事的料子!”
“他这样说了?”晋金存顿时双眼一亮,他扭头瞥了一眼坐在一旁翻书的云纬,目光里透着得意。但愿这次能真的感动巡抚给我做番安排,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于朝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好歹也侍奉过几任知府,轮也轮到我升了!晋升五品同知以后这几年,晋金存一直在盼着自己升任知府的消息,但盼来盼去,却终于没有盼到,心中不免焦急,时时都在暗暗祈祷官运来到,这次新任巡抚来南阳巡视,正是一个让上司认识赏识自己的机会,他自然不会放弃。
“嗯。”随从再次肯定。
“没有给那位马官人送点东西?”
“送了,一个独山玉香炉,一幅烙画立轴,裱好了的。”
“对,以后还要记住,凡上边来了客人,对他们的随从一定不要慢待,都要多少打点一下,可别小看他们,这些人能成事也能坏事,这些随从若觉你不错,对你有了好感,他就会常在主人面前说你好,就能帮助主人下定起用你的决心;若他们认为你孬,对你有了恶感,听说主人要起用你时,他就会填坏话,这样三填两填,就会把你的好事坏掉!没有听人说么?世上没有什么大事,所有的大事都是由小事引起的,有些人升官,很可能就是因为上司的老婆或身边侍从说了一句好话;连两国之间发生的战事,最初也可能就因为皇帝身边的一个什么妃子什么太监说了句什么话怂恿了皇帝!”晋金存低声开导着随从。
“噢,噢。”那随从连连点头。
“为买礼物总共花了多少钱?”晋金存吸两口烟后又问。
“三百多两。花的钱有点多了。”随从赔着小心。
“那倒没啥,”晋金存吐一口烟,“人生就是做买卖,有支有收,只要值得支出,就不要心疼,不过你们也可以想点办法,我听说尚吉利大机房最近买了机动织机,出货很多,赚钱不少,你可以让收税的他们去问问,好像使用机器也应该纳税的。”
“好的,好的。”随从很机伶地眨着眼睛。
“这事让我去吧。”一直默坐在一旁散漫翻书的云纬,这时突然开口。
“哦,你去?”差不多忘了云纬坐在一边的晋金存一怔。
“不就是讹他们家点银子嘛,我就说我要试穿他们家新出的绸缎,我看他们敢不给!”
“好,好,”晋金存眼睛一亮,“你们女人出面办这事更好一些,万一有人说起来,我就讲我不知道!”
云纬鼻子里哼了一声,慢慢转过身去……
看看暮色已经上来,云纬起身打开自己的那口樟木箱,从自己这些年积攒的体己银钱中,拿出了四个五十两的大锭,包在了一帕丝绢里——像大多数富人家的女人一样,云纬也已学会了攒体己钱。
这便算做是从尚吉利大机房弄来的!
后晌,她一听见晋金存要随从去尚吉利机房要税,心就倏然一缩,她知道这是变相的讹,她即刻就对晋金存生出一股更大的愤恨来。尚家的那点钱来得容易吗?那是用汗水、靠俭省,甚至是拿女儿的身子换来的呀!如今,有关尚家的两件事已经深深刻进了云纬的脑子里,一件是尚安业的下葬,那个老人为了省下一点钱,是用席片包住身子被埋进冰冷的土里的;一件是尚达志为弄到银子买织机卖了女儿,达志和女儿那天在泰古车糖公司店堂门口抱头相哭的场面,把云纬的心都揉碎了。对这两件事的记忆,使云纬心中原有的那股对尚家的气恨变得淡薄了。尚达志当初为了保住丝织祖业不和自己私奔的举动,在今天的云纬看来,仿佛也有可以理解的地方。而一旦她对尚家的气恨变淡,原先被她压在心底的对达志的爱就又翻了上来。现在,达志的举止行动,尚吉利机房的兴衰安危,又都在她的关注之中了,所以,她一听到晋金存要去尚吉利讹钱的话,就先气得打起哆嗦来。狗东西,你不动不摇,派人就要去把人家辛辛苦苦用汗水用眼泪积攒起来的钱拿走,这算什么道理?
可后晌云纬不敢多嘴,更不敢把自己心中的愤恨表现出来,她晓得晋金存要办的事谁也挡不住,她只有另想办法替达志把这个灾难挡开,于是便提出,自己替晋金存去尚吉利大机房弄钱。
达志,你放心,这个灾我既然知道了,就不会让它落到你的头上!
你安心做你的事吧!我真不明白你们尚家为什么会迷丝织迷得那样深,可你既然迷上了,你就迷吧……
她把那四个大锭包好往手袋里一塞,便出门吩咐轿礪:去尚吉利机房!
离着尚吉利还有百十步远,云纬便叫落轿,令轿礪站在原地等,自己一人向大门走去。尚家临街的店堂门也还没关,柜台上点着两根蜡烛,达志正一人借着烛光伏在柜台上算着什么帐目,云纬轻脚走进去,没有吭声,只是默然望着正聚精会神算帐的达志。
这十来年间,在这么近的距离上这么不受干扰无所顾忌地看达志,还是第一次。他显得瘦了;眼角已有了那么多鸡爪纹;左手背上有一道挺长的血痕,是什么时候划破的?衣服怎会这样破旧?左襟上撕破一个口子,右肩上有一大块污迹,是染印绸缎时溅上的颜料?头发显然很久没洗了,乱蓬蓬的。呵,达志,亏你还是个老板,你的日子怎会过成这样?……
达志大约是算完了一笔账目,推开算盘抬起了头,他看见站在柜台外的云纬,惊得“哦”了一声,他根本想不到她会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来到他的店里。
云纬无声地站在那儿,双眼定在他身上。
达志被云纬的目光望得有些慌张,上次见面时她的那顿怒骂还记忆犹新,他惶恐得一时不知该咋着开口,他在慌乱中想到的头一句话是:“你是来买绸缎的吗?”
这句问话一响,原本笼在云纬脸上的那层柔和又倏然隐走。她本来等待的是一句关切的、亲切的问候或招呼,未料还是一句纯生意的用语:你是来买绸缎的吗?
尚达志,你这个完全被绸缎遮住眼的东西!你以为所有来你尚家的人都是为了绸缎?就不会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想你、思念你、帮助你?!在你和你爹眼里,除了丝织除了绸缎宝贵之外,再没有别的宝贵东西了?!真是鬼迷了心窍!像你们这样一生只想着一个目标的怪物真是少有!一心想着织出“霸王绸”,狗东西,但愿你们永远织不出!织不出!……
云纬的牙又咬了起来,原有的那股对尚家的气恨又在心里翻腾开来,只听她冷然说道:“是的,尚老板,我是来买绸缎的!不过我要买一种特别的绸缎,一种用你女儿和未婚妻的眼泪浸过的绸缎!那种绸缎穿着舒服!”
这句话像一颗子弹一样准确地命中了达志的胸脯,只见他的身子摇晃了一下,他似乎想辩说几句,嘴动了动,但声音却被双唇关住了。他最后只是无限痛楚地看了云纬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