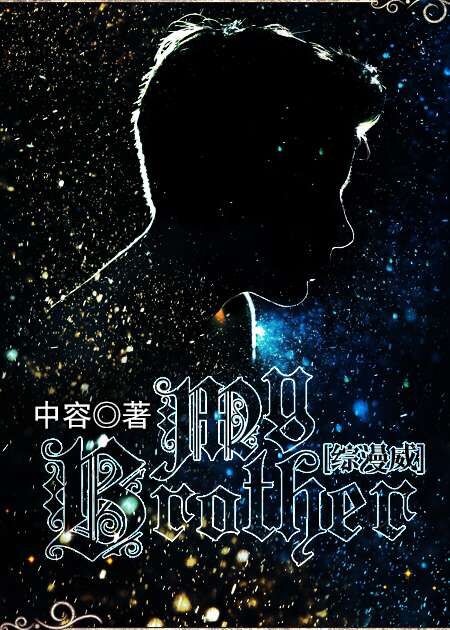刺心 by 清杏-第5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慕容也不辩,只道:“若他今日威胁是,他手里的那人是宫主,又会怎样?”
“笑话!”宁二嗤道,“颜帮主有个能力?”
慕容笑,飘身离去。
宁二焦躁,咬嘴唇,冲颜回道:“算狠。次不成,还有下次!”
群雄竟眼睁睁地让他们离去,许是因为宁二的愤,许是因为颜回的冷,许是因为其他。
宁二身影消失无妄山小径刹那,他回头,飘来眼,万般心思,嫉恨有,轻蔑有,……是对死敌的眼神。
他在面前暴露他的势力——那群黑衣杀手,与刺杀景容和同样身段的杀手。
他,不怕吗?
宁二,真是胆大的人啊。
章一零四 与谁携手
清灯古佛不得近,道与谁携手归
原来人生真如戏。
场闹剧。
曲终人散。
只是无妄山场戏,没有曲,日隐于无妄山第七峰后,人就散。
当年江湖血案,凶手不是,无妄山上群雄没理由为难,无论与情欢宫主是何关系。何况是在无妄僧门,是在玄业大师庇护下,何况还有颜回。他们也该知道,今日若不是颜回,无妄山想来已可能是血流成河,尸骨如山。
重重人影经过身边,投来的目光应有尽有,只是多奇怪,探讨,少怨愤。
宁二和慕容的人退去,颜回的人也随之自动消失。
无数下山人流中,没动。
他站在身边,安静。
不介意下山群雄的形形色色目光,却介意他的沉默。
“不回去?”
“色晚。”他笑笑,“不知无妄僧门可否让颜回借宿宿?”他在炫耀他的身法吗,炫耀几年他的功力进步吗?眨眼间,竟拦在玄业大师前头。
玄业大师并没回答他的话,反朝看来,端详几秒,摇摇头,又看向颜回,宣声佛号即离去。
他闪,和他相隔的距离远,下山的人开始不断从和他之间走过。
看见他在笑,看着笑。
“吃闭门羹吧?”丝窃喜,心情不由轻松些。
他摇头,唇尾翘起自信笑:“大师答应。”人有时就喜欢自作多情。
色是晚,么多人都急着下山,他怎不随他们去?
山寺后灯火亮起,幽幽曳曳。
瞧得久生恍惚,仿佛和他之间流逝的不只是下山的群雄,流逝着很多,很多。
时疲惫,错开与他对视的目光,径自走向敞开的山门。
人,下山。的
,入寺。
群下山的人流中抹逆流的人影,辉映着空山的孤寂。
还有抹流动身影中静止的人。
无数擦肩而过的人。
手暖,被握住,是另只手。
停住。
他不声不响,修长的手指根根契入五指的空隙,然后握紧,交缠。
有人影停下来,有脚步驻足,有人在观望。
看向他。
他没看,他的视线穿过山门,似乎望进重重寺宇深处,唇含抹笑,恍如春阳风絮,似在无人之地,闲然地握着的手,走向无妄僧门。
“颜。”低低唤他声。
他依旧没看,依旧看着前方,但笑容亮些。
相握的手突然被捏紧,丝生疼。他听到,走向无妄僧门的脚步却依旧不紧不慢。
众目睽睽之下,十指依旧交缠。
……
新月如芽,弯弯。
无妄山后的山谷,瀑布入潭声,因夜的静谧,显得纯澈,磅礴水声听上去竟觉脆生生。
“虚无果真在那?”
“他直留守情欢宫,怎么可能飞到相隔万里远的宁帮。”颜回的本正经。
“骗他们?”
颜回笑开,如湖面入石子的圆晕,漾起。
原来他也会骗人。
“从来不骗宁儿。”他收起笑。
“真的?”
“真的。”的
“嗯,若有机会,会杀他?”他,不是别人。
“若有机会,宁儿,会阻止?”他不答反问。
他的眸与夜色,看不清心思。
无数设想闪而过,但也只是设想罢。若真面对那刻,嗯,“不知道。”声音再轻,轰鸣瀑流却掩盖不。
“离开情欢宫前,记得问,为什么不还手,不能。宁儿,如今,也是个答案。”他目光幽沉。
纵使他杀?在心里问。
“他为什么不选择的左臂?”
颜回突然不吭声。
看着他,轻轻笑,无声。
水声淙淙。
如同大战场后精力尽失,无力斜靠着山壁。浸润瀑水的山壁,层苔厚湿,湿凉侵衫,冷如心底。
还是夏,不该般寒,却真真实实地在颤抖,心底在颤抖。
“宁儿,”他看着,眸色比厚重山色还平静,“回去吧。”
回去?回哪里去?
“已经离开。”失神着轻喃,“在里,每暮鼓晨钟,青灯古佛,颜,知道,心从来没有如此平静过。”
风来,瀑布过山崖激荡起的水迷蒙,溅得满身。“可以在里,在瀑下坐,有时甚至几几夜。想也许在里样过辈子,也是好的……”
迎面细湿突然不再,身子被拉入人怀里:“答应的。”他的声音响起在脖颈后。
“颜,——”
“答应过的!”异常坚定声,紧接着耳朵痛,被咬住。
长安别院吗?不由笑:“还敢跟佛祖抢人不成?”
“嗯。”耳朵疼,有热流滴下,淡淡腥味。他真学狠。
闪电,紧接着轰隆巨雷。刚还有如钩新月,什么时候变得?
“颜,佛祖生气。”取笑。
“只要不生气。”他笑,笑容隐着伤。眸间的冷不知何时散,只剩水水的,晶亮两汪柔波。
他的唇摸索上的,辗转,绵绵,动人。
衣衫互缠,身上的湿转移,爬到他身上,分的冷。
他的身体,温暖,让人心安。
……
秋,来的不知不觉。
几层细雨几回风,长安别院的梨树林已开始漫飞叶。
比起很久以前的春夜梨花泪,淡秋梨林飞叶也是景致。
湿泥沾叶,即使是好景致,也宁愿窝在长安别院角,看檐前烟雨,也不愿迈出步,让雨沾得半衫湿,让泥污脚。
秋雨,心中它是清冷。
不想再沾清冷,或许是清冷惯,或许是怕。在它到不的地方看着它,很安全。
卵石铺就的花间小径,轻快脚步声,并着轻松小调。刚束发的少年,不是他,是冷儿。
“啊呀,公子,怎地又穿得么少。”冷儿抱着卷轴,腾出只手,拉进屋,“秋雨渗人的。”他抱怨着,脸红扑扑的,眉间洋溢的喜意遮掩不住。”
“昨夜听得雨声,今早耐不住,出来心急些,忘披衣。瞧高兴的,今莫非有什么喜事?”
“少爷叫给公子送来个。”冷儿喜滋滋地放下怀里卷轴,铺在桌上展开来。
淡墨,笔勾勒。
檐前听雨图。的
人薄衫,伫立檐下阶前细雨。旧时窗檐旧时色,只人前不远,几丛他朝客新色,怒放。
那线条仿佛不是用墨,而是用尽腔心思,看得人眼灼灼。
画的正是刚才情景,可墨色虽新,却是干的。
他左手不仅剑术比右手精妙,连作画也如此,真是多才的人呐。
“少爷难道会未卜先知?”冷儿惊叹,“能料到公子在檐前听雨,竟事先画下来?”
笑,指腹细细描摹线条,若线条有温度,该是热的,灼烧的热。
“冷儿,颜除叫拿画过来,可还有什么?”
“差忘。”冷儿叫道,“光顾着看画,忘记告诉公子,少爷叫公子去雁楼。”
长安别院,不仅有梨花林,还有雁池。临池而建楼,与梨林隔池相忘,名雁楼。
又送画又邀约上雁楼,他,想玩什么?
拾级而上。
窗前桌人,桌上两杯盏,墙边叠酒。
“冷儿会未卜先知呢。”笑着坐于他对面,瞥向冷儿怀里的画,“孩子,欢喜画,也用不着抱着画来回跑呐。”
冷儿嘻嘻笑,画搁桌上,像怕颜回责罚似的,溜烟跑下雁楼。
“自下秋雨开始,几乎未亮就那样静静站在檐下。”他的声音如浸过多雨水的竹叶,沉甸甸的,“雨已经下好几。”
“可能不太习惯雨。”道,提起酒壶为他,为自己各斟杯。
“宁儿,”他把住送往口里的酒,按到桌上也没有放开,“不开心。若是不喜欢,,嗯,不用勉强——”
瞧着他蹙在起的眉,眸色平静无波,可的声音为何颤呢?
“傻瓜,怎会勉强自己!”拨开他的手,仰首饮杯。空杯顿桌,“颜,从来不会勉强自己,信!”
“好几没笑。”他看着,突然冒出句。
现在不是正在笑吗?颜回,不出来就不安心?
“颜,要记得,愿意与在起。只是不喜欢秋雨,不喜欢长安别院的秋雨。”
不是勉强,不是因为昔日承诺,颜,是愿意。
因为愿意,所以请不要担心。
“嗯?”
“很久以前,在里,正梨花含泪,看见过剑分尸,看见过和位叫挽情的子,嗯。在里,曾想杀,而也险先杀。”笑,“下着细雨的秋很让人感伤,不喜欢感伤。”
他才真正笑起:“们以后去别的地方。”
“那好极。”笑着饮尽杯。
颜,其实,不仅仅是些。其实,些无关紧要。
“避几,就是为躲在旁,偷窥画副画?”乜斜他,再次斟满杯。
“就在对面书房内,只是宁儿眼里只有秋雨,没有。”他似嗔非嗔。
“倒像是的错?”绕过自己面前满酒,自他手里夺来他喝半杯的,舌滑缠故他刚碰过的地方,含住杯沿,觑着他笑,见他双黑眸渐渐失去清明,不由唇齿把住杯,不用手地仰饮尽。
“宁儿,知道在做什么?”他的声音哑。
“什么?”装傻,把桌上自己的那杯满酒移到他面前,“今什么日子,大早得竟约喝酒?”
他就着的手喝完:“生日。”
“好巧啊。”手指反缠上他食指,笑道,“今也生日啊。”
“宁儿,”他的呼吸急促些,“嗯,不要样。”
承认是在挑逗他,只不过是捉弄性质,但好像小估他的反应。抽出手,“从今以后,就和同年同月同日生。”
“比大两年,而且的生日在春。”颜回失笑,“才喝两三杯,莫非喝醉?”
“不是。而且也很久很久没醉过。”自那年下无心山以后就再也没有醉过,“颜,从此跟同年同月同日生。”
他么聪明,该知道的意思。
果然他的眸亮起,把玩着空杯,那空杯在他手心转三两圈,他开口:“就些?”
“后面句也要?”笑问。
“贪心。”他叹气。
“曾经,就是头发白,也会在梨花满林的长安别院等。如今不用等到白发,们已经在里。”执起他的手,“辈子,本就是偷得余生,只怕活不很久。若拉上起走,会不安的。”
“不定有人心甘情愿呢。”他的黑眸闪啊闪的。
“做什么?殉情?”笑,“殉情的都傻瓜。那么聪明的,可别犯傻。”
他不语,他的眼睛却在话。
“不是吧?不知道只喜欢聪明人的?”
“当然,是聪明人。”他眨眨眼,状甚开心。
“哈哈,那喝酒,祝们的生日快乐!”
酒杯碰在起,声清脆。他用的是喝过的,用的是他的。
们努力地在笑,笑声下避讳着某些东西。
“还有琴?”不经意看见角落里事物,“的?”
“很久以前的。”
走过去:“果然,有些灰尘呢。”拂去那些,朝他笑,“会剑会画,还会琴,人才啊,可以吗?”请君曲,邀请他同时刻意盯着他右袖。
沉默三两秒,“嗯。”他起身。
笑得愈发欢。
在他身后,看他的手按在弦上,顿顿,开始有音流出。他的脸沉肃。
单手成调不成曲,但知道他奏的是什么。
很多年前,那座山,无裳满山。晨风怡人,或斜阳半山,或清月初起,有人偶会在无裳花丛中拨弄琴弦,旖旎的音调消融无裳花香间。
“曲春光无限。”那年某个月华清辉的夜,被曲勾起某种欲望,道。
“自然,它叫情欢。”那人含笑,“宁儿想学吗?”
那样的清辉朗月,那样的无裳花开,那样的人,那样的笑,唇舌顿觉干,不禁咽口口水,头早已脱离控制,不知多少下。
那人笑的愈发勾人。
坐在他与琴间,背与他的胸只隔衣衫。他的手覆上的,忘记撩拨弦时的感觉,只记得他手指的温润,他的呼吸,染上无裳花香的呼吸。
不敢回头,怕回头,怕对上他的视线就乱。
即使不看他,也知道,他的唇角定衔着抹笑,醉人的笑。
贪恋那种感觉,只和他在起时才练,平时是没心思弹。谁知日子久,般无心竟也学会。
次,竟和他直坐到晓,琴声时断时续,夜未消,那时刚勉强学会。
旭日冉冉,他似有感而发:“宁儿,首情欢,下只两个人会。”不知是被光线刺激,还是笑的开心,他眯起眼着话。
“吗?”
他笑,搂紧。
……
纵使曲不成调,纵使音不全,也知道他弹的是情欢。
缓缓坐于他身后,手穿过他的腰。左手停于他腰际,紧扣。琴面上出现两只手,只他的,只的。
他颤,拨弦的手未乱半分。两只来自不同主人的手,心有灵犀般拨弄着同曲调——情欢。
情欢本是催|情曲,沉浸于浓艳绮丽曲调,时春梦。
曲声消歇,雁楼的春色还在继续。
舌攀上他的脖颈,沿肩头路徘徊而下。双手摊入他的衣,在前面开路。
他,坐在前面,在怀里。
“宁儿,在里?”
“回屋忍得住?反正院子也就们三人,冷儿就算看到也会当作没看到。”
“那,委屈。”他笑得狡猾。
“委屈?”口舌松开,手还继续。“啊,——”冷不防被颜回按往桌上,跟着他倾身下来,唇已相触。
“今生日,该侍候吧?”调笑,着想反身,无奈两只手竟抵不过他只手的力,功力失,果然成手无缚鸡之力人?
“今也是生日。”他笑的意味深长,手解着衣衫带子。
难道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那们互相侍候。”嘿嘿笑着,率先咬住他的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