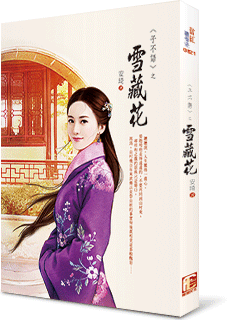含笑花(下)-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云漫天草草点了个头,一只脚刚跨进门槛,谈怀虚又叫住了他。等他回过身来,谈怀虚挥手喝退了两个守门的家丁,然后道:“有件事不知该不该告诉你。令尊他……他……”
云漫天霍然转过身,颤声道:“他……他怎么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谈怀虚见他面色煞白,知道他误会了自己意思,忙解释道:“今日黄昏时嘉炎派人送来一封信,说是他与令尊已经离开苏州了,却没说去哪里,听他语气似乎以后都不会再回来了。”
竟真的走了么?云漫天茫茫然伸出手扶住了门框。眼里悲愤连着绝望,绝望又连着荒凉。经过了昨夜,他只当自己已经能放下,可是此刻他的心却还是那么地痛。
谈怀虚见他神色不对,伸手扶住了他的肩,感觉到他浑身冰凉,不由吃了一惊。情不自禁之下他伸手抱住了云漫天,急声道:“你没事罢?怎么身子这么冷?”见他神情苦涩茫然,忍不住轻叹了一声,柔声道:“漫天,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父母总是要离开我们的,即便不是生离,有朝一日还是会死别……就象是我。你若是觉得孤单,我……我总是愿意陪着你的……”然而在云漫天失神的眸子里,他看见了自己小小的影子,有些惶惶然的。这让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也是惶惶然的,象是掉进了水里,说得再大声,对方还是听不清楚。
“……陪我?”云漫天茫然重复了一句。他抬起头望着谈怀虚,面上露出迷惘之色。
谈怀虚突然受到了鼓舞,他下意识提高了声音,喊着道:“是的!一直陪你!”抱着云漫天的手也紧了紧。
云漫天身躯一震,忽然推开了他。他抚了抚自己的额头,垂首了片刻后他重新抬起头来。只是一刹那他的痛苦便风过无痕,面上只余下一派雪白淡定。
“对不起,我失态了。”他说,对着谈怀虚道了声告辞,转身进了院门里。有一扇门在谈怀虚面前关上了——咫尺瞬间成了天涯。
云漫天上了楼。见南宫寒潇卧房的门大开着,里面死寂无声,他觉得有些纳闷——平时南宫寒潇的房门总是紧闭着的,不让人进去,因为那本来是南宫忘忧的卧室。
云漫天缓步走了进去。大概是南宫寒潇每日里都打扫的缘故,房间里一如既往的整洁。只是最近雨水多,总感觉到有些霉味飘散在空气里。站在那里,隐隐觉得那黄霉要在皮肤上滋长起来,透着腐败死亡的气息,趁他不留神就钻进他的骨髓里。
窗外有月光,房间里地上浮着一层白霜,有些支离破碎的影子散在其间。云漫天缓步踏过地上的影影绰绰,那影子便飘在了他的身上。他走到床边停下脚步,不知怎地,眼前突然浮现出南宫忘忧惨白的脸,鬓前还插着那朵干枯的山茶花,颤巍巍地。这让他突然有些胆怯了。
床上被褥铺得很整齐,里侧的枕头旁放着一尺见方朱红色描金盒,在白色的被褥上似是一滩血。云漫天盯着木盒看了半晌,突然明白了里面装的是什么。他不由打了一个寒战,刚想退出去,南宫寒潇却一脚踏进门来。
“你在我房间里干什么?”他闷喝了一声,阴沉中带着些许愠怒。云漫天见他反应如此激烈,索性在床边坐了下来,冷笑着道:“没事就不能进来么?”
南宫寒潇一个箭步冲到床边,喝道:“出去!”
云漫天偏头恶狠狠瞪了他一眼,他索性往床上一躺,挑衅道:“今晚我就睡在这里了,你又能怎样?”
南宫寒潇愣了一下,忽然露出一个讽刺的笑容,道:“你倒是食髓知味,难道刚才谈怀虚没有满足你么?既然这样索性请他进来好了,我们来个三人同乐。”
云漫天顿时勃然大怒,怒声吼道:“混帐!你以为所有人都象你这般下流么?……”
“可笑之极!”南宫寒潇面带讥讽地打断他,冷笑着道:“我是下流没错,可谈怀虚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四年前他就和男人睡过了!”
云漫天吃了一惊,下意识反驳道:“你胡说!”
“我胡说?”南宫寒潇面上浮现出一丝嘲弄,眯着眼盯着他道:“哼!你可知道他高潮时叫的是谁的名字?小天……小天……”
“够了!”云漫天“腾”地站起身来,恼羞成怒地向南宫寒潇吼道:“你嫉妒他!你自己堕落下流,也巴不得别人与你一般污秽下贱!”
“我污秽?我污秽你还不是巴巴送上门让我搞!”一瞥间隐约看见云漫天脖子上有些红色斑点,一时理智全失,口不择言地叫道:“你才是贱货!人尽可夫!”
云漫天狠命甩了南宫寒潇一个巴掌,他气得浑身颤抖,指着南宫寒潇吼道:“你再说!你再说!再说我杀了你!”
南宫寒潇擦了擦唇角的血痕,他怒目瞪视了云漫天片刻,突然一把推开他,急急奔出了房门。
云漫天望着南宫寒潇身形消失之处,脑中乱哄哄作响,就是秋达心从前拿他试药让他跪下求饶也没有让他觉得有这般屈辱过。不经意看见床上的木盒,暗红色的一片在他眼前晃动着,脑中一根弦突然断了,他踉踉跄跄走了过去……
南宫寒潇怒气冲冲跑下了楼梯,心中一团火熊熊燃烧着,烧得他慌不择路。他一路冲到后院的小亭子里,一拳捶向了亭中的石桌,
发了一通脾气后他稍冷静了些。“我为什么要生气?我本来就处处都不如谈怀虚,我本来就恨不得他和我一样肮脏。云漫天说得半点没错,我还生气什么呢?”
这时突然回想起谈怀虚搂着云漫天站在院外的情景,他心里猛然一惊:“难道我是在嫉妒?可是我为何要嫉妒?”有一个念头象瘟疫一般在他脑中迅速蔓延开来,惊惶之下他出了一身冷汗,“不可能!这决不可能!——我一定是因为最近伤心过度,所以精神有些脆弱。”可是他还是觉得惊惶。
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在亭子的栏杆上坐了下来。含笑阁临着一个小小的荷花池而建,一眼望过去,荷叶田田,随风摇曳。漫天的星光落在了池中,随着水波轻轻摇曳,象是火树银花的倒影,只是那璀璨不过是一夜之间罢了。
不经意间看见荷花池上二楼窗户处现出一个人影,他想起那扇窗户属于自己的卧房,本能地吃了一惊。他下意识冲到了池边,看见云漫天站在窗口,半边面容浸在溶溶月色里,另一面却被黑暗所湮没,看不清全貌,隐约有些阴森之感。
(二十二)
南宫寒潇正要出声喝问,忽看见云漫天右手一扬,将一个四方的东西朝楼下荷花池里扔了下来。那四方物在半空中便失去了盖子,经风一吹,青白色的灰便飘散在了苍凉淡黄的月色里,幽幽荡荡,飘飘忽忽,似有似无……
“二叔——”南宫寒潇忽地撕心裂肺喊了一声,用尽全力扑进水里。没等他跑到池心,那四方物便扑一声闷响掉进了水里,水花四溅,击碎了那一场火树银花的幻梦。
“不要!——”南宫寒潇发了疯似地喊叫着,用尽全力冲过去捞起了那四方物——一个朱红色描金的盒子。盒子里盛了不少水,混着残余的灰,有些浑浊,沿着盒子边缘的细缝往下滴滴答答,似乎很快便要流尽。头顶有轻风吹过,涩涩的扑在南宫寒潇的面上,隐约带着灰尘的味道,他只恨自己不能即刻也变成灰,好一起随风而去。
“不要……二叔……不要走……”南宫寒潇喃喃喊着,突然歇斯底里大吼了一声,抱着盒子朝池子的边沿撞了过去,直撞得头破血流。血顺着他的额头一股股流下,在他俊美绝伦的面上划出一条条红痕,象是鬼脸一般可怖。血水与池水混融在了一起,一丝丝地浮在水面上,开出朵朵凄艳的水花,然而只是瞬间又湮灭了。
撕心的痛中他茫然四顾,四周焦黑零落,无论他怎么弥补,都无法再挽回什么。一种崭新的绝望袭上心头——他的世界已被毁得一干二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茫然抬头朝窗口望去,云漫天依然站在那里,原本清雅的容貌此刻却显得有些狰狞,一身青衣荡在月光下,象是午夜的幽魂。见南宫寒潇看着自己,他微扬起下巴,朝南宫寒潇露出了一个冷森森的笑容,道:“真是有趣。”
南宫寒潇赤目嘶吼了一声,抱着残破的盒子跌跌撞撞冲进了楼里。一进房间他立即冲过去对着云漫天拳打脚踢起来,状若疯狂。云漫天并不反抗,自始至终他一直闭着眼睛,面上带着讥诮迷茫的神情。
打了一阵后南宫寒潇突然停了下来,看着躺在地上浑身是血的云漫天,他的眼神渐渐凄迷。就算打死了他又能怎样?——他心中突然前所未有的悲哀与绝望。一颗心象是一间四处漏雨的破屋子,补了这个缺口,却又立即发现了许多新的。
转过身,望着桌上残破的骨灰盒,他恍惚觉得自己在一个惶惶的梦里。可是这场梦那么长,再没有结束的一天了——他不由自主跪在地上抱着头失声痛哭起来,肆无忌惮地,撕心裂肺地——他再也不怕任何的耻笑与蔑视了,他什么都不怕了!
云漫天捂着心口急喘着气躺在地上,他有些惶惑地看着完全失控的南宫寒潇,脑中却是白茫茫的一片。他颓然闭上眼睛,黑暗里那哭声渐渐淡去,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耳边隐约回响着:“我愿意陪着你——假如这能使你好过些……”
假如这能使你好过些……云漫天猛然睁开眼睛:他竟希望自己好过一些!突然有东西在他心里噼里啪啦炸开了来,炸得他满腹满心都是生疼,他捂着心口的手也不禁更紧了些。无边无际的悔恨向他袭来,渐渐侵入了他的四肢、五脏、六腑,最后在他的心口处汇聚,沉沉压在了上面,让他不能呼吸。
窗外的淡黄的月突然沉下去了,带走了他眼前最后的光,头顶的黑暗一步步朝他逼近,仿佛瞬间就要将他吞噬。
他突然觉得疲惫,于是闭上了眼睛,恍惚中生命点点滴滴从他身体里流逝,他无力阻拦,也不愿阻拦——终于他晕厥了过去。
谈怀虚站在院子里看着上下翻飞舞剑的南宫寒潇,除了惊叹再无别的想法。三日前他把南宫嘉炎留下的《惊雷剑法》剑谱给了南宫寒潇,想不到短短的时间里南宫寒潇便已如此得心应手。假如不是由于南宫寒潇缺乏实战经验,惊雷剑法又对内力要求极高,谈怀虚怀疑自己并无十分把握能胜过他。
原来南宫世家的惊雷剑法与藏花阁的藏花剑法其实同出一脉,百年前两家的祖先同门学艺,在祖师爷的指点下各自创造了一套剑法。惊雷剑法与藏花剑法一刚一柔,相生相克,两家祖先虽有比试,却一直未能决出胜负。此后百年因为两家交好,惟恐比武伤了和气,因此再没有正式切磋过。到底哪个剑法更胜一筹一直还是个谜。
一束剑光飞速射向一颗大树,随即“砰”一声巨响,大树拦腰截断,向院中小亭直直压了过去。噼里啪啦一阵脆响后那小亭便被砸了个稀巴烂。
谈怀虚面上微显出惋惜之色,他朝收了剑的南宫寒潇看了过去,见他满面的戾气,心里不由吃了一惊。他缓缓走了过去,扬声道:“你的剑术如今在江湖中已是一流。我已无能力再指导你了。”因在细风湖那夜他答应了云漫天指导南宫寒潇剑法,所以此刻他有此一说。
南宫寒潇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似乎对此根本不以为意。他顺手拿过一块布拭了拭手中的剑,那不过是一把极普通的剑,可是他的神情却异常认真,仿佛他手中拿着的是一把上古利器。剑锋反射出夕阳昏黄的光,在他面上一晃一晃的,带着凄绝的瑰丽,象是用血染成的一片晕红。
见云漫天走了过来,谈怀虚忙迎了上去,带笑道:“寒潇果然是奇才。我看我已没有能力再给他建议。”
云漫天有些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两人站在树下闲闲聊着,云漫天的眼睛却不时衔着南宫寒潇。自那夜他摔了南宫忘忧的骨灰之后,南宫寒潇便再没有与他说过一句话,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云漫天虽有些烦闷,却也不打算去打破僵局。见这几日南宫寒潇发了狠地练剑,显然他并未放弃替南宫忘忧报仇的打算,看来两人之间的交易应该仍然有效。这样也就够了,反正再过半月多自己便要毒发身亡,又何必再去费那个心思?
然而他虽然想得豁达,事实上却不能自己地感到郁烦焦躁。他不由自主地留意着南宫寒潇的一举一动,只可惜从南宫寒潇的眼中他看不到任何情绪,甚至连憎恨也没有一丝。这让他感觉自己象是走在一条漆黑的通道里,随时可能有暗器飞出来射中他,然而也有可能自始至终什么都没有——他不过是白担了惊吓。
云漫天这边厢目光不离南宫寒潇,却不知谈怀虚也一直在打量着他。细风湖那夜次日的清晨,谈怀虚发现云漫天浑身是伤躺在床上,追问他原因他说是起夜时脚没踩稳摔下了楼梯。谈怀虚当然不信,因为他身上的伤痕明显是被人打出来的,可是他并没有追问——他又何须追问?含笑阁里只住着两人,答案是明摆着的。他虽然不知道南宫寒潇为何会把云漫天打成这样,可是这个结果既然对他没有害处,他也就姑且不去追究了。
这时阿凉惊惶失措地冲了进来,气喘吁吁地嚷着道:“不好了!不好了!两个小少爷中了毒!夫人请云道长赶快去看看!”
三人疾步赶到谈思晴的住处时,月落与沉星正口吐着白沫并排躺在床上。谈思晴坐在床沿上哀哀哭着,旁边南宫夫人正劝着她。一看见云漫天进来谈思晴立即扑了上来,抓着他的手臂哭着道:“道长你快救救我的孩子!”
谈怀虚见她情绪失控,忙拉住她低声安慰。云漫天走到床边试了试脉搏,又翻了翻孪生子的眼皮,沉吟了片刻后道:“他们中的毒叫‘夺魂引’……”
“可有办法治?”谈思晴哽咽着追问道,见云漫天面露难色,又哭着哀求道:“道长你想想办法,你一定有办法的!”
云漫天淡然看了她一眼,道:“想要救治他们只有一个法子,便是分别取下他们父母三分之一的心脏,加上适量砒霜做药引让他们服下。”顿了顿,又补充道:“若是其中那个关节出了问题,他们便会被砒霜毒死。”
(二十三)
谈思晴一听,娇容立时灰如土色。南宫寒潇的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