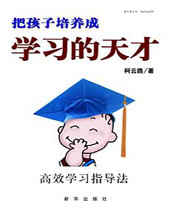第一辑像孩子一样说真话(节选)-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这方面的能力呢?还是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兴趣?我觉得很可能是后者,或者主要是后者。兴趣没有了,能力当然也就谈不上。所以我觉得,中国目前这种西方研究的貌似的进步的趋势里面,其实包含着严重的退步。
葛红兵:我想中国人对西方的意识受这样一些目的的驱使,第一个是功利主义的目的,就是“拿来主义”的想法,觉得什么东西可以被我们马上拿来,为我们所用,我们就去研究它,什么东西能够更快的改变我们,我们就去研究它。所以物质层面的东西,比如科技,民主,我们都很容易去切近它。第二个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什么东西妨碍了我们,比如人与自然的观念,人的基本权力的观念,我们就去反对它。我们受这两种趋向的影响特别深。总的来说,中国人没有脱离自身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考量去看待西方的习惯。
…
中国人的“西方学”(2)
…
郜元宝:上一次在你们学校开的会议上发生一场关于“911”事件的争论,其实这场争论并不是围绕怎样评价这个事件。他们谈论问题的切入点完全是政治的,似乎他们对美国的政治了如指掌。我觉得这是建立在他们自身对世界的政治兴趣上的。后来有几个年轻学者试图从民族文化和宗教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很快就遭到大多数人粗暴的否定。他们觉得这种事情完全没有宗教因素,他们说,你们受了亨廷顿和萨伊德的骗了。他们说这些话时是很有把握的。从这件小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知识实际上有的受到国内政治的驱动,有的是受到世界范围的政治关系的驱动。他就认准自己看待事情的角度是惟一正确的,惟一靠近真实的角度。
…
封闭的视角/开放的视角
…
葛红兵:从这个角度,总的说来我觉得中国当代学者看待世界的方式比鲁迅、周作人他们要封闭一些。比如周作人在讲泰戈尔来华的时候,因为泰戈尔是个东方主义者,周作人就对中国政府和中国诗界、创作界对泰戈尔来华的热烈欢迎表示了反感,他说中国应该欢迎,甚至不希望泰戈尔访华。他的这种态度是抱着对西方世界更为开放的心态来对待的。今天的学者会反过来,像萨伊德的观点在中国的流行,包括《日本可以说不》这种书在中国的流行和宣传,西方人崇拜东方的报道等等,这种心态完全和鲁迅、周作人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总的来说,当代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心态更加狭隘一些。
王宏图:这一点也是和几十年的政治教育的惯性有关。我们谈了那么多美国,宣传的焦点集中到美国,但即使我们到过美国的人对美国的了解又有多少?实际上要了解一个民族,文学还是最有力的途经。比如说我们不能从布什,奥尔布莱特这样的人身上去了解美国人,而应该从梭罗、马克?吐温、福克纳、海明威和弗罗斯特等人的身上去了解。其实美国人的精神世界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得要复杂的多,他们表面上热情,而内心比较冷,对待工作有清教徒似的热情,同时怀有作为上帝选民的优越感。我们不能把那些政客看成美国人的代表。
郜元宝:中国知识分子在认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的时候,如果撇开宗教的角度,文学的角度,艺术的角度,仅仅集中在政治经济角度上的话,我们也许只会认识到一个没有美国人的美国,或者是只有克林顿的美国,只有布什的美国,只有比尔盖茨的美国。(葛红兵:还有好莱坞的美国)这种事情其实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而且正在发生。
…
西方人看中国
…
郜元宝:当代知识分子在了解西方时,心态比“五四”那一代人更狭窄,宏图刚才也说到灵魂的问题,文学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确可以追问下去,就是说,今天的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比起西方人包括韩国、日本对中国人的了解,哪个更深刻?我作为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有时候会接触到美国人不管在什么样的“东方学”的研究机构里制造出的大量的关于中国的学术产品,还有日本人在整个大东亚的政策下面不断生产出很多关于中国的东西。你只要稍微一接触,就会感到惊讶:他们怎么这么了解中国。日本人在侵华之前对东三省进而扩大到整个内地,从历史、地理、人文的角度对具体的活着的中国人的认识已经丰富到连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的程度。美国更是如此,而且这种认识是多方面的。美国有费正清的系统,但也有别的系统,在不同的学术传统、学术体制下面对中国的认识拼合在一起,对中国的认识相对来说就全面得多。日本也是这样的,它不仅有在侵华这个总的构思下开展对中国的研究,我觉得至少日本的许多学者,他们研究中国是极其严肃,极其认真的,也极其刻苦的。现代文学界公认的鲁迅研究,最好的是竹内好,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从这件事来讲,我们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从实用的角度来讲不够,从灵魂的、人文的角度来讲更不够。我们能够说我们在开放、在认识西方吗?
我们在中国能不能找到一个为世界所公认的或者为我们中国自己所佩服的一个外国文学的研究专家,一个外国哲学的研究专家,或者外国的某一个人物的研究专家?他形成一个学派,形成一个从他身上看美国,看德国,看英国的窗口?我们没有找到。
葛红兵:的确没有。
王宏图:中国人在这方面以前有一点心理萎缩,总觉得我们是外国人,不如人家。其实不是这样的。语言是一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比如我们的中文当然要比竹内好的好,但他的鲁迅研究却不是现在的哪个中国人可以达到的。实际上我们对做学问的理解还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
葛红兵:我觉得主要是我们在这方面的视野还没有打开,像我接触一个学者叫罗宾逊,专门研究中国北京。他就在北京拜访了一百多个人,其中甚至包括朱文、邱华栋这样的客居北京的作家,认为他们可以代表对北京这个城市的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此外,他还拜访了很多画家,在他们的画当中看北京。如果我们去研究北京的话,根本就不会在乎朱文这些人对北京的看法,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微不足道的,或者可以作为反面教材。所以说我们视野的狭窄导致了我们看外国问题的狭窄。
王宏图:我觉得这个学问出不来和这几十年对知识界的摧残很有关系。在过去,比如清朝的戴震研究楚辞,当时他很穷,我们的生活条件比他要好多了,但我们现在就搞不出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固然有很多迂腐的东西,但他们有一股气,而且那种完整的生活世界是有意义的。20世纪以后,意义世界破裂了,经过50年代的摧残元气大伤,到现在实际上还没恢复过来,且不说超拔的精神品格,连一般的精神品格都没有了。特别是90年代以后大学的管理方式,科研方式过分急功近利,让人完全变成一种功利性的动物,很难想象在这种情形之下会有真正触及灵魂的思考。
…
中国人看西方
…
郜元宝:从这个方面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过高的估计中国人对外在世界的兴趣。从积极的意义上姑且可以说他们是睁开眼睛看世界了,但如果他看世界不是看世界上其他人群的心,其他人民的灵魂,那么越看,境界就越小。因为他没有看到别人的心思是一个海洋,这样看出去的世界,还是封闭的。越是封闭越要看世界,越看世界越封闭,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种看世界不是打开他的眼光,而是使他更封闭。所以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游历了五大洲以后回到家里,思想反而变得比从前更加封闭。
葛红兵:现在看西方有两种封闭的模式,一种是把西方看得很丑陋。(王宏图:妖魔化西方。)另外一种封闭的模式就是把西方看得很高。(郜元宝:过于美好。)这实际上都是没有深入到西方的内里去的看的图式。当然可能那种“标准的”看,“本质的看”是不存在的。
郜元宝:从文学从艺术的角度,也就是从人心的角度,相对来说可以看得更真切一些。
葛红兵:所以我希望更多的翻译外国作品。
王宏图:90年代对外国文学的兴趣大大下降,外国文学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占的位置愈来愈低。
郜元宝:不仅仅是外国文学,我们本国的文学也是。
王宏图:从翻译书籍来讲,实用类的图书,比如经济,英语的比重越来越高。
葛红兵:30年代上海的《现代杂志》介绍了大量的欧美作品,包括鲁迅、茅盾都出过外国文学的专号,而90年代以后,我们对外国文学和艺术的关心降低了,比如小说,从前我们还有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关注,出现过卡夫卡热等等一系列外国文学的热潮。但今天却没有了,我们今天关心的是什么?(王宏图:诺贝尔奖)还有六千块钱一张票的我们听不懂的世界三大男高音的演唱会,我们有些研究者把这些看成是中国与世界同步了。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表面上是越来越繁荣了,实际上本质上的交流是越来越少了。
郜元宝:一部耗资几百万、几千万的歌剧给中国带来的实惠,其实远远不如一首诗的翻译或一本小说的翻译。但谁会承认这一点呢?这也解释了中国文学界对外国文学的淡漠。鲁迅写过一篇杂文《由聋而哑》,说我们中国人听不到外国人的心声,翻译不好他们的文学,就好像是一个聋子,而如果你是聋子的话,久而久之话就说不出自己的话来了,就变成了哑巴。在现在普遍的开放的时代,我们要警惕一种新的封闭,不要被表面的开放所欺骗,也许它是一种新的封闭,因为历史上有过这种经验。比如我们在现代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开放,可后来突然间封闭起来了,而且封闭得如此持久和突然。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