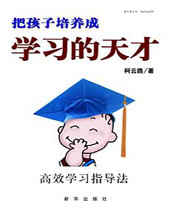第一辑像孩子一样说真话(节选)-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本身,比如他受到攻击时必须要反击。所以鲁迅在杂文的立场上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斗士。你们刚才说他的小说忽略艺术性,我觉得不是这样。像他的《出关》、《铸剑》,特别是《铸剑》,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他是一个极具想象力的人。他的小说中的艺术形象我觉得非常强,而且不是托附、熔铸在某一个形象上的,它给我们一个大形象。鲁迅在进行这种写作时把我们传统的对于小说的概念给搅混了。我一直觉得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不是一回事。我觉得鲁迅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更自由的,在进行杂文创作时是更被动的。在这种被动的立场上,鲁迅所存在的这种客观环境对产生鲁迅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一开始做革命者……
刘川鄂:所谓革命者通常是指他思想的革命性而已。
葛红兵:鲁迅不可能同任何地位比他高的人成为朋友。
刘川鄂:毛泽东欣赏鲁迅,我觉得他们有一点真的相通,即所谓硬骨头精神,对谁都不在乎,比如青年毛泽东二十来岁在长沙对自己精神意志的磨炼,后来在三十年代在同共产党高层的极左的领导人斗争期间,还包括了五十年代对苏联的斗争,毛泽东也有一种硬骨头精神。鲁迅也是这样:一个都不宽恕。
中国知识分子什么时候可以不谈鲁迅
葛红兵:二十世纪过去了,对鲁迅的梳理在学术界也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我昨天接到山东省一个国家级项目《多维视角中的鲁迅》的写作邀请。我想单从文学家的角度来认识鲁迅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如果仅仅只是从思想家的角度来认为鲁迅怕又有把鲁迅过分思想化了的倾向。鲁迅是一个谈不完的话题,英国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中国就有“说不尽的鲁迅”。中国知识分子什么时候开始不谈鲁迅,到底意味着一种进步还是意味着一种倒退?下一个世纪谈鲁迅还怎么谈?
刘川鄂:只要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没有完成,鲁迅的价值是永存的。鲁迅对传统文化“吃人”本质的理解是非常深入的。毛泽东读《资治通鉴》读到了秩序,读到了怎样治理国家;而鲁迅读《资治通鉴》读出传统文化“吃人”本质,仅仅这一个命题我认为鲁迅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人。如果每一个受过基本教育的知识分子都能领悟到鲁迅思想的价值,中国社会就真正进步了。鲁迅的价值肯定是永远存在的,但我们对鲁迅的理解上过分意识形态化。像三十年代鲁迅在左翼阵营中,尤其在鲁迅晚年,最后一两年生病中,那些别人替他写的,鲁迅自己签个名的文章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完全的鲁迅,我始终持一种怀疑态度。像冯雪峰、许广平的关于鲁迅晚年某些迎合意识形态的回忆录的真实性,我也持怀疑态度。
我们还应对长期以来神化鲁迅、加在鲁迅身上的光环给他一个本来的归位。因为鲁迅始终是在矛盾和寂寞中度过的。在20年代的“野草”时期,是个人与庸众、社会的矛盾,个人对社会庸众的清醒的否定,自己仍然没有力量反抗。而到了30年代他加入无产阶级文学阵营,他跟那些极左思维方式,那种惟我独尊的总管、霸王之间的矛盾,都是一般知道鲁迅的读者所不知的。而他评新月派是为国民党维持治安、说梁实秋是资本家的乏走狗、对他并不了解的极权的斯大林时代的过份肯定等等,都是应该向更年轻的一代阐明的。此外,鲁迅个人的价值观念的现代化与他生活方式的传统化也有很大的矛盾,比如他坚守个人主义,但他的那种“尊母情结”,孝道思想却很严重。思想上非常现代化、甚至有很多非理性倾向的鲁迅,在日常生活上是比较传统化的。
邓一光:他对正统体制的批判使他不得不倾向于另一种“背叛性”的体制,如“向左转”。实际上我感觉鲁迅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刘川鄂:但鲁迅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在如胡适对“新月派”“第三种人”的批评是所共知。鲁迅从他的青年时期到中老年时期始终对于人民、愚众、穷人的本位立场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说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鲁迅则更是民主主义的代表。
葛红兵:我现在倾向于把自由主义分为两种,一种是鲁迅式的绝对自由主义,它的核心观念是任个人;一种是相对自由主义,它的核心观念是民主。胡适是相对自由义的代表人物,他相信民主政体,所以他会在适当的时候拎起皮包去做国民党的外交大使;而鲁迅绝对不会相信民主政体,任何体制性力量他都是要反对的,他绝不会在任何一种政体中成为帮忙之人。
刘川鄂:鲁迅的不相信不是从理论上,而是从对现实生活的体察上来的。
…
钱钟书:被神话的“大师”(1)
…
葛红兵:钱钟书是一个横贯了现代和当代的学者、文学家。目前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什么“20世纪最伟大的学者”、“文化昆仑”,还有人创立了什么钱学。钱钟书也成了一尊神。他是通过学问而成神的绝少的几个人之一。评论一个文学家要看他在审美创造上对时代有没有独特的贡献,他有没有对一种语言的文学创作贡献出独特的什么图式。评论一个学者,则要看他在思想上对时代有没有做出独特的体系性的解释。从这个角度上讲,不论是对一个文学家还对一个思想家要求都是很高的。我想侧重于从思想角度来谈谈作为一个学者的钱钟书。学者有两类。一类是知识者,就是继承了人类以前的知识,然后传播知识,他自己虽丰富了知识大厦但没有奠定新的大厦。另一类,对世界有独特的解释体系,他们系统性地思考这个世界的始源问题,提出一种独特的、体系性的学说,因而称为建构性的思想家。钱钟书属于前者,他是知识大厦里的梳理人,又是一个传承人,但他没有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样一个人物在中国当代获得了这样高的地位和评价,从正面讲我们可以肯定钱在知识上所达到的成就,但从反面讲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荒芜。20世纪中国思想史没有对世界思想史,甚至中国思想史构成新的冲击,没有可以鼎足独立的人支撑起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大厦。在这种情况下,钱钟书的被高评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悲哀。
刘川鄂:有一句老话叫:八十年代出思想,九十年代出学问。钱钟书正是20世纪90年代被发掘出来的。此前他也很有名气,但他真正获得这么高的地位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是启蒙话语年代,像钱钟书这种学者型的人物大家不大注意。20世纪90年代,一是因为电视剧《围城》使作为文学家的钱钟书的知名度提高了,但另一方面主要是知识界、读书界给了钱钟书如此多的高评价。这些高评价表明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思想立场的某种放弃。因为20世纪90年代不光是钱钟书,还有吴宓、陈寅恪这样学者型的文人成了议论中心,兴奋点,这跟20世纪80年代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的那种学问跟日常世俗生活相隔得比较远,跟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直接批判也相隔较远。所以我觉得有两种文人:一种是思想型的文人,一种是学者型的文人。钱钟书是属于后者的。
邓一光:我对钱钟书读得不多,只读过《围城》、《谈艺录》、《管锥编》和少量随笔。我的老师非常推崇《谈艺录》,开过专题课,后来的作业也是它,但我觉得它就是梳理,很精制,没有把它当大师的作品来读。他的《围城》给我带来了阅读的快乐,我甚至觉得它和我后来读到的王小波的作品有相近之处,他对知识分子的形象化写照和理性批判在文学上是一个高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政治强权体系、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土壤、社会变化动荡不已的国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接受过西方文明思想和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他们与当下时代无法融合,他们难以突破自身的狭隘性,在钱钟书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读这部书的时候很早,是上高中的时候,它让我有一种怀疑,对知识分子的怀疑。
刘川鄂:作为一个作家钱钟书的东西并不多,一个短篇集一个散文集一个长篇。但他的写作态度我很欣赏。他散文的题目叫《写在人生边上》,甘居一个边缘人的角色。他的作品中没有很多浮躁的东西,没有那些外在的意识强加的东西,纯粹是作为一个写作的爱好者,他并没有意地把文学创作当成自己终身的职业,而是一种乐趣,所以他写起来非常从容,把他自己的智慧全部融入进去。而且他的《围城》在表现知识分子方面很独到。如果说鲁迅表现了中国农民的灵魂,张爱玲表现了中国三、四十年代都市男女的灵魂;钱钟书则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真相。当然这里的知识分子不是全部知识分子,而是那些比较卑微、自私、小聪明的知识分子。
葛红兵:从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讲,他在知识分子题材方面是有开拓,对知识分子的表现他是深刻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知识分子很少反思自身的立场和劣根性,钱钟书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他开始反思知识分子自身。《围城》在艺术上了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成就。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长河来说,钱钟书在文学的领域里可能还不能算一个大师――从量上讲他的创作不多,从质上讲,他毕竟没有创造一种独特的审美图式。今天我们把钱钟书看作一个大师主要是从学者的角度来讲。钱钟书身上附带了一个新人文神话。第一个是埋头读书的神话,他如何“一心只读圣贤书”,如何博闻广记;第二个是反流俗和虚名的神话,他如何“两耳不闻窗外事”,别人请他去开会,政府请他出席国宴,他如何拒绝参加等等。
钱钟书自己给自己造了这种神话,把自己搞成了一个埋头读书、同体制、同大众决裂的“学者典范”。这种神话本身我觉得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不会隐瞒他对时代的看法,他不会对这个现实的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不公、不平无动于衷,他不会对这个世界中丑陋的不合人性的东西视而不见,他不可能是鸵鸟,他对时代饱含热爱,对不公愤愤不平,对美好的止不住赞美。
…
钱钟书:被神话的“大师”(2)
…
想一想钱钟书在文革中做了什么?萨特说过:“在黑暗的时代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钱钟书,他反抗了吗?他躲在锅炉边看他的书――这是一种乌龟哲学。许多人在这个哲学里苟活,还以为自己伟大。
刘川鄂:中国知识分子参予社会无力,同流合污不甘,这就是钱钟书人格上的意义。
葛红兵:钱钟书给自己造出来的学者神话对当代学人不媚俗、不媚上,专心学术的精神的培养有一定意义,可能绝大多数人看到的钱钟书也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这个神话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也是一种麻痹。躲在故纸堆里生活,对时代沉默不是“龟缩哲学”吗?《写在人生边上》、《围城》都是很有体悟的,说明他对生活有敏锐的一面,但是解放后他为什么就失去了这些?他不关心这个时代吗?不,他关心这个时代,但他为什么不讲呢?肯定是有某种软弱的方面在主导他,文革吓破了他的胆子,这时他就过分强调他作为学者的一面,故意装作“两耳不闻窗外事”,这是他可悲的一方面。如果我们思考他强调自己埋头读书是想掩饰什么的话,那么钱钟书这个世纪的人文神话不像一开始我们所认识的那么高尚、伟大。在世纪之交人文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是什么,是写一部《管锥编》?是去研究钱学吗?我觉得这不是知识分子真正的出路,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他关注这个时代,但不向这个时代发言,他对这个时代一切都保持沉默,那么他能做什么样的学问?这很可疑。
刘川鄂:我觉得钱钟书这个神话主要不是他自己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病态的精神所致。20世纪90年代思想界的疲软,知识分子批评立场的放弃,启蒙精神的弱化都使钱钟书成了一个热门人物。“钱钟书热”是我们时代精神病态的一种体现。今天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其实有了更多的话语空间,也有更多亟待讨论的问题。如果把钱钟书神化,会有误导的可能,而这种误导往往是有的人所欢迎的。
葛红兵:是的,比之于尼采、萨特、海德格尔,一百个钱钟书又能算什么?
刘川鄂:回想中国历史上,思想最禁锢的年代往往是“学问”做得最出色的年代。这是知识分子一种放弃,转移的结果。所谓“康乾盛世”,清朝的考据学的兴盛都和知识分子放弃社会参予有关。这也是我们悲哀的一面。知识分子成了听话的、传话的工具,不仅出不了思想家,其实也出不了真正的学问家。这与整个社会政治体制、教育体制都有关。所以“钱钟书热”也是对新中国近50年的教育史、学术史的一个讽刺。
邓一光:就我的阅读范围,特别是到了当代以后,涉及到中国泛知识分子这个领域的文学读本只有贾平凹的《废都》较有意思。当然贾平凹的《废都》涉及的是文化人,不是知识分子。这两者有相通之处,就是他们有相当多的精神生活层面、文化生活层面以及边缘性姿态,承担着现实和精神上的双向压力和突围。《废都》把文化和文化人的终结归结到一个时代的终结上,写出了文化和文化人的无奈、颓废、堕落、消极和变异,面对文学,面对文化,更进一步面对知识阶层,只有妓女把肉体和崇敬一起奉献到祭坛上,这是极具批判意识的。物质化时代是一个新的革命时代,革命的对象之一是传统的文化和文化人,它们和他们必须接受身份和立场的改头换面,文化和文化人成了一个时代演变的标志。而《围城》的解剖在现代,它是对知识分子自身进行解剖,而且解剖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不是大动肝火,是把人物放在抗战的大后方,放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里进行那种聪明、幽默的小表演。我们对这种表演真的是无话可说,我们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