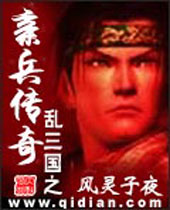花间辞倾国之新折桂令-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歌声丝丝缕缕伴着风声琴音飘了过来,听得人如痴如醉,心肠百转,全凝结于歌音之上了。
杜景之悄悄探头出去,想看看歌者的样子。
八角亭上,白纱轻扬,亭中放着一张琴几,一人席地而坐。案边的玉螭笼内焚着瑞脑,袅袅升出青烟,另一边搁着一只墨绿色的瓷瓶,瓶中斜插着一支白梅。素手纤纤拨弄着琴弦,一袭素色长袍,上绘着水墨樱花,式样不类其它宫服。发色乌黑,垂于腰际,只在末梢用根丝带束着,并无半支翠钿玉饰点缀。肤白胜雪,眉藏春山,没有半点铅华却让人觉得华贵清雅灼灼不能直视。
亭中之人唇边含着笑,双目却凝视着前方。杜景之顺着目光看去,白色的雪地里,一人正在舞剑。合着琴音,步走乾坤,翩若惊鸿,矫似游龙。剑尖带起无数雪花在身边舞成一片,除了明黄|色的衣袍和挽出的朵朵剑花,容貌也看不清楚。
未几,琴声嘎然,剑势也随之收回,雪尘片片坠入泥中。亭中之人含笑站起,将瓶中白梅执于手中,走到舞剑人的面前,伸手用袖子在那人额上轻抹了抹:“累不累?”声音低沉,让人听了极是受用。
“朕不累,到是你,天这么寒,当心冻了,瞧,手都凉了!”说着,把放在额上的手掬在自己手中,放在唇边呵着热气。
二人相视一笑,目光纠缠,仿佛天地之间只此二人一般。杜景之看着不觉痴了。正发愣时,突然见那亭中之人转身面向自己,美目一凛,口中叱道:“什么人?”
杜景之一惊,还未及反应,只觉得头上一紧,乌纱已经落到地上。
“父皇!母妃!”李崇义高声叫着,挥手从树后绕出。杜景之俯身捡起乌纱,硬纱已经陷下一块,那帽冠上方方正正嵌着一朵雪白的梅花,若是这梅花再低个三寸……杜景之吓出一身冷汗来。
定了定神,杜景之跟在李崇义身后,来到二人近前。
“微臣杜景之,磕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娘娘千岁千千岁!”杜景之低着头,伏下身去。
“免礼平身。”李朝旭抬手,示意杜景之起身。
“谢万岁!”杜景之起了身,抬起眼,正撞上樱妃那双莹动美目,杜景之连忙垂下眼。
“你就是义儿说的那个新科状元杜景之吗?”樱妃的声调有些奇异,但听李崇义说过她来自东瀛,杜景之也就不奇怪了。
“是微臣!”
“义儿从小顽劣,从来没听他夸过什么人。这回倒听他夸了你无数声,极是难得呢!”
“不错,连周侪也夸你才思敏捷,做事沉稳老到,应该是错不了的。”李朝旭看了看樱妃,柔声说道:“流樱,外面太冷了,咱们还是进屋里再说吧。”
樱妃点了点头。
第八章
和风阵阵,挟着青草的清香,在大开的窗户内外悠游穿梭。靠近窗台的书案上,沉重的乌木镇纸压着厚厚的书页,却压不住清风撩动页脚发出的沙沙响声。书案上摊开的雪白纸张上密密麻麻地布满工整的蝇头小楷,笔架上,一支湖笔孤独地横卧在青瓷烧就的山脊之上。
杜景之敲了敲酸麻的肩膀,揉了揉干涩的眼睛。不知不觉间,又熬过了一个漫长的不眠之夜。把身体的重量尽数托付给厚实的椅背,杜景之长吁了一口气。熬了这么多个夜晚,《国策论》总算告一段落。满意地把最后一张书稿压在黑色的镇纸下面,杜景之张开双臂,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
临着窗,可以看见窗外的柳树已经发出的青翠嫩芽,杜景之不觉怀念起家乡那满堤的绿柳来。不知是否为了照顾自己,在北方可不多见的柳树,居然在吟墨轩外随处可见。
今日自己不需要去紫辰宫,杜景之决定上床补眠。一手打着哈欠,一手拽着披在身上的外袍,杜景之晃动着酸软的身体向自己的寝榻而去。
“啊……啊……”门外突然传清脆稚嫩的声音,后面则是略显慌张的女子呼声。“等等,殿下,您别乱跑啊,当心摔着!”
杜景之回头,紧闭的房门被从外推开,一个极矮小的身影直直地扑了进来。
“非离殿下?”看着不到两岁的李非离被高高的门槛绊倒,杜景之惊出一身冷汗,困顿疲乏全都一扫而空。
李非离趴在地上,小手把身体撑了起来,先是四处张望,正打算自己爬起来,突然看到了一脸惊慌的杜景之,顿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杜景之把李非离抱起来,一边拍一边安抚:“乖,不痛不痛,殿下不哭,殿下是男子汉了,怎么可以动不动就哭呢?”
赶过来的嬷嬷正好看到,吓得“扑咚”一声跪倒在了地上:“奴婢,奴婢该死啊,没看好小殿下。”
“你起来吧,不碍事的,小孩子喜欢跑,摔倒也不全是你的责任。他没受伤就好了。”杜景之柔声唤那嬷嬷起来,又对李非离说,“殿下其实现在已经不疼了,对不对?”
李非离含着手指,看着杜景之轻轻点了点头。
“你看,这不是好了吗!”杜景之笑了笑,把怀中的李非离向嬷嬷递去,“好好看着他,别让他再摔着了。”
嬷嬷伸手要接,李非离却突然把脸别过去,两只手死死搂住杜景之的脖子。
“不要!非离要太傅!”
杜景之拍拍他温暖的小小身体,对嬷嬷说:“好吧,让殿下在我这里玩一会儿好了。”
嬷嬷有些犹豫,李非离却破啼为笑,在杜景之的脸上响亮地亲了一口。“太傅好,非离喜欢!”杜景之也跟着笑,在李非离柔嫩的脸上亲了一下,“非离殿下乖,太傅也最喜欢非离殿下了。”
李非离显然很开心,搂着杜景之的脖子叫:“太傅娘!”
嗯?杜景之不解地看着嬷嬷,嬷嬷也困惑地摇头。
“殿下,你叫微臣什么?”
“非离要娘,要太傅当娘!”李非离年纪虽然幼小,口齿却相当清晰。
杜景之的脸红到了脖根,尴尬地看了一眼捂嘴偷笑的嬷嬷,只好沉下脸来对李非离说:“殿下,不可以随便乱说。太傅是男子,不可以当殿下的娘。”
李非离那双神似李崇恩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杜景之,突然又哭起来。
“不要,不要,非离就要太傅娘,太傅娘!”
杜景之急了一头汗,只得一边点头一边拍着李非离。
“好好好,殿下莫哭,殿下莫哭。”
耳边忽听一声轻笑,杜景之抱着李非离偏身来看。李崇恩嘴角噙笑,双臂抱胸,倚在门框上一副看戏的样子。小瑞子则垂手侍立一旁,一双眼睛骨碌碌直往自己身上瞄。
“太子殿下!”嬷嬷行了礼,垂手退在一边。
“殿下?”杜景之想要行礼,怎奈李非离搂得死紧,只好抱着他欠了欠身,“微臣杜景之见过太子殿下!”
李崇恩笑着,对李非离招了招手:“非离,下来罢,别再缠着太傅了。”
李非离看看杜景之又看看李崇恩,十分不情愿地点了点头,杜景之连忙把他放下。李非离跑到李崇恩的近前伸手要抱,李崇恩一把将他抱入怀里。
“殿下怎么今日有空来到微臣住处?”杜景之把外袍系好,整了整衣衫,“不是明日授课吗?”
李崇恩空出一只手,轻轻抚弄李非离的小脸,一边悠然地说:“哦,今天非离特别顽皮,总吵着要见你,我就带他过来了,谁知道这小家伙脚快得紧,把我们都抛在后面了。”李崇恩轻笑了声,在儿子脸上狠狠亲了一下。“刚好我对太傅前日所讲的义理之道还有些不解之处,顺便过来向太傅请教一二。”
杜景之点了点头,放眼望去,抱在李崇恩怀中的非离虽然容貌娟秀如同其母,但眉眼之间分明有七成李崇恩的影子,看他们父子亲密的样子,心头没来由得一动。
“殿下,景之昨夜还在赶皇上要求的书稿,熬了一夜,现在着实有些倦了。如果殿下不介意,是不是可以等到明日再说。”杜景之拱了拱手,送客的意图昭然若揭。
为什么太傅对自己总是如此冷淡呢!难道自己曾几何时言语行动中对太傅有不敬不到之处吗?李崇恩心底暗暗叹了口气,转身把李非离交给嬷嬷。
“你带非离先回紫辰宫吧,我跟太傅还有事相商!”
“不,不要!”李非离拼命扭动身躯表示抗议。
“小殿下,”小瑞子忙凑过来,从怀里掏出一只竹蜻蜓来,边在手中转边逗他,“来来,你看这是什么玩意儿!”
李非离的注意立刻被吸引了过去,等到小瑞子把竹蜻蜓在掌心转啊转得转飞到天上,李非离的心也跟着全飞了出去。一边咯咯地笑,一边伸着手啊啊的叫。小瑞子对嬷嬷使了个眼色,两人带着李非离快速地离去。
“太傅!”李崇恩走近几步,“用不着你多少时间,不会耽误你歇息的。”
看李崇恩走近,杜景之不觉后退了数步,倒让李崇恩觉得有些尴尬起来。不知为什么,只要自己与杜景之两人单独相处,杜景之就会如同一只长满尖刺的刺猬,不但跟自己保持距离,而且说起话来不是冷若冰霜就是暗嘲明讽。
“太傅,我又不会吃了你!”就算脾气再好,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如此对待,泥人儿也会发火了吧。更不用说,除了对自己,杜景之对任何人,甚至是小猫小狗也是温和有加,笑脸相待。李崇恩不觉有些气闷。
杜景之低了头,口中语气丝毫没有变化:“殿下,微臣实在是很累了,我明日自会去紫辰宫,请殿下先回吧!”
李崇恩觉得很没趣,皱了眉道:“太傅,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如果实在不愿与我交谈,那我干脆明日请父皇旨,你日后不必再去紫辰宫好了。”
“微臣不敢,微臣只是累了!”杜景之抬起头,眼看着李崇恩,“景之一夜未眠,请殿下体谅。”
“算了,既然如此,太傅你早些歇着吧。” 李崇恩张张嘴,放弃地摇了摇头,转身走了出去。
李崇恩一离开,杜景之再也支撑不住跌坐在床上,汗水顺着额角流了下来,双手也在微微发抖。一点没有变,杜景之颓然地倒身在床上。只要跟他单独相处,心脏就会不听使唤地乱跳,四肢,五腑,全身上下,无一处正常的。
李崇恩郁闷地走在廊下,为再一次的挫败而气恼。
因为不觉得有什么必要,所以当得知自己将有一位太傅之时,着实抗拒了多次。直到见了杜景之,抗拒之情便烟消云散了。就算朝中对杜景之年纪轻轻便做了太傅议论纷纷颇多微辞,李崇恩也不觉得有什么。对杜景之,他有一种从心底而生的亲近与喜爱。且不说他的才学得到过周侪甚至是帝后的夸奖,也不说他的容貌举止更是朝中无数人羡妒的对象,只看着他的眼睛,李崇恩就已认定杜景之是可以尊重、信赖、交心并相契的。除了他是由号称“混世小魔王”的皇弟李崇义推荐这一点让人心中不安之外,李崇恩对杜景之的一切都相当满意。
“我并不仅仅当他是太傅啊!”李崇恩常常这么想。“我是真心想与他作朋友。”甚至是知己。
李崇恩常常会想起前年八月十六的夜里,第一次见到杜景之的情景。那双充满关切的明亮眼睛以及被抱满怀时的温热身体。每次一想到,心就像放在暖炉上烘烤立刻就热了起来。那种感觉,就算是和妻子在一起时也从没有体会过。
可是后来的杜景之,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李崇恩叹了一口气。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说话冷淡而疏远,时而中规中矩过于拘泥于礼数而叫人不得亲近,时而逾越礼制地对自己冷言冷语而叫人生气,每每克制不住时,一见到他那双好似藏了太多秘密而略显痛楚的眼神时,李崇恩总会心软气消。
太傅果然是藏着秘密的人啊!李崇恩这么想。常常能感受到身后传来的灼灼视线,李崇恩用不着回头也知道那是杜景之在盯着自己看。如果转头回去,杜景之必然会别开脸而后一通冷嘲热讽。如是数次,李崇恩自己也学乖了,如果太傅要看,索性就让他看个够好了。
但是太傅的失常只在跟自己独处之时。只要有外人在,或是只要杜景之面对的不是自己,他的笑容必是温柔而令人舒心的,他的言语必是合体而令人尊敬的,他的行为必是从容而令人心仪的。
为何只是单单对自己?李崇恩常常会思考这个问题,而一但想多了,便总是会想到令自己心惊脸热的地方去。
不会的,太傅不是那种人!李崇恩每次一想到那里,就会自动将其打断。虽然心里一百个愿意甚至希望杜景之是那个意思,但李崇恩总悲观地认为那只是自己的错觉或是肖想。
如果太傅真是那个意思呢?李崇恩的心怦怦地乱跳。自己一定会欢喜地接受吧,或许,自己有那样的想法也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杜景之啊杜景之,你究竟在想什么呢?
“四哥!你在想什么呢?”突然出现在身边的声间让李崇恩吓了一跳。
“崇义?你从哪里冒出来的?”李崇恩拍了拍胸口,“神出鬼没的,也不怕吓着人!”
“得了吧,我在你面前晃半天了,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想那么出神,我要不出声喊你,你从我身边走过去也不知道。”李崇义撇了撇嘴。
李崇恩脸上有些发热,用手推了李崇义的额头:“你还是那么多话。说吧,今天怎么跑这儿来了,又要耍什么鬼花样?”
“你少乱说了。”李崇义把李崇恩的手挥开,“什么叫鬼花样,我哪里有耍什么花样!我今天是来找景之哥……杜太傅玩儿的。”说着,探头向李崇恩的身后看,“怎么,四哥刚从他那儿出来么?”
“你要是想找他就改天吧。”李崇恩把崇义的肩膀一转,“他昨天熬夜写书,现在已经休息了,你不要去吵他!”
“咦,这倒怪了,太傅熬夜你怎么会知道?”李崇义的眼珠儿转了转,“莫非……四哥你昨夜个儿一直陪在他身边,陪到今天他睡了为止?”说着,竟嘿嘿笑了起来。
李崇恩一皱眉:“你少说这种暧昧不清的话,我是刚刚去找他才被赶出来的。你今年十五都还没到,怎么满脑子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喂!”李崇义脸一沉,“四哥,什么叫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又没说你跟太傅如何如何,只不过说你陪他写书而已,用得着这么急着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