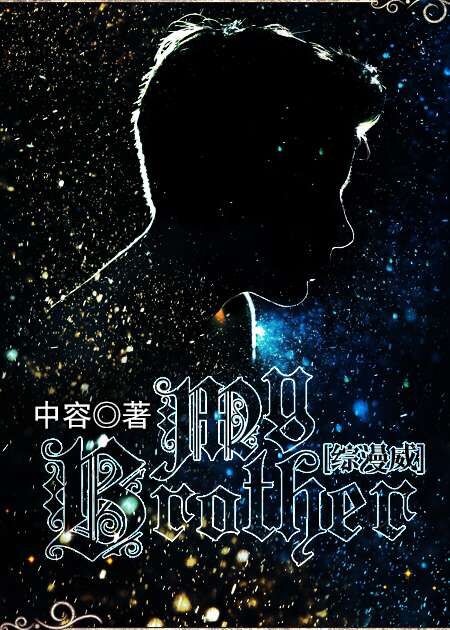浮光 by 渥丹-第3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本人一笔恶书,看到字好的人难免心生羡慕。特别是好字便於阅读,节省时间,真是功德无量的好事。
在仔细查阅之前先大概翻了翻,这都是言采中年之後的信,数量不算太多,一个文件盒就够了,收信人就那麽几个,应该是捐出这些书信的人。
我喜欢读书信,这其中的乐趣远远多於可以一窥写信人当时的心态和翻找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琐事。但是读陈年书信又是考验人的差事:那些人名地名事件因由,对当事人是再熟悉不过,两三句话彼此心领神会,但放到若干年後,外人看来,熟悉一点倒也罢了,不熟悉的,那就是看侦探小说兼之解谜。
初看言采的信,我乐了,一连几封都是和对方讨论当时在演的新戏,演员如何,导演如何,剧本如何,兴致勃勃的;要是他自己的戏,好像就从来没有见到他满意过,虽然也提,但大多是匆匆一笔带过,看来是对别人来信中礼貌的回复。
看过传记再来看信,果然省事许多。信中常常见他谈及朋友,措辞都很得体,但亲疏还是一看可知。
此人是个人精。
我越看越如此认定。
当天图书馆闭馆前,正好读到一封提及谢明朗的,还恰好是当年和我看见的那个展览有关。上面写:
。。。。。。吴敏的情况很不好,病情恶化得很快,我去看过他,他自己也不乐观,还竭力在陆修彦面前装出积极的样子。谢明朗前段时间登山摔到了背,伤到筋骨,又不肯停把拍照的事情暂缓(在病情确定後他们请他拍一组照片留念,至今已经两个月)。吴敏的病让他压力很大,情绪也很低落,他又坚持用胶卷,每次都在暗房里坐很久,这让伤势恢复得更慢。我当初应该坚决劝他不要接手。。。。。。
没想到那组照片之後还有这样的故事。现在想想,那照片里传达出坚定和阳光,哪里看得出是情绪低落的病人拍的。
第二天被其他事情拖住,没有去图书馆,第三天才又坐到那个明亮宁静的阅览室,拿着那些信,看到熟悉的字迹的一刻,竟没来由的觉得有些亲切。
我甩开这些杂七杂八的念头,继续读信。言采的信大多都是那些内容,想来也是,能乐意捐出来的信上,记的必定是些不伤大雅的事情。不过这字看得舒服,我又有目的性,读起来很快。
随着年纪变大,他的信不出意料地少了,变得更简短,字还是整洁有力,但行与行之间的间距也变大了。我无奈地想衰老是无人可以幸免的,哪怕那些语言依然生动有趣,但看着这些细微处的变化,时时暗示着时光的流逝,还是不免伤感。
他人生的最後一年只写了两封信,默默看完之後,又不死心地反复看了几次,只觉得大梦一场。记得谢明朗去世是因为癌症,免疫系统的问题,好像是淋巴。他给人的印象一直积极健康,上山下海,样样乐意尝试,以至於媒体公布病情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难以置信。我有同学对他敬仰有加,去他住院的医院探望不得,回来之後还专门给他寄了花和卡片。但他的病情起伏很大,前一阵子还听说手术好转,没多久又恶化,去世得很突然,但看来是没有受什麽罪。那一年的第一封信看时间是写在谢明朗去世一个月前,收信人名字很陌生,叫沈知。
谢明朗听说你来信,也让我附上他的问候。前段时间他病情忽然加重,弄得我们都措手不及。所幸目前症状又稳定下来。相较之下,他的精神状态比起我来还是好得多。他一个礼拜去医院两次,还是坚持照顾我、喂饱我、打起精神侍候花园。反而是我每天无精打采又沮丧,脾气也很坏。不管怎麽看,到了这一步上先走的那个人都应该是我,但大概我是真的做了什麽坏事,这种事情落到他头上。
前几天看戏回来──《侧影》这出戏不错,我们都很喜欢──回来的路上他忽然问我想怎麽死。我不知道怎麽答他,他说天底下最好的死法是两个人一起数数,数到十之後合眼一起死去。我真的不知道怎麽答他。在他生病之前我从未觉得自己老朽无用,现在却是每时每刻都在体味这一点了。
医生说再过几个月他的情况应该会进一步好转,但越来越多的朋友来探望我们,当然主要是他,这让他很疲倦,而我则觉得我们正在玻璃鱼缸里──太多人知道可能连我们都不知道的真相。但是我也不很在乎这一点,那就干脆别告诉我们就好。不过谢明朗和我认真商量过,如果病情到时没有好转,我们决定再动一次手术。
另,夏天近了,我们还是会上山,你要是有空,来看我们。记得再带个人来,四个人正好打牌。
另一封信上的日期是谢明朗去世後的三个月,这封信上他的字明显不行了,我看着都替他难过。收信人是後来和言采在戏剧上合作多次的导演,顾雷。
谢谢你的来信。我很感激。
最近家里多出很多人来。他们不放心我,找了很多看护,自从买下房子,从来没有这麽多人,几乎每个角落都是,这只是让我更不方便。现在朋友们常来看我,想法设法让我振作一些,只可惜我无法让他们如愿了。晚上的时候我会从一个房间逛到另一个房间(就是脚不太好用),这样倒是能让我好过一些。
最後的时刻很可怕。我们在医院频繁地出入,但这都是无益的折腾,其间我也病倒了,虽然很快好了,但这对此时的我们还是有雪上加霜之感。最後谢明朗说要回家,我们就回来了。所有的止痛剂此时已经没有任何用处,我就看着他在受罪。有几天他的精神不错,本来决定挑时间再去医院复查一次,直到9号早上,他忽然在我面前倒了下来。
他说不要来宾众多的葬礼,也不要什麽仪式,我就和他的家人把他的骨灰埋在了山里的一棵树下面,将来我也准备这麽做。
我必须面对没有他的生活,这麽多年了,还真是有些艰难。
不知为何,近来我怀念着过去,近於思乡一般。
之前那封信上还是两个人的签名,我已经很熟悉言采的字迹,看得出谢明朗的签名是言采代签的,这下忽然看到这一封的落款只剩下一个,心里还是堵了一下。
再没两个月,言采也去世了。
在一天之内看掉一个人的悲欢生死,只觉得信息量太大,呆呆坐着好久,手脚都冰凉了。
本以为那封信就是最後,谁知道习惯性合起文件夹的最後一页的时候,竟看见最後一封信反面一页上还夹着一张卡片。
卡片年份未知,只有月份和日期,图书馆的标注是言采写给谢明朗的生日卡片。我从字迹看,应该是还比较早的时候,卡片上寥寥数语──
这一生中的灵机一动或是忽然兴起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但那天晚上带你回去大概是唯一让我至今想起依然庆幸幸亏如此的举动。你给了我一辈子,我希望这些年过去,你不会觉得後悔或是白费,因为我已经再给不起任何东西。生日快乐。谢谢。我爱你。
8
我没有告诉意明我去图书馆翻看了言采的信件,有那麽一两次想提一句,最终还是羞於出口。如果只是言采也就算了,那是意明的外人。然而言采在,谢明朗也在,我怎麽能提起一个不牵扯到另一个。还是不提为上。
看完那些信之後对於言采私生活的挖坟,暂时告一段落。我不能说我对言采的好奇都被满足了,但目前真的无法走得再近一些,也许过一段时间我会再去看一看他的片子,找些正统的评论,但那都是之後的事情了。
没多久暑假到了,老板八月出门休假,也大发慈悲给了我将近一个月的假期。正在考虑去是不是回家,一天约会的时候意明貌似不经意地提起,他把年假也排在了这个月,後来还很无辜一般问我:要不要去哪里玩?
在一起这麽些年,还没怎麽出去玩过,听他这样说难免心动,反问他:你想去哪里?
意明沈思片刻,说我其实就是想两个人找个地方躲起来。最近太热了,山上还是海边,你喜欢什麽?
他说起这种甜言蜜语对我来说素来很受用,无奈生来怕水,海滨浴场沙滩之类统统与我无缘,但和他在一起,想来去哪里都是好的。我就答应说:别去海边就行,或者你愿意看我煞风景地不下水。
意明笑了,凑过来说:那好,我们去山上避暑。
没几天我们开车连夜上山,盘山公路上我骂他发疯,多等一个晚上又怎麽等不得。他却说摸黑上山别是一番风味。可是放眼四顾,除了路灯,偶尔对开而过的车辆,那就是黑黔黔的山头,随着车子一路开上去而一座座矮下来,风里传来不知道什麽的声音,风味不风味我不知道,鬼影幢幢倒是真的。
我在途中睡了一觉,醒来之後车子已经停了下来。夜里看不分明,借着路灯看见是一栋小楼。这种别墅在这山上多得是,私人产业居多,也有相当一部分改建成旅馆,租给短期避暑的游客。
进门一看果然是旅馆,听地板的声音已经有点年岁,但房间宽敞,装潢得也很体面,最重要的是床看起来很柔软舒适,我累得要命,别的也没多看,就睡了。
接下来几天我们在山上到处玩,晚上出去吃饭,喝得醉醺醺的手牵着手回来,每天都过得很安逸。我是第一次来,意明却对这里很熟,我也心安理得让他领着我玩。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礼拜,懒散得骨头都要酥了。
这日子虽好,我本性还是个热爱都市的人。此地清幽,太不适合我。住了这一个礼拜觉得已经够了,想想接下来还要再住一个礼拜就觉得乏味。也不太乐意出门了,宁可给朋友打电话再看看电视什麽的。意明对这种生活倒很满意,还拉着我早上起来打球,俨然是要过早睡早起的健康生活的架势。
一天早上我被雷声吵醒。山中多雷雨,也容易起雾气,远处山头的云飘过来,往往就化作雨水。醒来的时候意明不在身边,摸了眼镜戴上,只见他站在窗前,不知道在想什麽。
因为打雷,醒了吗?我问他。
他回头:嗯。你怎麽也醒了?
我披了衣服起来,走到他身边。我们住的宾馆相对地势本身就高,我们又在二楼,远望出去,只见一座座房子的屋顶掩映在翠色中,有些还能看见花园,在这静谧的清晨,山水画一般。陪着他看了一会儿,我说:我最近白天睡得太多,早上反而容易醒。
他看着我笑说:我想你也觉得无聊了。
倒也没有,只是享清福的日子,不是人人过得惯的。
他听到这里又笑了笑,拉过椅子坐了下来,又很快地站起来,说:坐着还是看不见。
什麽?
意明指着那些房子中的一栋说:我小时候在那里住过。
我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找了一会儿,还是不确定他指的是哪一栋:哪个?花园有个大花架的?
对。那里以前种的是三角梅,这个时候正好是花季。不过现在看不到花,新主人可能换了别的植物吧。
他这麽一说,我不免有些联想。不是这麽巧的。意明扭过头,看着我说:那是舅舅和言采当年的房子,他们以前每年会过来住两三个月。後来房子卖了,我也几年没上山,没想到变成这样了。
果然。
一旦开启这种话题,我就发现无论意明还是我,都变了。陷入对往事的追怀之中,有着平时难得一见的固执。至於我,则在一种介於畏惧和好奇的心理之中,不可抑制地希望他说得更多一些。
我就接过他的话:每年来避暑吗?倒也能静心住三个月,他们应酬都很多吧。
我以前也以为是的。後来才晓得言采工作的时候会失眠,一出戏又动辄几个月,他们就拿这三个月调整。
听到这里徒然有些羡慕,又去看了一眼这房子:好像能避世一样。
意明听了我这句话,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看起来是要反驳的,但最後居然并没有说什麽。
舅舅去世之後这房子就卖了,等到言采去世,城里的房子也卖了,钱都放到基金会里,这遗嘱不知道是他们什麽时候商量的。所以说我搞不懂言采,我不知道他怎麽能在我舅舅生病的时候两个人坐在一起商量遗嘱。意明脸色阴沈了,我果然不喜欢他。
你已经反复在强调了。我心里暗叹。嘴上则说:他不卖,难道还回来住吗?
意明就不说话了。
早饭吃得不甚愉快,或许是因为早上的回忆。吃完早饭後他也没出门,坐在一楼的厅堂里看报纸,我就陪着他,坐在边上看电视。这样到了十点,雨停了,太阳也从云里探出头来,他把手边的报纸统统读完,忽然说:我今早说了些怪话,情绪失控,对不起。
我看着他,说:只要涉及到你舅舅,你道歉的频率就比平时就高得多。其实没关系的,你想说就说,我很乐意听。这是你的家人,我很高兴你和我说这些。
他愣了一下,抿起嘴,又露出那种不自觉的固执来:这些年来我爸和我都不太提舅舅了,怕我妈难过。不晓得怎麽回事,自从听你说你在找言采的资料,我又开始想起他们。舅舅去世的时候我爸妈都在外地,没赶上最後一面。下葬的时候她又病了,是我爸和我去的,她因为这些一直难过内疚,说些傻话。
你想,也许你舅舅就是不想她太难过,才这样避开她。他们感情一定很好。我说完想到这句话和我素信的人死神灭背道而驰,一瞬间竟也想苦笑了。
谁知道呢。说完这句话他犹豫了很久,我正奇怪,不防意明低下眼来,淡淡问我,他们葬在山里,你想不想也去看看。
我们先是开车,往深山里绕,一开始还是公路,我一路上都在听意明说谢明朗的旧事。他想来压抑太久,说话的语气连我听来都觉得如释重负。眼看前面没有公路了,意明把车停在一边,我们走下车来。接下来都是山路,但早上下了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