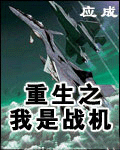我是如何弄垮巴林银行的--尼克·-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拿起电话,拨了八○八——那是巴林期货在sIMEX的号码。
“力塞尔,”我说,“是我。告诉我市场价格的情况及成交规模。”
“二十份标价三百五十,二百份标价三百六十,三百份四百五十,二百份三百四十,一百五十份三百三十,三百份三百二十。”
这个不祥之兆。看来,我们遇到了阻力。我一点都不喜欢看到这样情况。
“好吧,就这样吧。”
我从萤幕上找到了我关心的那一栏。我决心卖出一些。我得小心行事。看来,一万九千三百五十点是很难突破的。我决定小心卖出,每次卖一点。
我按了电话上的按钮,力塞尔能听到我的声音了。
“力塞尔,你给我在三百五十点卖出一百份吧。”
这比二十份多点。天知道我还有多少份类似的合同。这条报价给大阪方面后,他们延误了很长时间才把它打上萤幕。
因为这个缘故,我觉得大家都看出我的用心了。
“有人愿意买吗?”我问。
“很抱歉,尼克。还没有。”
这时,我听到迈克的声音从电话里传过来。“有个五十份的报价——它正好在你们前几秒钟出来——将你的那条挤出萤幕。现在有一百五十份报价三百四十。他们把你的吃掉了。”
“没关系。”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紧张。胃却越来越痛。“我马上就回来。”
我轻轻放下电话,不让别人看出自己的焦虑来。我还微微笑着,看起来很高兴似地。我又拿起一条水果香锭,将它折成两半。我等不及,没时间去把那银色的包装纸撕掉了。
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被迫做成交易的经历了。总是有人赶在我们前面,结果我们便失去了在某一价位时做成交易的机会。为此,我们大倒其霉,深受其害。上次我大阪时,大家还开玩笑,说有人窃听了我们的电话。现在看来,那不仅仅是玩笑了。大阪方面那些人还真是对了,我也开始相信他们的话。
切斯走过来,跌坐到一把椅子上。他把脑袋搁在桌上,语无伦次他说着他押在阿森纳队头上的钱输掉了的事。上帝!那正是我的感觉!我真想低下头,放弃这一切。我真想走到交易场地的中央;然后四仰八叉地躺在那儿,直到有人来把我送到游泳池边的椅子上去,外加一杯冰啤酒,还要有一个汉堡。我为什么要让自己看起来那么强大呢?我正想给切斯说话时,萤幕上的字又开始跳动了。我操!开始下跌了。三百二十闪烁起来。我抓起电话,拨了八○八。
“夏娃吗?我找卡罗说话。”以后我会向她道歉的,“市场如何?”
“一百份报价三百一十,二百份报价三百二十。”她说。
“我的天啦!”我用左手压住鼻梁,以防急火攻心,引起血液大量涌入头部。“竞价是多少?”
“三百点四百份。”
“好吧,那就在三百点卖出五百份。行动快点!”
我等了又等。
“尼克,现在没有任何交易。”
我看见萤幕上的价格跌至二百九十了。快点!快点卖出呀!有一种声音在我的脑袋里呼喊。
“一笔交易都没有做成。”卡罗从日本那边回话了,“有人赶在你前面。现在整个市场上都是比你出价高的标价,一共是一千份,报价为三百。最后的一笔交易是二百七十的。现在的成交额极低。”
我闭上眼睛,看到自己眼皮上直冒金星。
“好吧。”这回,我无法掩饰自己的紧张了。我的勇气和决心全没了。
“尼克,我很抱歉。”
我摔下电话。我不在乎别人看见我这副样子——别人都可以这么做,我为什么不能这么一次呢?我又回头盯着萤幕,开始耐心地等待。切斯懒洋洋地趴在桌上。我有两种想法,我可以和切斯一样,将头搁到桌上去,但我怀疑自己是否再能将它抬起来,我也可以站起来,抬起右手,在他露出来的脖颈上砍一下。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传来了我极不愿听到的消息。
“尼克,你已在二百五十点买进二百份;在二百四十点买进一百份;在二百三十点买进二百份;在二百二十点买进三百份。”
“好的。”我说,心里有如打翻了五味瓶。
我又开始等第二个电话。这次的消息是最坏的。它是力塞尔打来的。
“尼克,你已在二百一十点买进五百份,在二百点买进五百份。”
“市场现在如何?”我好不容易才积攒了足够的力气将这句话说出来。
“一万九千一百九十,看来非常疲软。大贩方面刚才打了电话来,问这边的情况。”
“告诉他们一切正常。”我给自己打气,“让他们做好买进更多合同的准备。”
我咬着下嘴唇,开始计算我的头寸。我又从大阪市场上买进了一千八百份合同(相当于从SIMEX买进三千六百份),平均价格为一万九千二百二十。但市场已跌破一万九千一百九十,而且显得非常疲软。这太荒唐,太奇怪了。也许用“悲惨”更能表达我当时的感情。但是那个词又太陈腐了。很明显,我是有点精神恍惚,糊里糊涂了。更确切地说,我是两眼一抹黑,不知何去何从了。
如果市场继续下去的话,很快就会跌到一万九千点。到那时,又会引起一阵对我的期权的“狂轰乱炸”——每个人都会拼命抛出,而我必须接受他们抛出的合同。这些期权合同就会在期货合同引起的亏损上雪上加霜。我很理智,知道这时我应该卖出。最好是将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期货全部卖出。但这意味着我束手就擒,被解出交易大厅,押上囚车,然后被关进监狱。我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做着巨额的交易,而且,造成的损失已高达一亿英镑了!我不敢肯定我是否在犯罪,但是我很清楚:我已赔进的钱可以铸成一座金山了。我不能卖出。我只能设法让疲软的市场重新坚稳起来。我的头寸是如此巨大,而且在不断增加,这使得整个市场都视我如“晴雨表”了。我必须扭转乾坤。但是,形势却非常不利,到现在为止,我还可以将八八八八八帐户中所有的期货卖出,变为空头。但我又怀疑能否完全将它们卖出。我是多头,而且必须硬着头皮坚持下去。
吃午饭的时间快到了。我决定任由市场发展,在下午上班前不再管它。这一上午,我的损失已经太惨重了。
“丹尼!”我朝着他喊道,“去‘东方’吃早饭怎么样?”
我们还没吃过任何西。我们总是将十点钟后的小段休息时间叫“早饭时间”,尽管大阪那边已经该吃午饭了。一我们走出了交易大厅,步入巴特利路。天真热。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又热又干,喉咙像刚抽过烟一样难受,丹尼截了辆出租汽车,将我们送到“东方”。一路上我们对工作和市场都只字未提。我们都睡过去了。有人将我们带进“东方”豪华安静带有空调的餐厅。侍者穿着洁白挺直的制服走过来取我们的点菜单。不知何处的音响里传出轻柔得不易察党的音乐。交易大厅里那喧闹的噪音终于从我脑子里退去了。我们吃了一份纯英国式的早餐:熏肉、鸡蛋、土司、柑橘酱。我离沃特福何止百里之遥!但是,早餐却总让我想起家乡——这在其他用餐时间是不可能的。起身付帐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还穿着那可笑的条纹夹克。其他客人都穿着体面的灰色西装。我一定非常刺眼。
“咳,气泡!你怎么没提醒我?”我抱怨道。
“我以为你知道呢!”丹尼说,“人们都知道他自己穿的是夹克还是长裤的嘛!不过,这身夹克倒是把你那条难看的领带盖住了。”
外面已经下起雨来了。我们只好和其他客人站在一起等计程车。返回sIMEX,正是刚刚重新开盘的时候。我们搭乘电梯到了三楼。我感觉噪音比上午更大了。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和丹尼分开后,我冲到离我最近的萤幕边。
市场又下跌了一百九十点。我几乎晕了过去。现在到了一万九千点了。我的期权都要扔给我了,上千买进的期货已经亏了一大笔了——三百万,而且还在上升。我两眼发黑,跌跌撞撞地走到日经交易场地上的办公桌边,我紧张地问:“到底怎么回事?”
“那些新加坡人想把我们挤出去。大皈方面还没有重新开盘,这边的压力太大了。他们知道市场上有人是多头。”
我也知道这个。
我离开日经交易场地,挤过去打“侗和“间谍”。大阪十分钟后就要开盘了。我看着远处的力塞尔,打手势让她告诉我大阪市场情况。
“开盘时有二百人卖出。”她用手势回答我,“不太低。”
周围的人都像中了邪似地,在拼命抽回头寸,我听到的声音都在喊“卖出!”“卖出!”,看到的手都在空中不断地挥舞。每个人都知道我为多头,都希望我也卖出。那些新加坡人都很怕我;他们正努力卖出,可是我一个人就足以扭转市场走势,将价格推回到较高的水准。他们每日的交易额都限制得很低。一旦我将市场价格扳回,他们便不得不减少头寸,并承受一定的损失。他们也会进退两难,因为如果他们在大阪有交易的话,一旦大贩市场也掀起抛售狂潮,那就会让许多人(包括我自己)的资金化为乌有,我静静地站在那儿,看那些红夹克狂呼乱叫,脑子里却万马奔腾一般,闪出许许多多的想法来。我最关注的就是一万九千点!如果价格在跌破一万九千点后继续下跌的话,那么我卖出股票出售期权的头寸就会奇迹般地毫发无损,而期货的收支差就会至少增加一倍了。我就知道,那一定是非常可怕的——就像飞机坠毁一样。
我找到“侗,告诉他在一万九千点时买进,脸上装出一个自信的笑来。没必要压低嗓音,我几乎没听见自己的喊声。
“多少?”他对着我的耳杂喊了一声。
“你爱买多少就买多少,肥仔!”
“侗行动起来了。
他做了个深呼吸,像帕瓦洛帝一样挺起胸,然后朝交易大厅吼道:“一万九千点,买进二百份!”他张开双臂,招呼想要卖出的交易员。他们都朝他围了过来。我看得一清二楚。
我远远地朝那些新加坡籍的交易员和日本交易所看去,我一眼就能看穿他们。
“买了二百份。”
“侗朝我喊道。
“我已买了三百份。”我还和诺穆拉就另一笔买卖达成了协议。我发现诺穆拉的交易员已跑回去请示去了。在他们商议的时候,我悄悄地数着数。诺穆拉花费的时间越多,市场情况便越对我们有利。他颠颠地回来了,看了看我,报出了另外一个五十份,我把它们抢购下来。“侗朝交易场地边上看了看,发现萤幕上的价格变成了一万八千九百七十五。
“把那个价格删除!”他叫道,“我们的标价是一万九千!”
萤幕上的数字果然消失了。不过,重新出现的并非一万九千,而是一万九千零五十。诺穆拉停止了抛售。我看着那个交易员,太好了!他在一万九千零五十点时买进了五十份。他在擦屁股了。我又看看那些新加坡人。他们紧张起来了。所有的交易员成夭都是紫张兮兮的,叫人分不清他的紧张出于哪种原因,也分不清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但是这回,我却很清楚他们紧张的缘由——他们都想避免从我这儿买进。他们在寻找其他的卖方。
我附在“侗的耳杂上,如此这般地交待了几句。“侗又开始付诸行动了。“一万九千零六十点,五百份!”他喊道,声音里仿佛全是怒火。交易员们在尽力驱动市场变化时,都是这样的。
市场终于开始上扬了。回到一万九千一百点了。这时,大阪市场也重新开盘了,喧闹声又大了起来。这是充满了痛苦和困惑的声音。大皈开盘一万九千二百点,和上午收盘时的水准持平。那些新加坡人简直疯了——他们拼命卖出,好不容易将价格降到了一万九千点,而现在,又要争着保住头寸。他们开始买进了。有位新加坡人恳求我,让我在一万九千一百五十点时卖出。他给我打手势,双臂张着手,拿交易卡,动作像一种扭劣的求偶舞蹈似的。看那样子,如果我不卖给他,他就会疯掉。
他会走到交易场地的正中间,横剑自杀的——他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我微笑着,欣赏他那夸张的表演,让这家伙痛苦一会儿吧。我又开始等待了。我知道他其实并不在乎,他的财富并不会因此而受丝毫影响。这时,价格上扬到了一万九千二百点。我在这时才把合同卖给了他。他的眼睛都没眨一下,就下找去一位卖主去了。这真有趣。价格又上扬了,到了一万九千二百五十点。
“我买了多少?”我大声问“侗。
“五百!”他回答道。
“把它们悄悄卖出去!”
“侗将二百份按一万九千二百五十的价格卖给了新加坡交易员,然后又卖了四个五十份。我按一万九千二百五十的价格卖出了二百份。之后,我又以一万九千二百五十的价格将五十份卖给了一个打量我许久的新加坡人。最后,把剩余的部份按一万九千二百卖给了摩根斯坦利银行。“侗和我都静静地站了一会儿。
“现在的情况如何?”
“还有一百份为多头。”
我感到志得意满。价格停在一万九千二百点上。我们耐心等着。实际上,价格已经稳定下来了。随着大阪市场的攀升,这边的价格也逐步回升了。当然,这比我们上午买进时的价格要低,但是,今天下午,我们丝毫没有退却。实际上,我们已狠赚了一笔。“了”是欣喜若狂了。他将最后的一百份以一万九千二百八十的价格卖出后,我们离开交易场地,来到工作间。
马士兰在那儿,他来看我们要不要什么东西。
返回工作时间,我满脸笑容。力塞尔正在给大阪打电话。
市场仍在回稳。我可能已经挽回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损失了。
今晚,那些起新加坡人肯定会谈起我的。
“你看见没有?他在一万九千点买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