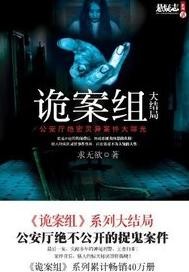玉鼠案-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玉面人儿躺床相邀,自有妩媚万千。
可惜展昭眼睛未瞎,便是灯下昏暗,也看得见属于男子的平坦胸脯,以及眉宇间那戏弄人的狡猾笑意。
展昭心中冷笑,这白老鼠想戏弄人,至少也该看看对象为何。
“好。”
他爽声应了,迈步上前坐落床沿。
“诶?!”白玉堂本算计他断不肯与己同宿,意欲鹊巢鸠占。怎料他居然应允,这下可轮到白玉堂发懵了。
看他愕然表情,展昭大方拖去外衣,推了推霸占整床的大老鼠:“劳白兄让半铺位。”
“你、你……”
他二人一猫一鼠,长年将对方视为竞手,便是同宿客栈也要分房而眠。今番可算白玉堂首次如此靠近这只天敌。
宁静心湖忽被掷入一石,波起阵阵涟漪。
“白兄?”
展昭见他还在发愣,靠过脸去唤了他一声。
人说南侠儒雅俊貌,斯文清秀,他白玉堂向来是闻之不屑。
此刻方知,是他偏见甚深,打一开始便死活认定猫儿的脸就跟猫儿一样滑稽好笑,对那俊郎外表视若无睹。
黑砾石般的双眸如藏了天上两颗璀璨星辰,剑眉若柳乃是神笔画之方有如此完美浓淡,五官容貌天作而合散发温雅气态,便是那片略白唇色,润泽厚度亦足教人留恋不去。
……
咦?奇了,他怎将这只臭猫的脸看得那般真切?
“啊!!!”
白玉堂这才发觉二人距离不过两寸,鼻子都快碰上。
展昭闻他惨呼,好似见鬼一般,不禁皱眉道:“白兄,你到底要不要睡啊?”
“谁要跟你这只臭猫睡?!”
白玉堂拔身而起,仓忙之间捞去床头外衣,窜离床铺,甚为习惯地破窗而出。
“哐!!!”
猫鼠之斗,向来是沉不住气的人先输。
而每次挑起纷争之人,却总也不知自己便是最沉不住气的那方。
展昭嘴角带笑,看着地上第十二度被撞破的窗户,心想明日又得唤人来修了。
“臭猫、烂猫、病猫!!!”
开封城内横街,一白衣男子正朝一只蜷缩墙顶的小花猫大声咆哮。
可惜那小花猫不买帐,任他百般叫嚣,只是耷拉了两可爱的小耳朵继续睡午觉。
这无聊人士,竟是那自命风流倜傥、潇洒人生的锦毛鼠白玉堂!!
昨夜他逃也似地离开开封府,居然就这么施展轻功跑了两里路子,方才察觉匆忙之间只取了一套外衣,装着银票的包袱,甚至连从不离身的画影也都丢在展昭房中。
天啊!!
他怎就像个被抓包的情夫一般,差点连鞋子都忘了穿。
想掉头回去取,可又憋不下肚里那口恶气。
全天下人都知道,他锦毛鼠与那只讨厌的御猫是死对头,昨夜他竟然当了那臭猫的面逃得如此狼狈,哪里还有脸回去取忘记带走的东西。
偏身上行当都在那包袱里,现下他白玉堂说的好听是孑然一身,说的难听就是比乞丐还穷。
“该死!!都是你这之臭猫、烂猫、病猫的错!!!”
“喵呜……”
小花猫许是嫌他太过吵耳,四足伸直站起,弯身一跃轻盈落到地上,摆着可爱小屁股,摇摇晃晃地走了去。
竟然连一只小花猫也瞧不起他?!
白玉堂登时恼了,骤一伸手,揪住那嚣张的小猫儿后颈皮,将它提至眼前。
“臭猫!你敢瞧不起我?!看我不扒了你的猫皮!!”
“喵喵喵……”
小花猫突然遭袭,四爪乱抓企图挣扎,可惜它只是寻常猫儿,怎逃得过这只锦毛大老鼠魔掌。
它越是挣扎,白玉堂越是得意,好似将对某一猫的不满发泄出来般。
“呵呵……怎样?害怕了不是?好吧!你求我便放了你!快求我啊!”
“喵喵喵……喵喵喵……”
可怜此猫非彼猫,难通人性,怎识开口求饶。
“这位兄台,何必为难一只小猫?”
终有人路见不平,出声相助。
白玉堂正玩得兴起,被人阻挠登感不悦。
转头,见是一堇衣青年,看此人儒巾包头,腰配长剑,打扮朴素清简,许是个浪荡江湖的游子。
“多管闲事。”
白玉堂心情更恶,瞪了那好管闲事之人,便又径自玩弄手上小花猫。
那人倒是锲而不舍,继续劝道:“闲事本该少管,可在下看来,兄台此举实属无端迁怒。小猫无辜,还请放了它吧。”
话虽无意,却准戳要害,立马将白玉堂那别扭劲给撩拨了出来。
“便是无辜迁怒,你又能耐我何?”
堇衣人闻言一愣,还真没见过耍泼皮也这般理直气壮的。对那白玉堂打量一番,不禁笑道:“确实不能如何。兄台果真不肯放手?”
“不放。” 狡猾明眸泛出挑韧光芒,“有本事,自己来夺。”
“好。”
话音刚落,只见那堇衣人身形一动,已贴在白玉堂身侧,出手快若闪电,直取他手中猫儿。
“来的好。”
白玉堂在江湖上向以轻功自傲,见其身法轻灵若燕,顿生争雄之心。
他不躲不闪,翻手将那猫儿抛至凌空半尺,随即伸手一搭,欲擒他腕臂。
堇衣人从容一笑,五指骤缩,翻转而上反拧白玉堂手腕。
便是在小猫上升下落这片刻间,二人已各自使出小擒拿过手十招,却仍不分上下。
眼看猫儿就要落地。
“啧。”
白玉堂骤一缩手退去攻势。
那堇衣人以为他肯认输,便也不再出招,弯腰探手要救小猫。
怎料一席白袖风卷而至,将娇小猫儿捞了回去。
便是使诈,但白玉堂已胜却也是事实。堇衣人束手旁立,暗中打量这个看来胡闹,武功却极为不凡之人。
将猫而捧在手里,白玉堂煞有介事地与它说道:“我说小猫啊!你可看清楚了哦,救你的人是我,害你险些摔破屁股的人是他。”
怎知那小花猫早被吓坏,哪里还管谁救谁,利爪狠狠一抓,登在光滑雪白的手背上留下四条血痕。
白玉堂吃疼立马松手,小花猫一个翻身跳落地面,几个窜身已不见踪影。
徒留那被伤之人望空叫嚣:“啊呀!!真是天下猫儿一般狠啊!!救了你还抓我!!今天若不把你的猫皮扒了爷爷就不叫白玉堂!!”
“哈哈哈……哈哈哈……”
旁边堇衣人见此情景,禁不住捧腹大笑起来。
本以为白玉堂是个蹂躏生命的恶徒,怎料却只是个好意气之争的顽劣大孩童。他识人虽多,但如此有趣之人还是初次见到,不禁生了亲近之心。
“笑什么笑!!”
被取笑的白玉堂瞬时转变泄愤对象,狠狠一掌劈了过去。
怎料那堇衣人竟然不躲不闪,立定原处,反叫他那凌厉一掌劈不下去。
白玉堂煞住攻势,掌沿在离他肩膀一寸之位险险停下:“喂!干吗不躲?这掌要打中了可要碎掉肩骨。”
堇衣人微微一笑:“在下适才误会兄台,愿这一掌以作抵偿。”
“……”,白玉堂皱了剑眉,又重打量他一番,却未能从那双清澈眸中看到丝毫作伪,“你毛病啊?这至于嘛?”
“在下心中有愧。既然兄台不愿伤我,不知可愿赏脸,聚贤楼上水酒一杯以作赔罪。”
看他语意诚恳,白玉堂也不好推辞。一路奔跑来回合共四里,肚子早觉空虚,便顺了他意:“如此,便却之不恭了。”
“哪里。”堇衣人温文一笑,拱手道,“在下唐文逸,未请教?”
白玉堂也是爽快之人,朗声报出名号:“在下白玉堂。”
3
“不知唐兄来开封所为何事?”
仅是半个时辰,白玉堂与那唐文逸已是一见如故。
唐文逸欣赏白玉堂那份爽朗豪情,白玉堂则对他毫无机心的纯直极是喜欢,言谈之间,二人皆觉对方经纶满腹,胸襟宽广,彼此心佩不已。
畅所欲言之下,白玉堂道了自家名号,亦闻唐文逸是来自极西之地,不禁生了疑问。
他心直口快,也不考虑对方可有难处,冲口便问。
幸唐文逸并未计较,轻品盏中清酒,坦言答道:“为寻一人。”
“哦?此来开封迢迢千里,跋山涉水不在话下。白某倒有兴趣,是何人引得唐兄万里来寻?”
唐文逸眼神一缈,缓缓放下手中杯盏。
叹息之声溢唇而出:“花萼开,并蒂连,埙篪齐奏叶双声。双生果,心两半,无影无痕觅千晨。”
白玉堂闻言,了然心中:“唐兄可是来寻自家胞兄?”
“……”
唐文逸闻言一愣,随即展颜笑道:“白兄猜得不错。文逸有一双生兄弟,月前不辞而别音信全无……后闻人说吾兄曾言要去中原开封,因此寻踪而至。虽到达半月之久,却总未得见……”
思念之情实教人动容,偏有人为之发笑。
“呵呵……”
唐文逸奇怪看着那笑得开心的白玉堂,人家骨肉离异,他居然笑得开心?脸色不禁有些黯然。
“唐兄莫要气恼。”
白玉堂提了酒壶为他满斟一杯,举杯敬道:“我倒要多谢令兄无故失踪,否则西域到此千山万水,要与唐兄如此妙人相遇想来绝不可能。”
“呃?哈哈……白兄所言极是!”唐文逸了悟其意,知他有意安慰,只觉一路跋涉、满身艰劳尽扫,心中担忧亦暂时放下,尽情享受这刻知己畅饮之快。
敲盏落碎,二人相视一笑,扬头痛饮佳釀。
酒过三巡,白玉堂多少有了几分醉意,话也渐多。
所说话中总带一人,或该说,是三句不离一猫。
唐文逸来自极西僻地,对中原盛极一时的猫鼠之争从未耳闻,自然觉得新奇有趣。
又闻二人破得奇案,更是心驰神往。
“唉,文逸久居西塞,看似跳脱世外,其实错过迭起风云,浪费了轻狂青春。”唐文逸拨弄桌上冷却菜淆,惋惜之意教那张儒生面容带了怅然,“难怪哥哥常惦记着到中原一闯。男儿胸襟当载天下……今日方知,文逸不过是一只故作清高的井底蛙,实在可笑可叹。”
“此言差已!”
白玉堂乘着几分酒性,顿时来了意气:“唐兄年华正茂,今朝来得开封,断少不了造就一番哄烈事业。”说罢抬起银瓶酒壶,灌下残酒,横袖一抹,“白玉堂当不能白吃了唐兄一桌酒席。”
“白兄?”
面带半分醉红,脚步却无踉跄,教人难懂他是醉是醒。
白玉堂嘿嘿一笑,明皓眸子朝他狡猾眨巴:“今晚便让白某作导,带唐兄到京城名胜开封府一游!”
“咦?!”
开封府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大人房中桌上,放了一个包袱以及一把华美宝剑。
可并非因为房主意图远游。
展昭一日公务终了,推开房门,见桌上仍放着包袱宝剑,顿生纳闷。
昨夜那白玉堂匆忙离去,竟丢下从不离身的画影及衣服细软,可知当时是何种狼狈。展昭心觉好笑,那看来大胆妄为的白老鼠,其实那片脸皮子可薄得很。
料他会来取回包袱,为免他趁机发难捣乱房间,展昭故意将包袱及宝剑放在当眼之处,只望白玉堂取了就走,莫要多作留难。
怎知一日下来,二者原封不动。
展昭不禁心下有忧。
包袱或可不取,但那把白玉堂视若生命同体的画影却怎可能置放别处,更何况留在他这个头号劲敌的房内。
莫非出了事故?
越想越坏,月前种种骇况渐现眼前。
画影被骤然握在暖掌中,展昭吹熄烛台火影,与巡逻守卫的马汉说下情况,便匆匆出府去了。
他前脚离府,白玉堂后脚便至。
而且还带来一个初到京城的旅客——唐文逸。
二人轻功相当,如两只巧灵夜燕,无声无色落于府衙内院。
唐文逸到京城也有一段时日,亦有几次途经,对此地之肃穆庄严自是心敬不已,怎想到有朝一日居然冒犯府威,夜探开封府。
他向来奉公守法,光明正大,替一小畜生仗义执言可见一斑,今晚这等近乎夜贼小偷行为对他而言是何等匪而所思。
感觉上,便像一平日乖巧听话、只坐书斋的孩子被坏朋友带去后山野林逃学玩乐,那种打破规限的奇妙快乐令唐文逸兴奋莫名。
齐整脚步从远而近,马汉带着一队衙役巡了过来。
白玉堂是轻车熟路,朝唐文逸眨眨眼,伸指指向房樑。
那唐文逸倒也聪慧,一个动作半个眼神便明了意思。
待那队衙役通过之时,廊内平静如昔,但如若抬头,定见两名不良分子静伏樑柱。
白玉堂凑近唐文逸耳朵,压声笑道:“嘻嘻,唐兄,你倒有些樑上君子之才啊!”
“哪里哪里!”唐文逸温文回笑,“怎也比不过白兄驾轻就熟,像回家一般。”
“谁家啊!”嗔了一句,白玉堂翻翻白眼,“这可是臭猫的老窝,若非确实有事,我是能不来就不来。”
“咦?”唐文逸故作不解,“可之前白兄不是在展昭房内度了数夜么?”
“……”
樑角暗黑,窥不见白玉堂面色,恐怕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