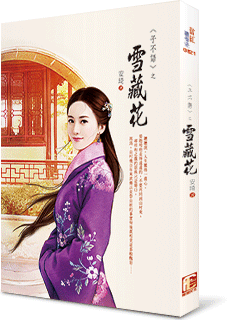迎春花(冯德英)-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来日方长,慢慢地干,猛一下子闹大了,易出乱子。嗬,山河村这群牛伸了腿,就够曹振德那伙小子受的啦,也出出我这口压了多少年的冤气!”
孙承祖板紧脸皮沉思了一会,说:“现在牲口最要紧,要杀!不过,你说在咱村停牛场上放毒?”
“对,对!”蒋殿人点头应道。
“使不得。”
“这我就不懂啦!”蒋殿人忍不住地叫起来,“和着土信煮一升黄豆,今夜撒在西河滩停牛场上,明早天不亮牛就去了,饿肚空肠,吃下去一个也活不了!这是万无一失的手段,怎么使不得?”
孙承祖连连摇头,脸上露出冷笑:“你怎么忘了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啦,嗯?”
“哦,啊……我白多吃那些年粮了!”蒋殿人恍然醒悟,自惭地拍拍脑壳,朝国民党的特务心服口服的说,“差一点为我的疏忽出乱子。嘿嘿,镯子,我比你男人差远啦!他真是‘智多星’,我可光顾出眼前的气啦!”
“伸冤报仇也要看大局。天下的共产党都是咱们的对头,打它的哪个地方都痛着它的心。咱在自己村边的停牛场下手,人家不就怀疑到本村有坏人了?一时查不出来,也会加强对我们的防备,以后我们的手脚更不好动了,何况曹振德这小子,虽说土里土气,可他那把骨头是为共产党长的,够厉害的了,咱们要处处提防这把刀!”
孙承祖的这一席话,使蒋殿人和王镯子连连称是。
不过我们不怕他,要干!我要怕他们就不回家乡啦。只要咱们多动脑子,曹振德那几个人算得什么!”孙承祖攥紧了拳头,瘦长脸上闪着凶狠的青光,看着毒药说,“牧牛山大得很,不光是山河村去放牛……好,煮饺子吃,吃饱去打这一仗!”
“姨父!”上身白衬衫下身蓝布裤的青年,文雅地叫道。“若西,你坐吧!”老东山的妻子招呼道,望着躺在炕上的丈夫:“你外甥看你来啦,还不快起来。”
窗外细雨霏霏。虽是中午时分,屋里光线黯淡,气候倒还凉爽。
老东山慢腾腾地坐起来,闭着眼摸起烟袋,沉闷地说:“你来啦。”
孙若西把布伞放到桌前,将手里的能盛一斤的酒瓶子高高地举起来,讨好地说:“昨天赶集,打了点酒……”“哦,不用你破费!”老东山眼睛睁开,满意地接过瓶子端量一番,放在窗台上,吩咐妻子:“烧水给外甥喝,他不喝生水。”
“一斤酒的脸面这末大,舍得草烧水给我喝啦。”孙若西心里暗道。姨母走后,他坐在炕前的凳子上,试探地说:“姨父,我爹妈有个意思,想和你老人家商量。”
“说吧。”老东山闭目抽烟。
“是这末回事,”孙若西陪着笑脸,“是我的事。姨父你知道,外甥今年二十多啦,还没订亲,想和你老人家商量……”他咽口唾液,想知道对方的反应。
老东山冷淡地说:“要说亲,好事嘛。想找谁家闺女?”
“我爹妈的意思,是想咱们两家,来个亲上加亲。”“嗯!”老东山突然睁开眼,有些惊讶,“和我娴子成亲?”“是,”孙若西谨慎地看着老东山的脸,“是我爹妈的意思,姨父,我自知无才,怕高攀不上我表妹。不过,姨父你知道,外甥虽不种地,也念过一肚子书,教着学,一月挣几十斤粮食,我家也用不大着。我爹在烟台的买卖虽说不太大,也有点门面,家里不种地也过得去。再说,有了教学这个差事,年头好也吃饭,不好也饿不着。再说万一变了天下,也一样干,和铁饭碗一样,破不了。地呀山峦对我一点也不需要……”
老东山的眼睛早又合拢了。孙若西的话多半没进他的耳朵,他心里正在打算盘。对于淑娴这个无爹无妈的侄女,老东山心里不知想过多少回。他想给她找个丈夫嫁出去,但要是个富裕户。这样不会找自己的麻烦,也尽了他对死去的弟弟的责任。不过也不能太富裕了,那样恐怕挨斗争,日子不好过。理想的人家是象他自己一样,上不上下不下的中等家庭。
听外甥孙若西一提,老东山心里活动起来。孙若西在他眼里不是十全十美的人。老东山觉得他不知道干活,话多,好穿戴打扮,淑娴嫁给他,他很可能挑唆淑娴向自己要财产。转念又一想,孙若西是识字人,教学挣死粮;他父亲在烟台有商行,乡下的家产和自己相仿佛;论讲门当户对,自己还逊人一等,不会来要财产。其次,孙若西也是个标致青年,老东山虽说看不惯不种庄稼的人,可是他想现在都兴识字念书,给侄女找这末个女婿,她一定会心满意足,也省得自己费唇累舌。不过,老东山忽然又想起最重要的一件,出口就问:“若西,你属么的?”
孙若西正在猜测对方的态度,被老东山突然一问,一时愣住,怕一字说差,计划破产。他陪着小心探测道:“姨父,你是说……”
“这还不懂?结亲两家的‘属’犯忌,那还行吗?”孙若西心一惊,暗自叫苦:“妈呀!属什么的和属什么的才是和的呀?倒忘了他有这一着。我是属老鼠——啊,不好,老鼠谁都讨厌。我属……”他猛然看到墙上贴着张陈旧的画,上面是只虎,他心里一亮:“虎,画这末旧他还留着,他一准喜欢。”
“嘿,姨父,我有些记不清,刚想起来。外甥是属虎的。”“不对吧,若西?”老东山妻子端上水,说,“我想着你比俺家你儒修哥小一岁,是属老鼠的。”
“不,姨!你记错啦,错啦!”孙若西急忙分辩。“真属虎的?”老东山闭着眼问。
“不错,一百个不错!”孙若西绝口咬定。心想:“老头子,这一下叫我看透你的心啦!”可是对方的回答使他大吃一惊。“哦,不用提啦。”老东山断然地说。
“怎么回事?”
老东山冷淡地说:“俺娴子属小龙①的。”
“这末说——”
“蛇虎如刀锉。”
孙若西懊丧极了,急忙说:“不对,不对!我记错啦,我姨说得对!我属老鼠,耗子。”
“嗯,你二十几?”老东山留起心来。
“二十四。”
“不会错,若西是二十四。”老东山妻子证明。老东山脸上露出点和悦颜色,说:“属相对,小龙和鼠,斗只管斗,可是和善的。”
“姨父,你乐意啦?”孙若西惊喜地叫道。
“我算有意,你和你爹妈说说。
“那用不着,他们都喜欢。姨父,说定了吧!”孙若西迫不及待地要求。
老东山沉着地说:“哪有这末简便的?等看好了日子再立婚约。”
“好好,就听你老人家的!”孙若西毕恭毕敬。孙若西走后,老东山妻子担心地说:“这是个大事,等和娴子商量好再定吧!”
老东山不以为然:“养活她这末多年,这事我还做不得主?”
“如今不是早先,得儿女愿意才成。”
老东山沉吟着说:“也好,不得罪她。我看和若西成亲,娴子不会不……”
突然街上传来惊呼:“不好啦!牛死啦!牛死了一大群……”
老东山象离弦的箭窜下炕,拖拉着鞋就向外跑。
二十几条大牛和犊儿,躺在西河滩的停牛场上,痛苦地翻滚着身子,把脖子伸长,头角向沙里撞,从内脏里发出绝望的嚎叫。牛犊儿蹬着小蹄儿乱窜,眼睛流着浑泪,嗷嗷地直叫“妈妈”。
先后赶来的人们都在牛身旁忙乱着,想尽一切办法去解除牲畜的痛苦和厄运。
牛,一条条绝命了,不到半个时辰已死去十多头!全村三十多条的牛群①在逐渐减少。
人们身上象着了火,虽然落着细雨,阴气逼人,他们身上却冒着汗。有的人冲到牛倌耿老汉跟前,愤怒地吼道:“你他妈的怎么闹的啊!怎么把牛放死啦?”
“你这个混帐的老头子!天一晴就要种豆,正赶这节骨眼上,你这不是要俺们的命吗!”
“耽误了生产,你的罪名多大!”
激烈的怒责声,把耿老汉吓懵了。他抱着一只花牛犊,眼泪直流,一句话也说不出。
曹冷元自己并没有牛,但比谁都来得早,在牛群里逐个地察看。他向大家说:“大伙先别吵吵,别难为老汉。”“老哥,你放过牛,是行家!你看牛到底是怎么啦?”有人问道。冷元有把握地说:“照我看,牛是中毒。”
“中毒?!”人们大吃一惊。
“是中毒。”冷元说,“躺下的牛,嘴里冒白沫,嘴唇子都烧起了泡,不是吃了毒药是什么?”
耿老汉大哭大叫:“冷元老弟,我老汉平常没和你过不去,你这是要我的老命!”
人们齐声叱喝——
“放屁!对坏蛋,不讲情面!”
“正赶上缺劳力,你这老东西下此毒手!”
“牛死在他手里,别人谁能放毒?”
“别说啦,把他送到政府去!”
“妈啊!妈啊!”传来一阵粗哑的哭叫声,只见老东山哭喊着发疯般地向耿老汉扑来。老东山听说牛死了,冲到牛场后,一直和自己的大黑牛躺在一起,抱着牛,在沙滩里打滚。牛断气了,他哭天抢地,直取耿老汉,动手要打;但被人们拦住。他嘶叫道:“你这老东西!赔我的牛,赔我的牛!我和你拼命,拼老命!”他挣扎着向前冲,“上政府!要人民政府惩治你!”
“不要吵!看,指导员他们来啦!”有人叫道。曹振德和江水山、江合急跑着赶到。
人们七嘴八舌向他们报告了情况。
“指导员,振德兄弟!我可没干黑心眼的事啊!”耿老汉拉着振德的胳膊,哭着说,“我放了一辈子牛,压根也没象八路军来了有人看得起,有吃有穿。我报恩无能,怎么会使坏心啊!”
“老哥,放宽心!”振德安慰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政府有眼睛。”
“我信咱人民政府……”耿老汉话没完,老东山怒吼道:“你敢起咒?”
耿老汉指天盟誓:“我要黑良心,天打五雷轰!”
振德向大家喊道:“不要停着,赶快想法子救牲口。”冷元应上道:“用稀粪灌。”
人们急赶回村,从茅厕里挑来粪便,用水搅起稀粪汤,想尽办法向牛嘴里灌。牛吞下粪水,胃肠发作,把吃过的东西都呕了出来。
经过大半下午的努力,挽救出十几头牛的生命,其它将近二十头牛,丧失了!
曹振德几个人,跟着耿老汉顺着今天放牛的路线勘察了一遍。他们在牛群每天必到的牧牛山的一片新嫩的草上,发现了洒在草上的白面。曹冷元抓了个蝈蝈,叫它吃下带白面的草芽,它一会就死了。人们明白,洒在草上的是用面粉掺着的毒药——土信。
“妈的,敌人捣的鬼!”江水山气忿地叫道。
耿老汉又惊吓起来:“民兵队长!我可有良心。”“你有良心,还有没有良心的!”江水山怒目竖起,抓着手枪柄对指导员和村长说:“错不了,是反动派!马上把那几家地主押起来!”
“水山,你又冒失啦!”江合急忙阻拦,指着绿茵茵的广阔的山野说,“牧牛山这末大,多少个村子的牛群都来,也没固定场合,你怎么敢断定就是咱村的人使的坏?有的村子的情况比咱村复杂,也许是别村出的坏蛋干的。再说,咱村真有人想毒牛,为么不在西河停牛场上放毒,跑到这末老远的山上来干?我看还是报告给上级处理吧。指导员,你看呢?”曹振德的脸一直紧绷着。这时他沉思道:“江合哥,先不要把事情看死。敌人不都傻,他们破坏时,也会先想好叫咱们查不出来的手段。不管是哪个村的坏蛋干的,说明敌人没有睡觉。也好,打咱们一巴掌,叫咱们清醒起来。没证据不能抓人。把事情报告给上级。咱们本村也要调查。”“雨下得这末甘贵,看样子明天放晴就得种豆,这可是难处啊!”曹冷元看着天,难过地叹道。
“没关系,老哥!反动派怎么破坏,也挡不住人民向前走,只不过多受些难处罢了!”振德望着在蒙蒙烟雨中的山下的广大田地,信心十足地说道。
接着,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叫江合去区里报告案情;同时立刻派人通知附近各村,防止牛中毒;还叫耿老汉在牧牛山上守候一个时间,不要使其它村的牛群再吃了这片有毒药的草。
细雨不断头地落下来,松树针、梜萝叶、山草发出簌簌的响声。天空灰糊糊的,西边半个天亮一些,云层在逐渐地裂成块块。水气浓重的雾网,顺着山脊,从高处向下游荡——这是要起风的征候,一起风,天就要晴了。
曹振德下了西山,顺着河边的一道山梁上的碎石小路,步履艰难地走着。由于听到牛群出事,他顾不得戴草帽或披上块麻袋皮就跑了出来。此时此际,他衣衫全淋透了,浑身上下,前后左右,里里外外,没有一点干地方,连那双打着补钉的猪皮鞋子也灌满了雨水,一走一噗哧,脚象插进蟹窝里一样了。雨水将他的发茬淋得紧贴头皮,水流淌到脸上,那久未刮过的乱糟糟的胡茬茬挂着成串的水珠儿。振德那因为长期熬夜老是发红的眼睛,现在又浸进雨水,倍加涩痛,他时刻要用手背去揉搓一下。
中国共产党山河村支部委员会书记曹振德,从抗日战争中期挑起负责一个村的工作的担子开始,就一直感到这副担子的沉重。有时完成了一件重大的工作之后,觉得轻快一些了,想舒口气了,猛然,却又会因对突然来临的新事情没有足够的准备而感到受不住,被压得够戗。曹振德不只一次地尝过这种味道。所以,他无论在怎样顺利和胜利的时刻,都自然地留有余地,以备应付新的形势,不致为想不到的事件的来临而慌乱失措,束手无策。
今天,发现了敌人的破坏活动,党支部书记没有感到惊异,不过心里也禁不住说:“敌人可真无孔不入呵!”几年来,山河村没有发生过暗藏敌人的破坏活动,群众和干部也很乐观,正象村长江合刚才说的,山河村的情况不象有的村那样复杂,地主少,富农有限,伪属只有一家。
“毒牛,有没有可能是本村的人使的坏呢?”曹振德在心里问自己。指导员他细细地数了数全村每户人家的社会、政治情况,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