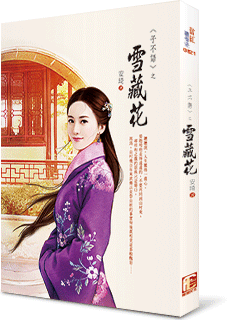迎春花(冯德英)-第5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箭牌,打掩护……明白吗,闺女?”春玲的脸不觉一红,点点头,有些紧张地说:“那咱们快去抓呀!”
“这是我自己想的,还要做调查。搞清也不难,只要弄明白江任保和王镯子的关系,孙承祖回家没有就会真相大白。别的主要干部都在忙支前,咱们父女要快去做工作。你去找任保媳妇谈。江任保,有我。”
“啊,爹!我原以为你在家养伤,可你……”春玲见明轩、明生放学回来了,没再说下去。她掀开锅盖,那乳白色的滚热的水蒸气,立时散满了茅草屋。
按照孙承祖的指示,这些天王镯子经常在大路左右观看有没有公安干事和武装人员进村,以推测干部是否注意到孙承祖身上,预防万一。
这天上午,王镯子提着竹篮子在村后玉米地里假装摘菜豆角,眼睛时时瞟着大路上的行人。忽然背后响起喊声:“谁在那里?”
王镯子吓了一跳。看清是江任保站在地边上,她想不理他,就顺着玉米秆的孔隙向北走。
“啊,不说话,你在偷庄稼?”任保又喝道。
王镯子仍是不理睬。
“我抓啦!”任保威胁迫。
王镯子已经接近地头,见他还不松口,就停住脚,没好气地说:“你没长眼睛!这不是俺自己的地吗?”“哈哈,是你呀,小娘子!”江任保叫着快步钻进地里,碰撞得玉米秸哔哔啦啦地响。
王镯子见江任保衣服底下鼓鼓凸凸地藏着东西,就问:“你拿的什么?”
“嘿嘿!”任保从怀里掏出两个大甜瓜,丢进王镯子竹篮里一个,自己把一个瓜乓一声掰开,大口吃起来。“你这家伙,当贼喊贼,我要报告民兵去啦!”王镯子假意儿威胁着,心想篮子里这个瓜留给丈夫。她伸手夺过任保的一半瓜,贪婪地吃开了。
“甜不甜?”任保歪着头得意地笑着。
“巴苦的。”王镯子想快点叫他走,“你快走吧,别叫人家来抓住。”
“走?”任保嬉笑着,“别人看不到,这一大片苞米一人多深,正是好地方。”
王镯子知道他要来纠缠,又用好话假意抚慰:“你回家等着,我送酒你喝。”
“我不要酒啦,我要你……”任保上去抱住了她的腰。“你滚开,死东西!以后再说。”王镯子急了,任保不松手,她打了他一耳光子。
江任保放开她,气恨地说:“好吧,你对我无意,我对你无情!对你说吧,指导员找我啦!”
王镯子脸变白了,以惊慌的眼光盯着他。
“当然啦,是看得起我!”任保见对方吓住了,异常得意,“昨天晚上,青妇队长还找过我老婆。”
“找你老婆做什么?”王镯子心里发慌,情不自禁地抓住了他的衣袖。
“我老婆说是了解你和我的事。”
王镯子松开手,舒了一口气,毫不在乎地说:“调查去吧,反正我敢做敢当,受什么处罚我顶着。”
“你不要这末轻松。我老婆说,指导员今天上午要找我。”“这我管不着。”王镯子冷笑一声,欲走。
任保见还是制不服她,又大话吹开了:“你不要瞧不起我江任保,我是无产阶级分子!我老婆说,青妇队长对她的态度可好啦!哼,指导员找我也不是为别的,看光景是他们发现了俺两口子是积极分子,要提我上区当干部。”“那你就当吧。”王镯子讥笑着迈开了步子。
江任保急了,拿出了最后一手,恼恨地说:“好哇,娇娘们!好话不听,我也翻脸不认人啦!我要去向指导员坦白,没和你真私通……我去,我就去!指导员救济我,待我好,会宽大我说过的假话。我听他的,做好人,不叫人家骂啦!”王镯子大惊,骇然地想道:“天哪!他照实说出去,干部一审,查出我的肚子,馅就露了!怎么办?嗳呀,和他……承祖也有话在先……他也和孙俊英勾搭。只是任保这个丑相……管不得啦!”王镯子下了决心,严厉地说:“任保!以前我想和你好,只是嫌你不牢靠。如今你有心,那就要真好!你得听我的话……”
孙承祖望着神色不安、头发不整的妻子,眼睛恶凶凶地瞪了一会,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壳,沮丧地说:“完了!完了!我要赶快走,跑……”
“不碍事,”王镯子还有信心,“任保得着我这样的女人,象苍蝇沾着血。他满口应承,曹振德问起时,他一口咬定和我早有来往,枪毙他也不改口。你放心吧!”
“哼!瞒得过别人瞒不过曹振德!”孙承祖的瘦脸变得铁青,“他的嘴比枪弹还歹毒!连你妈都被他打动了心,何况一个反复无常的江任保。经不起曹振德的舌头动两次,江任保就会把肚子里的东西全倒出来。你失身也是白搭!”王镯子悲哀地抹开了眼泪。
“快给我备干粮!”
“别急。我看你再到刮地皮家里躲几天,看看动静再说。”“不行,我想过了。他们一直没再来联系,即使不出事,也准是被人家监视上了,我怕自投罗网。有你哥的例子在先,不能等挨闷棍。我马上动身,先溜进房后的玉米地,等天黑就上路。一步晚了,曹振德的网就撒下来啦!”“那你得领着我!”
“这怎么行?我一个走都危险!没关系,你一个女人家,多哭几声,把错都推在我身上,共产党不会怎么难为你。你咬着牙忍几天,国军的重兵正向这里进攻,到那时重见天日,报仇雪恨!”
“你要早点回家,千万不要丢了我啊!天哪……”王镯子大哭起来。
春玲在村公所见到儒春的来信,心都快冲出口了。她跑回家扪着心窝躺在炕上。过了好一会,才使激荡的心平静了一些。她用剪刀小心地将搓毛了的信封口铰开,仔细地读着:春玲同志:你好!
这些日子我早想托人给你写信,可又压了下来。
因为我暗下决心,要加紧努力,做出一些成绩,再写信给你。我这末做,你生气吗?请你批评我,原谅我。告诉你,我已经参加了好几次战斗,打死两个敌人,抓了四个俘虏,还缴了五支枪,受到俺营长的表扬。我告诉你这不是为表功,我知道,自己做得很不够,比别的同志相差一大截。我的心意是让你放心,我正在上级和同志们的教育帮助下,使劲进步哩!我要和你比赛,向你学习。
俺们部队的生活可好啦!大家亲兄弟一样热乎,又唱又跳,又打又闹,还学习文化和政治。再住几个月我要自己写信给你看,你可不准笑话我写得不好,先打个预防针。现在我们在胶济铁路一带,天天行军作战。
这信是我找班长写的,我们这时正坐在草地上休息,擦枪,一会就开始行军,不能多写了。我真想知道你对我要说的话,一定很多,是吧?我爹还那末顽固吗?你把我的事告诉他吧,要他赶快换换脑筋。盼你回信,祝你健康。
此致
敬礼
儒春上
七月二十一日
欢悦和幸福使姑娘不知怎么好。跳了半天,就拿着信往老东山家跑。来到门口她才想起,公公赶着牲口和村里一些人去送公粮了。她把信的内容告诉了婆婆和嫂嫂,大家自然都欢喜异常。春玲立即给儒春写回信,勉励他努力杀敌,告诉他老东山的转变,表白一番她对他赤诚钟爱的心……写了半上午,还没把心里的话说透。天正晌了,明生已经放学来家吃饭。春玲把饭打点进锅。吩咐小弟烧着火,她扛起扁担出了家门。
正是吃午饭的时候,原野里没有人了,春玲却扛着扁担向西山走。她父亲整天忙着工作和生产。明轩除了去外村上半天高小,下午也象个大人似的在互助组里劳动。明生的半天时间,得给牲口割青草。春玲是工作、家务、生产样样都有份。全家忙得柴烧光了也没工夫去山上挑。自孙俊英被群众正式罢免后,大家一致选举春玲为妇救会长,青妇队长选了彩云姑娘。春玲今上午先忙着收齐各家为军队磨好的面粉,又给儒春写了封回信,这时抽出身,赶着上西山挑担柴回家。春玲心里萦回着当人民战士的未婚夫的来信,眼睛一时也不闲着。她看天,艳阳炽烈,蓝得透明,朵朵的白云,迤逦多姿。她望庄稼,乌森一片,香气扑鼻,日渐成熟,但等金风,粟米归仓。
春玲上了山,曲折的山路,节节上升,通到山顶。蝉在树上叫,蝈蝈在草下鸣,蜜蜂在花上飞,蚂蚱在地下蹦。天是如此明媚,山川是如此娇美,年景是如此大好,使姑娘心神向往,目不暇及,竟忘记即兴编歌唱了。
春玲登上一座山梁,满面绯红,眼睛被强烈的阳光刺得眯眯起来。她看见一对花蝴蝶在飘飘悠悠地围着山菊花转,立时跑过去,将菊花采下来,对着那惊飞而去的蝴蝶说:“不高兴吗?有意见提吧,这花春玲是要戴的!”她搂着扁担,向发针上插一朵小白菊花——她忽然停住了,眼睛直向前方瞪着。
春玲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穿绿褂的女子,在路旁那陡峭的山壁上徘徊。她立时忖道:“奇怪,那人在干什么?一不小心摔下去,骨头也零碎了。”春玲急忙向那里奔去。
春玲跑到近前,听见那女子在抽抽搭搭哭泣。由于松林密集,她认不出是谁。忽地,那女子把篮子向后一摔,身子更移近绝壁的边缘,如果她拽着松树枝的手再放开,身子即刻要栽下去。
春玲惊出一身虚汗,刚想叫——又忍住:那女子一惊,更要跌下去了。她急忙脱掉鞋,赤着脚丫,悄不声地顺着陡坡冲向崖边。尖利的石头、棘针、草茬,碰刺得姑娘的脚疼得要命,但她咬着牙忍住,只顾往下快跑。
正当那女子手脱松枝,要向绝壁下跳去时,春玲象只燕子似的抢上去,两手奋力地抓住她的胳膊,猛向后拉她。两个人一齐向后仰倒在山坡上。她们的脚下搓起的石头,飞蹦着滚向深沟。
那女子从惊吓中醒来,向前挣扎着叫喊:“放开!放手!”
春玲紧张地拼全力地用脚蹬住树根,使她们不致一齐滚下去。她急声叫道:“淑娴!你……”
那女子忽然停住,转回头惊呼道:“啊!春玲……”“你这是做什么,快上来!”春玲眼睛潮湿了,用力向上拖她。
淑娴哭着说:“好妹妹!别管我。”她又向崖边冲。春玲赶到她面前,堵住去路,着急地喊道:“淑娴姐!是人还能见死不救吗?你,你这末傻!”
淑娴直直地看春玲一霎,捂着脸嚎啕起来。
“快走吧,这地方不是好玩的!”春玲把淑娴拉到路旁的树荫下坐好,这才看清,淑娴的眼睛肿得和熟透的桃子一样,前襟湿了一大片。
春玲掏出手绢给她擦着泪水,怜悯地问道:“快告诉我,淑娴!你这为的什么呀?”
今天吃完早饭,淑娴和正要出发送公粮的大爷老东山商量,要去儒春的姨家走亲戚。她是以走亲戚为名,去找孙若西的。
孙若西自从调到他本村任教后,很久前来照过淑娴一次面,以后再也没见影子。淑娴越想越不安,最后鼓足勇气要去找他一趟。
“拿上点饼和鸡蛋。你催催他,好日子也过了,打算多会成亲。我忙着,没工夫去。”老东山嘱咐道。
淑娴跑了十几里路,来到儒春姨家的大门口。她不由地惊住了:那漆黑的大门板上,贴着刺眼的崭新的红对联——德高望重书香门第青春儿女喜结红姻门上,墙头上,贴着红纸墨笔大喜喜字。淑娴虽然认不全上面的字,但是它们所表示的意思她是心明如镜的。这就是说,孙若西正在办或已办完喜事了,因为他们家再没别人能结婚。
“我没走错门?不错,是他的家……这,这怎么会呀?”淑娴心里狂乱地叫着。她站在门口,全身麻木,象站在冰窖里一样寒冷。她痴呆呆地,愣怔怔地站着,眼睛发黑了。她隐约地听到身后响起话音:“瞧,这是谁家的闺女?”“哦,是不是孙先生他姨家的人?”
“对,想必是来吃喜酒的,明天是孙若西的好日子。”“呀!姨家到底是近亲,老东山赶早打发闺女来帮忙,明天他自个也准来。”
“那还能少了他?”
“那老头子见外甥娶了个门当户对,在烟台上过学的大闺女,一准喜得合不上嘴。”
“那还用说!”
淑娴的心象有钢刀在剜,眼泪禁不住夺眶而溢。她转过身,迷迷糊糊地看见两个女人站在井台边指着她发议论。淑娴再没力量听下去,迟钝地顺着来路往家走。
姑娘迈着沉重的两腿,眼睛无神地看着倒在地上的自己的影子。她一直被悲怆塞住,神情有些恍惚。她不知想些什么,想了没有;也不知走向哪里,走了没有。她的整个心胸,一再响着两个字:“完了!完了!”
春玲听完了淑娴的叙述,气恨地皱起眉尖,板紧脸面,忿忿地说:“犯得着吗?淑娴姐!为他那末个东西值得送命吗?照我说这是好事,苦枣当甜的吞下去,上当只一次,认清坏蛋再不受骗就是啦!那样的人,离得远远的才对,不值得正眼看!”
淑娴嘴唇搐动了好几下,哽哽咽咽地说:“妹妹呀!俺上当啦!”
“是呀!”春玲看着她,恳切地劝慰道,“淑娴姐!不是我多嘴,老爱批评人。你性子那末软,怎么行呢?既然孙若西那样狠心,还有什么值得哭的?我真替你难受,本来对水山哥那末好,就架不住碰钉子,经不住孙若西的甜言蜜语,心就随他了。你可真没见识。好啦,把泪擦干,吐口唾沫,呸,忘掉他算啦!”
“我恨他一辈子!”淑娴低下头,咬着牙,揩着不断头的眼泪,“他害我……我没脸见人……我……不要脸的他,还,抱过我……”
“那个该死的东西,真该死!”春玲骂了起来,“好,你也别太认真啦,算换了个教训!”
“春玲啊,你看我,自己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人家知道了,再怎么过下去啊!”淑娴悲伤地说,“我再没希望啦,一辈子算糟蹋啦……”
“淑娴,我又责备你,为这些事寻短见,那是旧社会里的人做的。可现在,你,你太没出息啦!”春玲恳切地对女友道,“人活着哪里是光为自己的事?你要想得开,看得远。咱们不光为自己活着,要为大家,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