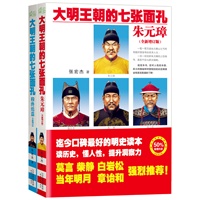秃头旅馆的七把钥匙-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写的不真实,呃,其实作者就是我——”
“噢!”女子惊讶地喊道。
“是的,”马吉说,“而且我还写过其他类似的小说。哦,我的灵感来自于一位穿沃斯牌长裙的暴发贵妇人,我的野心是拥有一辆红色跑车。我是站在书摊前的一个行吟诗人,向过路人说:‘给一分钱,先生。’写那类东西很好玩,而且也让我赚了用不完的钱。对此我不感到丢面子,因为一上来就写这些没什么不好。但有一天——我想可能是一则广告的原因——我突然对那类小说厌烦了,决定换一种写法——写真东西。我本以为是一则广告让我改变了想法,现在我才明白其实是两天前你的一番话。”
“你难道是说,”女子低声说,“你上山来是为了——”
“没错,”马吉笑道,“我来这儿是为了彻底忘掉令人头晕目眩的离奇情节,忘掉在无人住的屋子里争夺珠宝的角逐,忘掉夜间的枪声和编织的情节中穿插的爱情。我来这里是希望——创造文学,如果我身上有文学细胞的话。”
女子无力地倚在秃头旅馆的墙壁上。
“哦,真是命运的嘲弄!”她大声说。
“我知道,”马吉说,“这很滑稽。我想这里发生的事都是为了引诱我。我决不能动摇。我要记住你讲的盲人姑娘的故事——那盏没点燃的灯。我要写出货真价实的东西,以便当你哪天说——这句话你肯定会说——‘我是比利·马吉的女友’时,你可以骄傲地说出。”
“我相信,”她悄声说,“我要是真说出这句话——哦,不,我的意思不是肯定会说”——因为此时他立即抓住了她的手——“我要是真说出这句话,肯定会带着骄傲说出。可现在——你甚至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我真正的名字。你不晓得我干什么,从哪里来和为什么想要那个讨厌的金钱包裹。我总觉得——你的行为是秃头旅馆的气氛使然。即使冬天也是如此。男人们脚一踏上这块地方,无论碰上哪个女孩儿,就开始谈情说爱,而且就在这个阳台上——在那片树下。女孩子们就听凭他们谈,因为气氛就是这样。然后秋天到来,人人大笑一场,忘得干干净净。我走后,我们的秋天是不是也会接履而至?”
“绝对不会,”马吉大声说,“对我来说,这不是一种消夏的嬉戏。这是真正的冬夏之恋,亲爱的——也是春秋之恋——你离开后,我也跟着走,只在你身后十英尺。”
她放声笑道:“他们在秃头山也这么说——尤其在夏天快过去的时候,这是游戏的一部分。”他们已走到旅馆的一侧,连接配楼的地方。女子收住脚,用手一指。“瞧!”她呼吸急促地轻声说。
配楼的一扇窗子里闪过一束摇曳不定的烛光,宛如白驹过隙,倏然而逝。
“我知道,”马吉说,“那边有个人。不过相比之下他现在并不重要。这决不是夏天的游戏,亲爱的。现在的温度表就是证明,我爱你。当你走时,我也会随之而去。”
“那你写的书呢——”
“我找到了比秃头旅馆更好的灵感。”
他们在缄默中走了一会儿。
“你忘了,”女子说,“你说你知道钱在谁手里。”
“我会得到的,”他自信地答道,“我本能地觉得我会得到。在此之前我不想多说什么了。”
“再会,”女子说。她站在她房间的窗前。一个沙哑的声音从屋里叫道:“是你吗,宝贝儿?”“我想再说一句,”女子莞尔一笑,“干我们这行的,最喜欢有跟在身后的崇拜者。”
女子返回房间。马吉先生在自己的房间里逗留了片刻后,再度下楼进入办公室。房子中央,伊利亚·昆比和海顿站在那里,四目相视。
“怎么回事,昆比?”马吉问。
“我上来想看一眼这里的情况,”昆比说,“没想到遇到了他。”
“我们新来的一位客人。”马吉笑道。
“我正帮着海顿先生回忆我俩最后一次见面时,他勒令我走出他的办公室的情景。”昆比说。他牙关紧咬,眼里射出愤怒的光芒。“我对你说过,马吉,市郊铁路公司曾答应安装我的发明。后来坎德里克走了——由这个人负责。我再次去他们的办公室时,他嘲笑我。后来我又去找他,他管我叫二流子,让我出去。”
他顿住,再次瞪视着海顿。
“我来到山上以后变得更加愤怒,”昆比说,“每当我细想你和你那帮人对我说过的话,想到事情的结果本应不致这样,我就愈加愤怒。在你办公室里发生的情景总是不断地在我脑海中浮现。我坐在这里,想着你就代表着那帮把我当傻瓜耍的人;那帮人冲着我耳朵嚷道:‘让公众的利益见他的鬼!’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是怎么把我撵出你的办公室的。”
“你要怎么样?”海顿说。
昆比说:“现在形势掉了个个儿.你现在擅自闯入我所管辖的旅馆,我也该轰你出去,把你撵走。”
“你试试看!”海顿不以为然地说。
“不,”昆比说,“我并不打算这样做。也许是由于我过多思考我的失败,变得胆怯了。也许是由于我知道第七把钥匙在谁手里。”
海顿没有回答。屋里的人都沉默着,半晌,昆比迈开脚步,从餐厅门走了出去。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上一页 下一页
第十五章 餐桌漫谈
第七把钥匙!提到它马吉先生便异常激动。由此看来,伊利亚·昆比知道躲在配楼里的人以及他来此地的目的。还有别的人知道吗?马吉看向各个人的脸,市长的硕大宽广;迈克斯的干枯蜡黄;布兰德的惶悚而沉思;海顿的忧虑而挂着笑容。还有别人知道吗?啊,是的,当然还有这个人:比较文学教授为觅食而从楼梯上走下来。
“晚饭好了吗?”他四下探头探脑地问。
烛光在与强大的阴影的抗衡中微弱地闪烁不定;冬季的狂风呼啸地吹打着窗梭。楼上某个房间的门咣当一声关上了。秃头旅馆的戏剧已进入最后的一幕。对此马吉先生觉察的出,但说不出缘由。别人对此似乎也有所预感。隐士在昏暗的光线中跑前跑后准备着晚饭,众人在沉默中等待着。俄顷,诺顿小姐和她母亲走下楼来。随后桑希尔小姐和海顿在楼梯脚邂逅,引起一阵小小波澜。
“米拉!”海顿喊道,“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
“很不幸,”那个女子说,“我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于是海顿遁入阴影之中。
最后,隐士做出的姿态表示,晚饭已经就绪。
“我看你们可以入席了,”他说,“能做的都做好了。此处一个厨子招架不了,需要设立个伙食科。”
“彼得斯,此话对我们的客人不大礼貌。”马吉嗔怪说。
隐士站在餐厅门口说:“一个人单独住在山上养成了崇拜说实话的习惯,顾不得什么礼节,想摆出彬彬有礼也做不出。”
冬天的客人们一一入了席,于是十二月间在秃头旅馆的第二顿晚餐正式开始。然而餐桌上的气氛并不像头天晚上那样融洽和谐。马吉先生留意到担忧和猜疑的神情,恫吓阴冷的目光时不时移到他身上。不言而喻,困扰就餐人的首先是那个装满金钱的小包裹,而且显而易见,他们中的多数人都以为,包裹就在马吉本人的掌握之中。他几次抬头,都看到迈克斯用猫似的目光盯着他,后者躲在不相称的金丝眼镜后面的一双贼眼邪恶而凶残。海顿充满敌意和愤怒的目光也偶尔向他扫去。这些人已急不可待,随时会铤而走险。马吉先生感到剧终的帷幕快要拉下时,他们把他一个人看成了阻碍他们攫取财宝的绊脚石。
趁汤撤下去之时,卡根开口说:“我来山上当隐士之前——顺便说一下,由于秃头山上玩乐的东西很多,我当隐士的愿望肯定实现不了——我来这之前,吃饭的餐桌上从来不点蜡烛。我把蜡烛都留给了海顿先生那类乐意在阴暗的环境中工作的人——我这人最主张吃饭时把吃的照得灯光通明。我害怕的是把这个习惯带到山上来,让查理给我备一盏银制分枝大烛台,照耀着我的啤酒。那样一来,查理的店就得设计一些新颖的蜡烛了,是不是,卢?”
“查理的店点蜡烛未免太漂亮了,”迈克斯先生说,“除非关门以后。关门后我见过他们用过,不过不是为了点缀和装潢。”
“卡根先生,但愿你不要讨厌蜡烛,”诺顿小姐说,“它们可为浪漫的事情增添无限光彩,你说是不是?我见到烛光就激动不已。窗户哗哗作响,烛光摇曳网烁,不禁让我总想到两行诗:
爵爷尾随朝他耳语的人走去——
我听到的唯有风声和蜡烛的哭泣。
我不晓得爵爷是谁,也不知他尾随的是什么——或许是第七把钥匙。但风声和蜡烛的哭泣却是何等浪漫,多么像今晚的秃头旅馆。”
“我要是有个与你同龄的女儿,”卡根不无善意地说,“她定会在家里的火炉旁读劳拉·简·利比,而不是在一座山上追求浪漫。”
“我相信那样对她最好,”女子甜甜地说,“因为那样的话她就不可能发现她父亲的一些事,惹得她心里不安。”
“亲爱的!”诺顿太太叫道。接着没有人再吱声,大家都看着市长,他却埋头只顾吃。马吉先生开心地笑着,设法把谈话引到与隐私无关的话题上。
“我们听到大量的关于浪漫的谈论,尤其在媒体竟相断言浪漫已经死亡之后,”他说,“我见到的每一个人,都对浪漫持不同的看法。卡根先生,你是个见多识广、宽宏大量的人,对浪漫的含义有何高见?”
市长用手指捋了一下灰发,沉吟片刻。
“浪漫,”他嗫嚅着,“我的想法与书本上说的大不相同。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是这样的。这是选举日的前一天夜晚,我站在主大街一间小屋子的窗前,我的小伙子们总能在那儿找到我。我听到街上传来震天响的奏乐声,一会儿便看到了黄澄澄的火炬,就像闪烁不定的蜡烛,还有上下摇摆的旗帜。接着,小伙子们列队而过。所有的小伙子们!帕特·多赫提、鲍布·拉森、迈特·桑德斯——所有的人!他们走到我窗前时,挥动帽子向我致敬。我只不过是个站在窗前的胖老头儿,但只要有谁反对我,他们就会把他拽到大街上较量一番。他们非常忠诚,完全拥戴我。他们就这样游行而过——歌唱和欢呼——所有的人——只是为了让我听见和看到。咳,这对我来说就是浪漫。”
“是权力。”马吉解释说。
“是的,先生,”市长大声说,“我知道我赢得了他们,他们是属于我的。世界上的改革者加在一块儿也摧毁不了我当时的振奋。我想老拿破仑对这种激动心情是不陌生的。我觉得他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浪漫者。当他与他饥寒交迫的弟兄们行进在山上,他回头看他们穿着破衣烂衫,历尽磨难时,我看老拿破仑就是在经历最伟大的浪漫。”
“天晓得,”马吉说。他猛然意识到,对这个扑朔迷离的概念所做的定义中,也许能暴露每一个人的性格和职业。在餐桌的尽头,他的目光落在诺顿太太饱经风霜。疲惫不堪的脸上。于是他把定义浪漫的话题交给了她。
“噢,”她说,嗓音似比往常柔缓一些,“我已经多年没有想过这个词的意思了。可一旦想起来,就仿佛看到我自己三十年前坐在我家的游廊上。我当时穿一身小巧玲珑的薄纱裙,一副亭亭玉立的身材,脸上的颜色么——就是诺顿最爱看的那种。至于发型——可我想到了他,诺顿。他对我说他要让我一生幸福,当时我差不多快要决定让他试一试了。我看到他——从我家前面的人行道上走来。来看我——我刚才说我身材特苗条、特迷人了吗?我心目中的浪漫就是这个。”
“是青春,亲爱的?”诺顿小姐柔声问。
“说的对,宝贝,”老女子似在梦境中说,“青春。”
一时间,桌旁的人都静默下来,无疑都在各自想像着多年前坐在游廊台阶上的那个苗条淑女。他们偶尔朝那个诺顿曾乞求使其幸福的女人瞟上一眼,怜悯的目光中掺杂着几分讥讽。比较文学教授首先打破了沉寂。
他学究气十足地说:“字典把浪漫定义为一种小说写作文体,最初起源于罗曼方言,后用于散文体。可是字典枯燥乏味,没有灵魂。我能否把我对浪漫的理解说给诸位?我这就说。我看到一个人在阴暗的实验室里辛苦劳作着,那里有奇异的火花和难闻的怪味。他夜以继日地做着试验,眼中流露着一种特有的爱,心中怀着助人的欲望。后来黄金时刻到来了,那个宁静乏味小屋里的伟大时刻——发现的时刻——到来了。血清处方,或类似的东西被发现了。他把发现献给了世界,一些病倒的人于是重新康复了,一些悲伤的人展开了笑颜。浪漫在我看来既不是权力也并非青春。它意味着——奉献。”
他将黯淡无光的眼睛垂下,注视着食物,马吉先生以一种新的诧异目光看着他。这个老家伙从壁炉旁盗走包裹,从隐士手中夺走钱财,还在配楼的门口深夜与人密谈,却竟然能发出这样的感慨。马吉愈发觉得困惑和着迷。这时迈克斯先生斜眼睇着桌面,也大杀风景地发表起见解。
“这事真逗,”他说“一个词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思。要是跟我提浪漫,我决看不到灰不溜丢的实验室。浪漫不是昏暗,而是世界上最晃眼的灯光,最好吃的菜肴,餐桌之间还得有人跳最时髦的怪舞。远处有乐队伴奏,性感的妞儿走来走去,一会儿门口哧一声停住一辆出租车,我便叫人捎话给司机:‘车就停那儿等,早上送牛奶的车来了再走——我付得起钱。’咳,这才叫做浪漫。”
“海顿先生,”马吉说,“我们能不能听你说两句?”
海顿踌躇着,朝米拉·桑希尔的黑眼睛看了一会儿。
“我的想法经常遭到反驳,”他说,目光仍盯住桑希尔,“这次还可能惹起非议。不过依我的看法,世间最伟


![快穿之我的七十二变女友[gl]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18/1839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