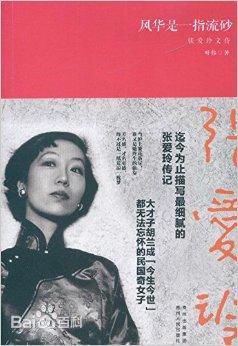一指观音-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要找也找不着了!所以,这个钱是非花不可的。”
袁世民:“照你这么说,再过他一百年那不……”
袁之庆:“就成了文物了呗!”
袁世民:“我说你这个民兵连长啊,当得还真称职。”
袁之庆:“还不是你这个队长领导有方啊!”
说完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袁世民:“对了,你那囡儿这两天怎么样了?”江南一带的方言,女儿叫“囡儿”。
袁之庆:“哎哟,这个小东西,可把周凤整惨喽。”
袁世民:“又咋了?”
袁之庆:“上个星期刚出的院。”
袁世民:“就是那叫什么的……”
袁之庆:“肠套叠。”
袁世民:“什么希奇古怪的病,我们乡下人听都没听过。你们城里人的孩子也就金贵,生个病吧,连个名字都希奇古怪的。”
袁之庆:“别说你了,就连我和周凤都没听见过,也算让我们长见识了!那见过刚两三岁那么一丁点儿大的小东西,就动手术了!”
袁世民:“这两天又咋啦?”
袁之庆:“说是奶疳,吃啥拉啥。把个周凤闹得没日没夜的,人都瘦了一圈了!”
袁世民:“快叫周凤把孩子抱给她们村的仁通伯看看,他可是个‘百晓’,让他瞧瞧,保管马上就好。”
袁之庆:“对,我怎么就忘了!刚生下来那会儿,全身蜡黄,简直成了‘黄帝’了,医生说是先天性黄疸,慢慢会退掉的,就是仁通伯给抓的几帖草药,一吃就退了。我回去马上叫周凤把她抱到仁通伯那里去。”
袁世民:“你爸知道你生了个囡儿了吗?”
袁之庆:“知道,就数他最高兴了!说是我家几代都生男孩,到我这儿才生了个囡儿,是喜事,整天大包小包地往这儿寄东西,还整天闹着要照片呢,简直一个老天真。周凤哪有空啊?”
袁世民:“瞧你,说到女儿就来劲儿了!快三周岁了吧?起名了吗?”
袁之庆:“起了,周岁时就起了。世民叔,我说了你听听,行不?”
袁世民:“行,我听听。”
袁之庆:“这小可人儿啊,长得跟周凤一模一样,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袁世民:“那干脆也叫‘凤‘得了!”
袁之庆:“哎哟!世民叔哎,咱俩可想到一块儿去了!”
袁世民得意地:“要不还讲什么‘英雄所见略同’呢?”
袁之庆:“对,我干脆随了周凤的名字,给她取了个叫‘晓凤’!”
袁世民:“哪个‘小’?”
袁之庆:“拂晓的晓。”
袁世民:“好名字!又好听又好叫,意思也好!‘一日之计在于晨’嘛!又是凤凰,以后飞得高高的远远的,好,好,好!”
袁之庆:“那我就不改了,定下了!”
袁世民:“当然不改了!”
中心小学办公室里,丽珠与周凤坐在一块儿正说话。
周凤:“你说这个孩子,真是我前世的冤家,难产差点要了我一条命还不算,你看刚生下那会儿,先是先天性黄疸,后来又是什么肠套叠,听都没听说过,幸亏,那段时间我正在省城我妈家,不然,还不知那条小命保得保不住呢!前两天又是什么奶疳,牙床和两颊都烂了,还有脓和血……”
丽珠:“现在呢,好了吗?”
周凤:“唉,当时,可真把我吓坏了,后来,还是我们村的仁通伯给弄好的。”
丽珠:“那就好。”
周凤:“你说,这样的孩子,把她送给了别人能放心吗?”
丽珠:“我早跟你说了,到底是自己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啊,能说送就送掉吗?”
周凤:“唉,只是冤了之庆了!”
丽珠:“之庆知道吗?”
周凤摇摇头:“比自己的还宝贝呢!”
丽珠:“你听我说,他们两个都不知道,除了之庆,再不会有人更爱这个孩子了,只要你真心爱之庆,养大了也是一样的。”
周凤:“唉,也只好这样了,现在,就是你叫我把她送出去,我也舍不得了。”
丽珠:“行,这不就结了。”
瑞芳的小酒店里,瑞芳的老公仕才,坐在柜台边,阴着脸,不说话。
瑞芳:“又咋啦?你看你那个脸,拉长了像条三角裤似的。”
仕才:“你才三角裤呢!你那三角裤不是拉长了;而是拉下了!你说,昨天他又来干吗啦?还是福成找他吗?”
瑞芳:“你说你这个人怎么……怎么这么粘呼呼的?不早就跟你说清楚啦!什么人又在你跟前嚼舌头根子啦?你把他叫来;我来跟他说!”
原来;这吴蜡经常来跟瑞芳幽会;天长日久的;瑞芳老公自然就有所察觉了!先跟瑞芳闹了几回;瑞芳自知理亏;倒也认错只是照常还是藕断丝连。这吴蜡还是独身;瑞芳嘛;等于也是独身;只不过多了个监视的人;两个人偷偷摸摸地;那滋味比那两夫妻还要恩爱呢!后来,瑞芳反客为主,干脆“猪八戒倒打一耙”缠着要老公跟她房事,那仕才那是她对手呢,自然败下阵来。
瑞芳趁势跟他论理,提出要离婚,这一手是瑞芳的杀手锏,这招一使出,仕才只好讨饶了。这件事要是传了开去,还要得吗?瑞芳是个聪明人,她本也不想这样,仕才一讨饶,她也就见好就收了。她跟仕才说:“人家以前连典都还要典呢?现在解放了,不作兴这一套了,你想典也不能了。”
仕才:“那典是我去典人家,可我现在算什么呀?”
瑞芳:“嗨,说你傻瓜,你不爱听,不说你傻瓜吧,尽说傻话。”
仕才:“怎么傻啦?”
瑞芳:“我问你,你去典人家,你还真能跟她生一个出来?”
仕才无语。
瑞芳:“你要能生,我去帮你找人,保管不吃醋,不吵闹,行吗?”
仕才低下了头。
瑞芳:“这不就结了!你不能跟人家生孩子,到头来,这个孩子跟你不亲,跟我更不亲,将来要闹的事还免得了吗?”
以前农村里为争财产,房族里的人,不承认那种女人不住到承典人家里的孩子的事是常有发生的,俗话说“隔重肚皮隔重山”,也有丈夫典了孩子,妻子不喜欢而闹事的,可谓比比皆是,仕才一个土生土长的江南人,听得还少吗?能不知道吗?仕才叹了一口气。
瑞芳:“你也不用叹气,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有了!能生下个一男半女的,总是我的亲生,到时候,还怕没人乖乖地叫你‘爸’?是儿子,咱死了,有人替咱戴三联冠,是女儿,棺材横头也有人哭哭热闹。”
仕才:“真的?”
仕才仔细想想瑞芳的话,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与其弄个两个人都不亲的回来,还不如让瑞芳自己生个下来,用瑞芳的话讲,真的还怕他不叫我‘爹’!
套用一句章回小说的话“各位客官”啊,人这个东西,可是最讲不清楚的了,仕才他自知无能,也只好退了一步讲话了,他也明白,即使他把瑞芳离了,再娶一个,能保管不再发生这样的事吗?合法合理的事,固然冠冕堂皇,可那都是只放到书里和摆到桌面上讲的,在现实的生活里,有许多东西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够讲得清楚的。瑞芳红杏出墙,固然可恨,可是,这能怪她吗?她从不跟人透露仕才有性功能障碍,替他遮掩,就是怕家丑外扬,这一点,仕才岂是傻瓜,能不知道吗?从此以后,吴蜡来家,仕才反而倒怕人发现,总是替他们遮掩了。瑞芳见他这样,心中反倒存了一份感激,到底她还是不想拿自己的名声开玩笑的。
仕才:“那我跟你说,等到三四个月,你就住到你母亲家去,就说你母亲病了,要你去服侍,等孩子养了下来,对外就说是我们自己生的,对他就说是我们抱来的。反正不能让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
瑞芳一愣,心想:真要说他傻,还真不傻呢!只是这半年多时间再也见不到吴蜡了!
瑞芳:“好吧。就依你说吧。”
半年后,瑞芳在娘家生下了一个女儿。
以后,吴蜡也还是常来,也经常给仕才一些钱,仕才虽说不是为了贪这几个钱,一来,家丑不可外扬;二来,得了他的钱到底不太好开口;三来,也是最主要的,那就是他自己是“关公卖豆腐——人硬货不硬”;所以,他还像以前一样,总是替他们遮掩着。但是,当王八的滋味能好受吗?所以,隔三差五地仕才总会这么闹他一闹,瑞芳也总是软硬兼施,好言相劝一番。她心中恋着吴蜡,只怕他腻了她另寻新欢,所以,从不把仕才闹腾的事告诉他,每次来,也总是好酒好菜地款待。那吴蜡因自己破了瑞芳的瓜,心中再不把瑞芳看成一个轻薄女人,加上瑞芳善于察言观色、又知冷知热,遇事她也有杀伐决断,该挑肩子的事她也从不扭扭捏捏,他倒把她看成了自己的红颜知己,恨不得娶了家去。有一段时间甚至连周凤也不去多想了,只把心思用在瑞芳身上,每次相会,总有一种“久别胜新婚”的甜蜜劲,两人是愈来愈难舍难分了。
昨天,吴蜡又来了,两人关起门来,吴蜡一直到半夜才回去,仕才越想越窝囊,所以今天一早起来就跟瑞芳闹起来了。可是等到这瑞芳一高声起来,他又蔫了。
“女儿有什么用,到时候,还不有场闹!”仕才压不过瑞芳,只好拿女儿说事。
“什么女儿儿子的,不都是眼眉毛画画好看的啊,你不要隔三差五的闹,命中有子,还怕生不来啊,前次江南殿的钱瞎子说了,我是先开花后结果,说不定接下来就是儿子了也不一定。”
仕才听说能养儿子,自己先软了一半,不敢多说了。在江南农村里,以前婴儿的出生率是不低的,但是成活率却不怎么高,天花、麻疹、小儿麻痹症、七日风、蛤蟆撑等等,就连感冒有时也会要去一条小命,可是解放后,医疗防疫搞好了,农村也有了医疗单位专门负责防疫接种,死掉小孩的事也越来越少了。仕才心想,只要生下了男孩,自己就有后了,人前也直得起腰了,到时候,吴蜡再想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再说,他总不能老不成家吧。瑞芳见他不吱声,知道风雨过去了,也不去管仕才他心里到底想什么,自己出去有事去了。
这天早上,吴蜡起来,准备到茶场去。自从吴茗和陈娇双双死后,吴蜡到茶场去得少多了,一则睹物思人,揪心得很,二则,那陈武自他姐死后,见着吴蜡总是不冷不热地,让人心寒,他本想把那个可怜的小侄子抱回来养,可是陈武死活不让。茶场因那小孩是吴茗遗孤,父母双亡,陈武现在抚养着小孩,就让陈武住进了吴茗原来的房间,并给陈武安排了一个长期临时工。这事虽说不怎么符合政策,但是,吴茗生前人缘极好,自然,不会有人拿这事儿说事;再则,吴茗夫妇双双身亡,这房间,陈武不住也没人敢住;三来,陈武在茶场是临时工,不过是长期的罢了,不占什么居民户口名额,这样,陈武就在茶场住了下来。以前,吴茗在时,吴蜡一来茶场,自然就到吴茗这里来,好象来自己家一样,而现在陈武这里他就不怎么来了。
这个吴蜡,虽然书读得不多,可是人却真是个人顶上的人,特别聪明。什么事到他手里,总是干得有门有道的,茶场里有什么难题,一到他手里就迎刃而解了,他接的茶园坎,工夫特别地道,不但牢固而且美观,所以,一到农闲,茶场搞茶园基本建设时,总少不了要请他来,人家农闲挣不了钱,可他农闲反而忙不过来。茶场的茶厂里有两台柴油机,茶季一到,整个茶厂离不开柴油机,以前,城里知青没来的时候,都是吴蜡给摆弄的。虽说,他也没专门学过,可那机器到了他手中,就没出过什么毛病,一直给侍弄的服服帖帖的。后来,知青中有一个叫柳贵的高中生跟吴蜡学会了开柴油机,这个柴油机就归他管了,可是他遇到什么难题,还是总要把师傅请来的。
上个月,柳贵被几个在大学读书的同学叫去到北京去了,眼看茶季就到了,茶场就又想到了吴蜡,请人把他找了来,让他先来顶一阵子,所以,吴蜡就来了。
吴蜡把柴油机房打开,整理了一下,又把那两台柴油机和那台发电机保养了一下,坐下休息,准备这两天就上班了。茶厂的会计老黄跟吴茗是至交,所以,吴蜡的事他总是特别关照。吴蜡也知道这个财神爷的劲道,总是把他捋得熨熨贴贴的。两人关系甚至胜过了当年吴茗在时。今天,他来了一下,到老黄办公室去了一下,算是点了个卯,办公室几个人都看见他了,从今天起,茶季的工资就可以算起了。
吴蜡独自一人,一年收入也算不少,没多大开销,只因他恋着瑞芳,经常给她一些体己钱,又经常在仕才身上用点钱,除此而外,就再无他用了。在跟瑞芳相好以前,他用钱的地方更少。吴蜡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花花轿子人抬人”,要在场面上跑,得有人抬着,所以,他也不攒什么钱,只要身上有闲钱,他跟朋友、同道从不计较,有人借了几个小钱,他也不要人还。为了图个热闹他经常会买了菜,到人家家里“混饭吃”。那时节,上馆子可是大事情,再说乡下地方,也无馆子可上,平时,吃点肉都是稀罕事,有他这样来“混”的,大家也都喜欢,平时大家“斗儿吃”,有几个人,爱凑热闹却又没钱,吴蜡就把他们的份儿给出了,大家见着他自然喜欢,远近几个村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气。三里湾的仁通伯送了他一个雅号叫“小孟尝”,意思说他像春秋时的孟尝君,吴蜡起先听说有人给他起外号心里还不痛快,后来,吴茗跟他讲了孟尝君的故事,知道孟尝君原来是个轻财重义的君子,他倒欣然接受了这个雅号,还常常以孟尝君自居了。
茶季开始后,柴油机房里日夜灯火通明,茶厂加夜班,发电机不能停,柴油机当然更不能停了,吴蜡就日夜扎在机房里,有时怕犯困,就叫几个朋友打扑克,打发时间。场里还另派了一个中学生跟吴蜡一起守机房,所以,吴蜡有空还是可以抽空回去“看看”瑞芳的。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转眼夏茶煞尾秋茶开摘了。
这天,吴蜡、朱牧天、裘善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