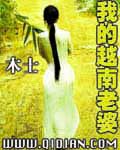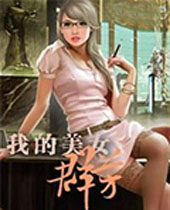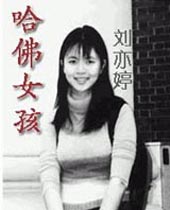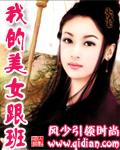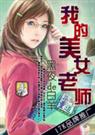漂亮女孩的美德-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车厂的生意,顾客主要是来修理汽车,而不是来买汽油。人们信赖马特科尼的修车技术,他们很清楚一个优秀的机械师和一个普通汽车修理工之间有什么区别。一个优秀的机械师懂得汽车的“脾气”,他只要听听引擎发动的声音就知道汽车的毛病出在哪儿,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只要看看病人的气色就知道病根在哪儿一样。
马特科尼先生曾经这样告诉他的两个学徒:“汽车引擎会对你说话。听听它们在说什么,它们在告诉你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们用心聆听。”
当然,这两个学徒根本没有理解马特科尼的话。他们对汽车的理解截然相反,很难想象出引擎也会有“情绪”和“感情”,引擎也会情绪沮丧、感到压力;或是情绪放松、舒缓。马特科尼先生雇佣这两个学徒纯粹是出于仁慈心,他很担心他们这一代机械师退下来之后是否后继有人。
马特科尼曾经对拉莫茨维小姐说:“只有有了机械师,非洲才能无所不往。机械师就如同是楼宇的基石,其他人都站在它之上,医生、护士、教师,所有人。总之,一切事物都建立在机械师之上,所以培养新一代机械师非常重要。”
汽车缓缓驶向车厂,拉莫茨维小姐和玛库兹看到一个学徒正站在一辆汽车的车轮边,另一个学徒正在慢慢地把车推进修车车间。看到她们两个人,推车的学徒停了下来,汽车缓缓倒退。
拉莫茨维小姐把她的白色小货车停在树下,玛库兹下车,走向办公室大门。
高个儿学徒说:“早上好。您车上的支撑零件不太好,您用得太使劲儿了。您看,它都偏到一边儿去了。我们可以给您修一修。”
拉莫茨维小姐反驳道:“我的车没什么毛病,马特科尼先生亲自打理这辆车,他从没说过这零件有什么问题。”
于是学徒答道:“可这两天他对任何事情都不发表意见,他一直少言寡语。”
玛库兹停下脚步,透过她的大眼镜凝视着这个学徒,自我介绍道:“我叫玛库兹,现在是这里的执行经理。如果你要谈什么关于修车的事儿,就到我的办公室里谈。你们现在在做什么?这辆车是谁的?你们准备拿它怎么办?”
高个儿学徒转头看了看他的同伴,于是后者坏笑着答道:“这是住在警察局后面的那个女人的汽车。她是个生活不检点的女人,经常用车接男人去她家,现在车子坏了,哈哈!这下子她没男人陪了。”
玛库兹闻言大怒:“车子发动不起来了,是么?”
“是的,”学徒答道,“车子一点儿也动不了了。我和查理得用拖车把它拖进修理厂。现在我们正要把车推进车厂,检查引擎。这车可不好修,可能得换新的启动器。这你是知道的。这下子这些男人们要出点血了,没有他们她付得起钱吗?哈哈!”
玛库兹把眼镜架到鼻梁上,目光直视说话的学徒,问道:“电池组工作吗?也许是它的问题,你试过吗?”
学徒的笑容马上僵住了。
拉莫茨维小姐强调说:“是啊,你们试过没有?”
学徒摇摇头说:“这是辆老汽车,可能是其他问题。”
“胡说!”玛库兹说,“把车前盖打开,厂里有新的电池组吗?把电池组线接上试试。”
学徒看了看他的同伴,后者耸了耸肩。
“来吧,”玛库兹接着说,“我还有不少事儿要处理呢,快点儿!”
于是,两个学徒马上开始干活儿,他们把车推进修车车间,把电池组导线接到新的电池组上。拉莫茨维小姐没吭声,只是默默地看着玛库兹指挥他们工作。一个学徒阴沉着脸爬到汽车驾驶座上,试着打火,引擎马上就发动起来。
“充好电,”玛库兹吩咐道,“给顾客换好油,然后把车还给她。同时要向她道歉,因为你们没有及时修好她的车,所以要免费给车换油以示补偿。”说完,她转过身对正在微笑的拉莫茨维小姐说:“诚信非常重要。我们给顾客方便,顾客就会一直光顾我们,而保证客源是做生意的关键。”
“是这样的。”拉莫茨维小姐赞同道。她曾经怀疑过玛库兹的管理能力,现在看来她是过虑了。
当两个人开始整理马特科尼凌乱的办公桌时,拉莫茨维小姐不经意地问她的秘书:“你对汽车很了解吧?”
“懂得不是很多,”玛库兹答道,“可我很熟悉打字机,机器的原理都差不多,你觉得呢?”
接下来,首要的任务是搞清楚有哪些车正在修理过程中,哪些车预定要修理。年纪稍长的查理被叫进办公室,玛库兹要求他列出一张需要马上处理的汽车清单。一共有八辆车需要马上修理,其中一辆漏油,一直缺少零件,停在车库后面。有些零件已经订购了,有些没有。
拿到清单后,玛库兹立刻逐一给每个零件供应商打电话索要零件。她加重语气地说:“马特科尼先生的脾气可不怎么好,如果你们让我们的生意做不下去,以前的订单我们是不会付钱的,这一点你要搞清楚。”玛库兹的话发挥了效用,大部分订单都保留下来,几个小时之后,需要的零件被各供应商亲自送达车厂。玛库兹命令两个学徒做好零件标签,按照需要的紧急程度排好顺序,放在工作台上。然后,两个学徒忙碌地装配零件,测试引擎,修好的车由玛库兹把关。玛库兹严格地询问他们修车的过程,甚至亲自检查工作的效果。因为她不会开车,所以在电话通知车主取车之前,要由拉莫茨维小姐试驾。玛库兹还决定只收一半费用,以补偿时间上的拖延。这一举措稳住了绝大部分顾客,仅有一人例外——他声称以后要去别处修车。
玛库兹用平和的语气对他说:“真可惜,这样的话,您就享受不到我们的免费服务了。”不出所料,这位怒气冲冲的顾客马上改变了主意。
一整天下来,特洛克翁大街快捷汽车维修公司交还了六辆汽车,所有的车主都对他们表示谅解。
夕阳西下,目送着两个筋疲力尽的学徒缓缓走下坡,玛库兹对拉莫茨维小姐说:“好兆头。他们今天干得很卖力,我每人奖励了50普拉,他们高兴透了。我相信他们会越干越好的。”
拉莫茨维小姐正全神贯注地凝思着什么,她闻言答道:“也许吧,你管理得很好。”
“谢谢,”玛库兹说,“现在我们得回家了,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呢。”
拉莫茨维小姐开车送她的秘书回家。正是下班回家的时间,路上熙熙攘攘、人流如梭;城市小巴上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超载的小巴发出刺耳的吱吱咯咯声;自行车行李架上也搭载着人。拉莫茨维小姐已经送过玛库兹回家很多次,对这条路线非常熟悉,对这个街区摇摇欲坠的矮房子和对任何事情都很好奇的穷人孩子也并不陌生。拉莫茨维小姐把玛库兹送到前门,目送她走向房子后面的简陋的小棚屋。忽然,拉莫茨维小姐似乎看到了一个人影,也许只是树影吧。看到玛库兹转身,拉莫茨维小姐赶紧开车离开了,她不想被玛库兹发现。
第四部分第七章 经历三次生命的女孩(1)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佣人,可是如果一个人有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房子又像拉莫茨维小姐的这么大,却吝啬到一个佣人都不雇用,那似乎就说不过去了。拉莫茨维小姐知道,在有的国家,即便是富有的人都没有佣人。她认为此举简直难以理解,既然养得起佣人,那为什么不给别人一个养家糊口的机会呢?
在博茨瓦纳,塞普拉·特弗大街的每所房子——确切地说,是每所有超过两间卧室的房子——都有应当佣人。虽然法律规定了佣人的薪金,可人们一般都视若无睹。有的人对待佣人的态度非常恶劣,他们总是竭力压低佣人的工资,同时又希望佣人一天到晚马不停蹄地工作;而且据拉莫茨维小姐所知,这种人占多数。这就是博茨瓦纳的阴暗面——事实上的剥削——尽管没有人愿意提及这个字眼。当然更没有人愿意谈论过去莫萨尔瓦人是如何被当成奴隶来奴役的,即使有人偶然提及,在场的人都会闪烁其辞,立即改变话题。但历史不容置疑,更何况如今这种情况依然存在,这一点大家都心照不宣。这种事在整个非洲大陆都普遍存在;奴隶制度是非洲大陆挥之不去的阴影,非洲的奴隶贩子一直十分猖獗,他们贩卖自己的同胞,非洲的“奴隶大军”只赚取一丁点儿可怜的薪水,受到“准奴隶主”的残酷剥削。非洲的奴隶平静地接受压迫、毫不反抗、弱小无助,在有钱人家当佣人的也不例外。
有的人对佣人冷酷无情,拉莫维茨小姐对此震惊不已。她曾经到访一个朋友,闲谈中主人不经意地提起,说她的佣人每年只有五天假期,而且假期时没有工钱。她还吹嘘说,仅仅因为她觉得佣人懒散,就成功地克扣了佣人的工钱。
当时,拉莫茨维小姐问她的朋友:“那她为什么不辞职呢?”她的朋友笑道:“去哪儿?想接替她的人多得是,她心里明白着呢,我花一半的钱就能再雇一个像她一样的佣人。”
拉莫茨维小姐什么也没说,但暗自决心终止这份友谊。这位朋友的言行让她思绪万千:行为失当的人也会有朋友吗?还是说“物以类聚”,坏人只会有坏朋友,因为只有其他坏人才可能跟坏人有足够的共同语言?拉莫茨维小姐联想到一些臭名昭著的人物,比方说伊蒂·阿明和亨里克·维尔沃尔德;当然,伊蒂·阿明是因为身体不好,也许还不像那个心冷得像冰一样的维尔沃尔德那么坏。有人爱过维尔沃尔德吗?是否有人曾经握过他的手?也许有过,很多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他们也像在好人的葬礼上一样痛哭失声吗?维尔沃尔德当然也有他的朋友,也许不会全是坏人。如今南非事过境迁,但这些人还得生存下去。也许他们已经明白错在哪里,即使他们自己已经忘却了,人们也已经原谅了他们,非洲人民一贯胸怀宽广,他们懂得如何忘记仇恨。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有时非洲人也有些傻,但他们绝不允许仇恨生根,曼德拉先生就是力证。塞雷斯特·科哈马先生也是这样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尽管出了博茨瓦纳人之外,他鲜为人知;但科哈马先生是非洲最伟大的英雄之一,拉莫茨维小姐的父亲曾经握过他的手。拉莫茨维小姐清晰地记得,那时科哈马先生访问莫丘迪,与当地群众亲切交谈;还是个小女孩的她充满敬意地看着他走出汽车,人们立刻围住他,而其中手持着一顶旧的扁平帽子的人就是她的父亲;当科哈马先生握住父亲的手时,小女孩满心自豪。每当拉莫茨维小姐看到壁炉上方悬挂的科哈马先生的照片时,当时的一幕幕就如同电影般重现眼前。
拉莫茨维小姐那位恶劣对待佣人的朋友并不是坏人,她一向对家人和善亲切,对拉莫茨维小姐也彬彬有礼,但就是丝毫不顾及佣人的感情。拉莫茨维小姐曾经见过她的佣人,这个来自莫莱波罗莱的女人脾气和顺,而且工作勤奋。在拉莫茨维小姐看来,朋友的这种言行源自对人性的漠视和对别人感情的不理解;而理解他人恰恰是一切美德的源头。如果你了解别人的感受,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就一定不会制造痛苦,因为加在别人身上的痛苦会还施彼身。
拉莫茨维小姐知道,有关道德是什么,人们争论不休。她个人认为答案很简单:首先是博茨瓦纳的传统道德,照着它做准没错;当然还有其他道德,比方说基督教十诫,几十年来聆听莫丘迪主日学校的教导,拉莫茨维小姐对此倒背如流,这也是绝对正确的。这两种道德标准像博茨瓦纳的刑法一样不容置疑,必须严格遵守,任何人都不能自封博茨瓦纳的最高法官,擅自决定遵守或不遵守哪些道德准则。道德准则不允许人们质疑,也不容许任何人自由更改。一个人绝不能自己决定对某项禁令认可与否,“我不会偷窃,当然不会;但通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其他人不可以,但我可以”,这种逻辑十分可笑。
拉莫茨维小姐认为,大多数道德准则是长期以来被人们普遍认同为正确的言行举止,并为人们普遍接受和遵守。任何人都没有能力自创一套道德准则,因为一个人的生活经历远远达不到制定道德准则的标准。哪个人有权利说自己比老一辈人懂得更多?既然道德准则制约着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那么大多数人意见一致才能确定一项道德准则。由此而形成的现代道德准则宣扬个人主义,注重个人利益,这样的道德准则经不起时间的磨练和考验。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制定道德准则,那他们就会制定出自己最容易遵守的,并允许自己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为所欲为、不受约束的道德准则。在拉莫茨维小姐看来,不管说得多么冠冕堂皇,这纯粹是自私行为。
拉莫茨维小姐曾收听过一次“服务全球”广播电台的节目,节目内容令她瞠目结舌。在节目中,一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哲学家大肆吹嘘自己的主张,她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法国人。他们宣扬,每个人都应该采取让自己感受真实的生活方式,真实生活中要做的事情就是正确的事情。拉莫茨维小姐不禁哑然,不用说在法国,就是在博茨瓦纳也有很多所谓的存在主义者,比如说她的前夫诺特·莫科蒂。她甚至是在对此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糊里糊涂地嫁给了一个存在主义者。诺特是个极其自私的男人,他从不为他人着想,甚至对自己的妻子也是如此;他追捧存在主义者的观点,反之亦然。难道说自己晚上出去泡吧,却把怀孕的妻子孤零零地扔在家里,这种做法不是存在主义吗?他们甚至还和酒吧里认识的所谓观点相同的女人出双入对,全然不顾别人的看法和感受。存在主义者自己过得潇洒自在,可他周围的那些非存在主义者就得跟着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