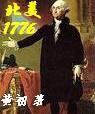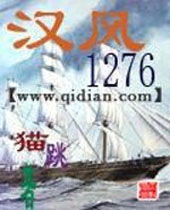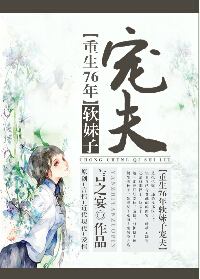5276-��ʱ��������й�-��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ۼ͡������Ӻ���Ů������ʮ����ҹ��������������ʮ���ա�ʮ���ա�ʮ����ҹ���조��͵���������ذ��ʱ���ġ���͵���ǻ������͵��֮�⡣������Щ��ʵ����һ����Ϊ����͵Ϸ�Ĵ�ͳ��κ�����������壬�������֡��ڱ���������ʮ�����ѳ�Ϊ���һʢ����ա���ʱȫ�������ҹ�件�����ں���ʷ����û�м��أ����ϳ�ʷ����Ҳû�м��أ��϶�Ԫ������Դ�ڱ�������һ�ɡ�����ϰ�ס�����Ŀ���׳�����1994��棬��217��223ҳ���������ذ��ʱ��������ʮ������͵���Ա�������ʮ����ע�뻶����������ʵ����������˵Ԫ������Դ�ڱ���������Ԫ�����һ����Բ֮ҹ��������صģ���������ʮ���յķ�����Ҫ�����֣���δ�й��������͵ƵĻ�����ϳ�����ʮ�����ŵƵĻ��δ�ռ���䣬��ȴԨԴ���ԡ���˾���Ԫ���γɽǶȿ���κ���ϱ���������һ����Ҫʱ�ڣ�������˵�˽���Դ�ڱ������ϳ���ֻ��˵�ϱ�������һЩ�Ϊ��Ԫ�ڵ��γ�ע��������ϱ�����һ��ʷ������Ԫ���γ��ڡ�������ʵ�ϣ���Ԫ���γ��л�����һ��Ҫ���أ�����̵�Ӱ�졣��쾵ۡ���Ԫҹ��ͨ�齨��ҹ����¥��ʫ��˵������������ת������������������ǧ���գ�������֦������ʹ���ǿ������������Dz����ڡ����֡������������ķ�̻�еġ�������ˣ����ĵۿ������������ʮ���ս������쾵�ʱ���ƻ��ˡ���ҵ���꣨610�꣩���£���������ެ�����ϼ������������ڶ��Ž�ʢ�°�Ϸ��Ϸ����Χ��ǧ����ִ˿�������ǧ�ˣ�������ʮ��Ի��������ƻ������أ����¶��գ����Ѱ�����������Ϊ����������ʡע������������ʮ���ա�����Ԫ�����֣���ʼʢ�ڴˡ���쾵�ʱ��������ʮ���ս��°�Ϸ�͡��ƻ𡱽����һ�����ע���ƣ�Ԫ�����֣�ʼʢ�ڴˣ��������γ���Ԫ���ڡ�ǰ��쾵�ʫ����Ŀ�г��֡���Ԫ��һ�ʣ����յ��̵�˵������Ԫ����ٴ�֮ʱ��Ҫ���ڽ̻������ʮ�����ŵƳ�Ϊ��Ԫ�����ڴ�ʱ����Ȼ��Ԫ���ڲ�����һ�����γ���쾵�ʱ�ڣ��������н��յ���������������ǰ�ķ�������֪��ͬκ���ϱ���ʱ������ʮ���շ��ķ�չ��ֱ�ӹ�ϵ��ͬ��������Զ��������й�����κ���ϱ���ʱ����չ����쾵�ȼ���ܵ���̵�Ӱ�죬ҲӦ����һ����ʷ�����Ļ���������˵����Ԫȼ�������ǰ�Ѿ��ܵ����Ӱ���ˡ�
����ʱ��������й�������һ�����ϡ���Ԫ��2����ͼ��
��������ȼ�����̵Ĺ�ϵ�������Ѿ�ָ�����������ԭ�����ˡ��ŵơ�����������������ɮʷ�ԡ�����������������Ի������ʮ������ʮ�գ��Ǵ˷���������ν֮����䣬���������յƣ�������Ҳ����һ��������宇��ͨҹ���ǣ�ȡ������˾�@�������ռ��룬������Ϊ���¡���������˵������֮�µò���֤����������д�����ռ��������൱�ں�������ʮ���գ�Ϊ����Ԫ���������ںϷ���ṩ�˻������������˵��̶�����Ԫȼ�Ƶ�Ӱ���������ǰ����ȱ�����ϻ����������Ļ�����ô�ƴ����Ͽ��Խϳ�ֵ�˵���˵㡣��������•����ڱ��͡�������꣨713�꣩��˵����������ɮ���u��ҹ����ȼ�ư�ǧ�棬������ҹ���ʵ�����ϲ�Ź۵����֣�������ҹ����ʰ����֮ͦ������֮����ֹ�����ɼ����������ʮ����ȼ�Ƶ��ᳫ�ߡ��ִ��ƴ��ػ���Ժ������ͬȼ�ƽ��йصļ��غܶ࣬����֧�����͵���;��ʾ���ƽڵ���Ҫ���������¿�ȼ�ƣ���ר��ȼ��ɮ��������ɮ�ٶ��Ͽ����ؽڡ����ػ������л������ƪ��ȼ���ġ����ǹ�������ף���ж��ġ��ػ͵ĵƽڳﱸ�������ô�ͳ�����������ʽ�����ȼ���磬�����ھ�����֧Ԯ�ƽڡ����Ź����ػʹ��½���̽�ۡ������й�ʷ�о���1989���3�ڣ����ɼ�ȼ���Ƿ����Ҫ�����ԭ������أ�����������˵����ʱ���а˺��ɳ������Ů�ȣ������߱���Ϊ�����������ֱ���Ϊ������������Բ��ʱ��Ů�����������������ȼ�Ƶģ�����������������Ϊ����ʮ���˵����ϣ��������й��������ȡ�����Ǻ����˵ģ���̲�����á������ݣ���ʮ����ҹ���������У���լȼ�ơ��������·��ǰ����¥�����¡�ͥ�м����Ȳ�ȼ�ƣ���յ�����ؼơ���������������ơ���ƣ��ƴ�ǧ�ơ���ס���֮����������֮ò����Ҳ������֮�������Ǿ����Բ�ʡ�������Ѳ���мǡ���һ�����������ͷ�������ʮ����ȼ�Ƽ����ձ��ԣ����Ҵӵ��Ƶĸ�ˮƽ�������ƽ��γ���Ϊʱ���̡���Ԫ�ƽ����ƴ���ʽ�γ��ˣ���̽������й��Ŵ�����ʮ���յĴ�ͳ������������������̣����������Ժܴ��Ӱ�졣Ҳ����˵����̴ٽ�������ʮ�����ŵ�֮���ձ黯����ʽ�γɡ������ƽ�֮�������Ƴ�������ʮ������Ϊ��ȼ�ơ����ա��챦���꣨744�꣩�涨����ÿ����������ʮ�ġ�ʮ�塢ʮ���տ�����ȼ�ƣ���Ϊ��ʽ���������ƻ�Ҫ�����ľš�ȼ�ơ����춨�˺����ƽڵĻ�����������ĩ��������Ԫȼ�Ʒϣ������ʱ�ָ����������ƣ��������ʷ•����̫�汾�͡�������������ʷ•����һ����˵�����Ժ���������ҹ��������ȼ�ƣ�����֮�������δ��ĵ��ڣ����ԡ�������ı¼������˵����̫��Ǭ�����꣨967�꣩���¼׳�گԻ������Ԫ�ŵƾ�ֹ��ҹ����͢���£�����V�����������֮��ǣ�����ʿ��֮���֡�����⸮����ʮ�ߡ�ʮ����ҹ�ơ�������Ϊ�������δ�ȫ���о��Ʒŵ����գ������ǿ����������ա����⡶�������¡����أ���Ԫ���������ο�����䣬����Ǯ��������ҹ��չ���ʮ�߰���ҹ��ν֮��ҹ������������ʱ�ڣ��ۺϡ�����¼���������־��¡��ļ��أ���֪����Ϊ���죬����ʮ����ֹ��ʮ���գ������ں����ڵ���ʺ�ֱ���������ʮ����ʮ�����˶���Ϊ���գ����ҽ�ֹ���֣����˽�¿���Ϊ���ա��ٰ�����ĵط����ƽ�һ�������졣�����δ��ƽ�ʮ�����֣��Ƶ�Ʒ�ַ��࣬���ݷ��ɴ���Ԫ�����н���ٽг����ʮ���ϡ���֪����ʱ������ʢ�������ŵ���ʽ�ж��ŵƣ��Ƶ�ʽ���������ơ��ŵơ�Ȯ�ơ�¹�ơ����۵ơ�������ơ����ӵơ����ѵơ��ơ��µơ�С��ơ������ơ�����ơ����ơ����ơ����ŵ��⣬�����𡢻�����Ҳ�ǽ���������Ŀ�������δ�����������Ԫ���͵��յĻ�������־���•����Ʒ�����������Ծ�Ƽ�дʫ�ʣ�ʱԢ��Ц�����������ͷ������ɾ�ڻ�ϷŪ���ˡ�����ν���T�����ͷ�ǽ��յ�����ÿ��Ŀ�ͷ��������ͷ���������һ�֡�������������Ԫ�ڣ�����ʱ��1403��1424�꣩���涨Ϊ���졣�����ִ������к��ڵط�־�������ؽ��ڲ�ͬ������һ����ʮ������ʮ�������졣������ʮ�����Եƣ�ʮ�������ƣ�ʮ���ղеơ����ξ���̫����־�������Ϸ�ʱ��ϳ������������㡢��Ϊ����㽭���ݸ��������죻���˸���ʮ����ʮ���գ����죻���˸���ʮ������ʮ�գ��ư��죻����������ʮ����ʮ���գ����죻���ݸ���ʮ������ʮ�գ����죻��ƽ����Ϫ���dz�ʮ����ʮ�գ�ʮһ�죻����̫�ִӳ��˾�����ʮ��ֹ����ʮ�����졣���������ƽ��У��ŵơ��۵ơ��µ��ո����ձ顣���صĵ����ռ���ÿ����ڣ��������ŵ��⣬����ַ��������������Ҳ�����ij���������֯ר�ŵ��͵�֮���������㽭�������־��˵��������Ȼ����������ƣ�Ϥ�����ƣ������������ߣ���ʴ�֮�������߸�����������Ҫ��Ϊ��¥���µ��Ϸ����ɽ��������棬��ĸ�ک��������Ϣ����Ϊ���Ǽ�������Ԫ�ƽڵ��ŵ��龰������͵ƾ߶��ԣ��ξ����ϡ����¸�־��˵������Ԫ��ֽΪ�ƣ��������������ʣ��������������������࣬���������˿���������ľ��ɡ����������µĵ��侫�ɣ���������ĵƸ�Ϊ���������ջ���ռ��ԣ�Ҳ�ɼ��ڡ����¸�־�����������������գ�ҹ������Բ£���Ի��ĵơ����������̻���������Ԫ�ڵ���һ��Ҫ���ۣ������˽��յ��������ա����¡���̨־�������˺��ϵ��̻𣺡������ջ����������ɲع��¡����ݣ����������������и�����ʮ������Ǿ۹ۣ���Ի���̻𡣡��̻������ḻ�����ո��ʵ��̻��������������������ݸ�־��˵���������ݻ����������ɣ���Ϊ�ӷѣ�������Ϊ�ţ���ΪͲ��Զ������Ϊ�档����������ƽ�ʱ�䱱������������������Ϊ�����Ϸ�ʱ��ϳ������������Զ̣�һ��Ϊ�����졣ͨ����ʮ�������ŵƣ�ʮ�������ƣ�ʮ��������ơ��ƽ��������������û��̫��IJ�𡣡���ֵ��һ����ǡ��߰ٲ������ס�����Ԫ���Ѿ����֣������С��߰ٲ���ʫ�������ǵ�������ʢ�����С�ҹ���������¸���С�ã���Լ��ױ�߰ٲ�������ת�Թ�����������־��������ʱ��������ʮ���հ���ʢ�С��߰ٲ�������߰ٲ��ֽ�ɢ�ٲ����ΰٲ���Dz�ٲ������ٲ��ȣ�һ���ǵǸ����ţ��������㣬˵�ǿ���ȥ���������μ�����һЩ�������и���飬Ҳ���൱��ĵ�����Ů�������������С��������˻���Ϊ��������ʮ���գ���ν֮��ĥ�գ���˽�����ֿ⡣����˵ʫ�ơ����½���������ĥ�������������£�ͬ�������ˡ�������Ԫ���ף�����ʮ����ν֮��͵��������Ϊ�����ϣ�����͵ʱҲ�������������ʮ��ҹ֮�߽֣���������Ҳ���������������������������������Դ֮һ˵�������������Ϲò���������ʮ���ջ����й��Ŵ��������ա���������ʱ�ǡ����أ�������ʮ���գ������ӣ��������ϣ������Ż����������濴���ƺ����Ǽ����Ż�֮�ס���������ע����ʱ���������г�ǡ�˵�����������ų�ҹ�𣬺���һ��������լ���Ͻǣ�ν��Ի�����˵��Ǿ��Ҳ��ң��Ҽ��˵�֮���������°룬�������࣬���������Լ��ң��������ɣ�ٱ������Ծ���ʧ֮�������������ࡣ�Դ˺��òϡ�����ϸ�����ģ���֪��������Ϊ�˼��������˲ϣ������ø�������֮�¡��������������࣬Ҳ�DZ�ʾ��ϡ������д�����˵�����ɣ�����Ż��ı��塣
����ʱ��������й�������һ�����ϡ���Ԫ��3����ͼ��
������������ʱ�ǡ������أ�����������ף����ռ��ţ�������֦���ţ�����֦��ָ�����ԾƸ���ʳ������������֮����������ѧ�ǡ�����������˵�����������°����ൻ֮�����⸲���ϣ�����ʳ֮����Ի�����Ǹ��ӣ�Ю���ԣ��������������������ϡ�������Ϊ�������ӡ���������ʷ�Ͼ����Ա���ϵͳ�Ź�հ��ע�������д��ǵĿ�������һ���ǻ����ķ��ף����������������ʹ�ϼ���ҵ�����ף����ᡣ�����ӿ������ܵ��Ϸ�Ӱ�죬��������������Ϸ����졣ǰһ�������Ż�ӭ�����Ļ������������ӭ�������ڶ���ĩ�ġ����ϡ�������������о��м��ء�����������������������ס��Ź�հע�ܿ��ܼ̳������ϵͳ������֦��ָ���룬��ζ���ڸ������ķ�����롣��������ʮ�������Ϸ����У����в��ϹõĻ����������ʱ�ǡ�˵����ӭ�Ϲã��Բ�������ɣ����ռ���¡����Ϲò��Ĺ��³����ϳ�����ʱ������Ȩ�ġ���Է�����ഫ�Ϲ�������檣�Ϊ���������ޣ��������������£��Ϲ�������ʮ�������߶�����������������һ�������Ϲõ������ڲ�����������ӭ������ף��˵�������ɷ��ڼң��ܷ����ѻ�����ˣ��Ϲ���ɳ��������Ϲ���������ռ���£���δ����ɣ���������˵������ʱ������ӭ�Ϲ�ռ��ɣ���µķ��ף��Ϲ�����Ϊ�������õġ��д�����Ϊ����ͬ�й��������Ը����һ�������������������й�ϵ�����������ķ�������ũɣ����Ҫ���á��������ű��߷dz�֮���������ǿʢ���纺���ݷ������ڲޣ�����Ҳ��֮Ϊ�ݹ�������������������ʮ�����ϵ������Ϊ����ʮ������Ϊһ������������£������������壬��ռ��֮�ס��������ԣ�����Ϊ�϶𣬶���ɣҲ��Ů�ԵĹ������硶����г�ǡ���˵������֮��Ҳ��Ů����Ϊ������Ϲ���Ů���ڳ���֮�գ�����Ч�õġ������Ϲ�������ʫ��������ӳ������ǡ�����ʮ��ҹ�������Ϲ������²Բԡ�������������Ԫҹ�ž��еƺ��ùۡ��������в�������ʢ�������������Ϲá����ƴ���Ԫ�ڵ��Ϲ��������ɼ�һ�ߡ������δ�����˵�����Ϲ��������ͬ������ϡ�������������Ϫ��̸������һ˵����������������ҹӭ����ν֮�Ϲá�������£���ʱ�Կ��١�����ʱ��С������������֮��Ϊ��Ц��������ӭ�Ϲ������࣬���ʶ������¸�ʫ���м����ߣ����ż�֮�����Ϲó�ΪС����Ц����������дʫ֮�ߣ�ɥʧ����ʥ�ԣ����һ����Ϸ�����Է����˺ܴ�仯�����Ρ��ļ���־���ɾ�����������Ϲá����彲����ӭ�Ϲõķ��������Ի���ʣ�ʹ���˷�֮����������ɳ�С����δ��Ϲó�Ϊ��������֮�����η��ɴ���Ԫ�����н���ٽг����ʮ���ϡ��С���ʫ��ʾ����䣬��ע���������Ϲã���ν֮���ɣ���������á�����˵������ν���°ٲ��飬���㡢έ���롢��֮���Բ��ɣ�����ӱ�Ϊ֮�������ڻ������Ϲã���Ϊ��ͬ��ɨ��á���á�έ��һ��IJ������л����㡢���Ǹ�Ů�ճ�����֮������������ϵ���У�����ռ���ƺ�������Ч����������έ�����һֱ���������彭��һ������������ʱ������Ԫ�Ϲò��������ձ飬�Ϲò���Ҫ���ڼ��ס���������Ǹ���Ϲ����ɣ�Ĺ�ϵ����ɣ�ϲ����Կɿ������纼�ݵ�����Ԫ�ڣ��������������֮����������ɡ���������־�ࡷ��һ�壩���Ϲò��ķ���������ĩ���۾������ԡ��������أ�������ǰ��ҹ����Ů�����ˣ�ֽ���棬������ȹ���ųƹ����ͯŮҴ֮���������࣬��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