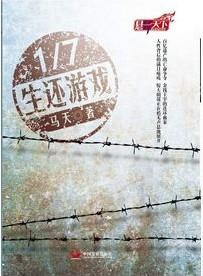341-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77年12月15日,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副校长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到任没几天,他就问中央组织部过去过问过“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
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冤案的平反了。
一些熟知耀邦的人更知道:耀邦革命一生从未整过人,并对所有被冤整过的人满怀同情。
1932年,他十六岁,在中央苏区湘赣省委负责儿童工作时,被称为“AB团分子”,如不是少共中央局书记冯文彬及时而巧妙地解救,他险乎英才早丧。1942年在延安,他已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他的夫人李昭也一度被康生捺下“抢救运动”的漩涡,耀邦自己也受到了株连。在事隔多年的1960年,耀邦向他身边的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回忆“AB团”往事时说:我那时还小,受到那么大的打击实在受不了,我哭了。那时我比较胖,人们都叫我“小胖子”,但从那之后我就成了“小瘦子”,直到现在也没再胖起来!
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所谓的共产党内也有“AB团”和延安“特务如毛”、必须在投奔延安的抗日青年中大搞“抢救运动”等等,都是杀人连眼睫毛也不眨一眨的康生之流臆断出来的。
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和这一出出自相残害的历史悲剧,促使耀邦早就暗立誓言:永生永世决不冤屈任何人,也不容任何人这样干!
1956年7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肃反运动”总结大会。作总结报告的,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西元。当刘西元讲到“肃清反革命”的曲折过程时,坐在台上报告人后面的胡耀邦突然立起身,大步走到台前,挤到话筒前说:“这次‘肃反’,伤害了一些好同志……”,边说边接过一旁秘书递过来的一张名单,大声念了起来,第一位就是《中国青年报》编辑朱志炎(这位复旦大学毕业生,八十年代初是主持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文本的编译出版者)。念完了名单,耀邦接着说:“这是书记处的责任,首先是我的责任,是我的失误,因为我是第一书记……我要向这些好同志道歉!同志们,对不起了!”说罢,他又走到台前正中央,向台下深深一鞠躬,并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1957年整风鸣放,《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在首都新闻界座谈会上,就如何办好一份为青年所喜闻乐见的报纸为主题,作了一个包涵五个问题的发言。他说青年报应突出青年的特色,不能什么文件讲话都照抄照登,而应当精细加工,使其生动活泼,形象具体,不要将报纸弄成个“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把他的这些话见了报,全文被载入人民大学新闻系讲义。
当时人们都不把这当一回事。耀邦按原定计划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去伊朗等国访问。在接着到来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时,团中央的“反右”斗争由书记处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罗毅全权领导。他东一头西一棒地在团中央打出了七十三名“右派”,张黎群的那句话也被抓住不放,并被密报到党中央。
1957年秋天,耀邦从国外一回到乌鲁木齐,就给北京的罗毅打电话,询问团中央的“反右”斗争情况。当他得知光是《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就被打出十七名“右派”,约占编辑部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七,而且大部分都是副总编辑、部主任和业务骨干时,十分震惊而沉痛地说:“损失惨重啊!”他立即赶回北京,想出种种办法挽救和保护一些同志。
他先去了中南海,向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张黎群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讲的那些词句,是糊涂俏皮话。他是说报纸登的通知、讲话什么的太多了,好像是贴布告,说了句俏皮话。他很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对党还是很有感情的……”
此前,当有些报纸猛批张黎群的那些用词时,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就把张黎群的整个发言稿调去看过了,还在小平面前为张黎群说了不少好话,并拍了胸脯打保票说:“此君绝不会反党!”现在又听到耀邦也是这么说,小平说:“那就算了吧!不过他既然糊涂,就不能再当报纸总编辑了!”于是张黎群的问题就成了人民内部矛盾,被定为“犯了具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严重的政治错误”,给予四个方面的处分:写一篇检讨文章,由新华社发通稿,供各报刊登,以消除错误影响;撤销共青团中央常委;党内严重警告;下放陕北米脂县担任县委书记处书记。
但是不管怎样,耀邦总算从“敌我”分界线上救回一位好同志。而且他还针对上述四条处分,来了个四条保护措施——在1958年8月举行的团中央三届三中全会时,当面对张黎群说:“你的‘政治事件’就到此为止了;处分决定不登报;保留党的‘八大’代表资格;不当常委可仍是团中央委员;不是一般的‘下放’干部,而是真正有职有权的县委书记处书记。到了那里要认真研究如何改变老根据地的贫穷面貌。这是新担子、重担子啊,务必得挑好!”
张黎群临离北京时特向耀邦告别。耀邦又叮嘱他说:“党员犯错误是难免的。你看在延安办轻骑队的许立群,那时有人说他犯了大错误,而今还不是被起用了、重用了?你可千万不要没精打采、一副倒霉相!而应该昂首挺胸,回到老区米脂县立新功!”
然而耀邦痛感遗憾的是,他虽然也作了种种努力,结果未能把《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钟沛璋、陈模等同志和团中央其他被扣上“右”帽的同志,从“敌我”线上救回来。但是他对这些同志从不歧视冷落。有人登门求见,只要有空,他都亲切接待。
当这七十多位同志整好行装,即将去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的故乡——山西平顺县接受考验的时候,他又把他们请到团中央二楼会议室,对他们作了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他说:“我要给你们讲两点:第一,你们所犯错误的性质十分严重;第二,你们的前途十分光明。”但是对于第一点,他没有再说第二句,而对第二点,却似清泉滔滔地讲了许多。他说在党号召整风时说了几句过头话,并不能表明就是反党。《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的干部,绝大部分来自大学,而且是参加过地下工作、学生运动的优秀分子,或是地方团委及地方青年报的比较优秀的干部。他们都对党深有感情、工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思想也都比较活跃。
最后,耀邦对这些同志说:“你们都还年轻,有文化、有能力,过去都为党为青年团做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我深信,你们下到农村后,必定会和人民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为改天换地建立新的业绩,在将来的某一天,你们还有可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耀邦的这番真挚动情的讲话,对这些被推到“敌我”线上的人们是个强有力的激励,不少人听得直掉泪:“耀邦还是把我们当做自己人的呀!……”
这些同志去了平顺后,都没有辜负耀邦的殷切期待。只两三年工夫,全都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一些山沟沟里的村干部和老乡,还把许多人评为模范干部,他们都婉言谢绝,说他们是下来锻炼的,不参加当地干部、社员的评比。他们回到了团中央,都被妥善地安排了工作。像陈模、钟沛璋回到了《中国青年报》,虽然没有恢复副总编,但都当上了青年活动部和知识部的副主任,不仅让他们编稿、发稿,还可以照样撰写评论和社论。
“反右派”斗争结束,耀邦把各单位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一个一个地请到自己家里或办公室谈心:“你们哪是什么‘右派’,多半是骄傲自满、说话欠考虑而已”;“‘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切不可灰心丧志,自暴自弃。”
他深切关怀的当然不仅仅只是“右派”。
1956年,在团中央书记处一次扩大会议上,书记处书记项南、梁步庭等同志,强调共青团要充分发扬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并提出了一个包括民主化、群众化、自治化的“十点建议”。对这个建议,大家都表示赞成,并下发各省市党委和团委,请他们参照执行。
1958年夏,党中央某些同志以检查党的领导为由,先把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打成“反党分子”,开除了他的党籍,接着又要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他们实在抓不住胡耀邦的辫子,就把他曾同意的项南、梁步庭的“十点建议”作为“毒草”来大批特批,连续召开了七十三天的批判会,终于给“十点建议”定了性,说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攻击党的领导”,“篡改青年运动的共产主义方向”。会议定项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农村劳动;梁步庭也受了处分。
其后多少年,耀邦一直为没能保护好这些敢于直言的好同志而深感内疚。他决心要为所有被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
到中组部的前一个月,在他指导下撰写的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他特别建议执笔者加了这样一段话:
“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
这就为“右派”冤案的平反公开委婉地埋下了伏笔。
一次大解救“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将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的遗留问题。
按当时已经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共约四十五万余人;从1959年建国十周年开始到1964年,先后摘去五批“右派”帽子共三十多万人,尚有十多万人必须全部摘掉帽子,并连同过去已经摘去帽子的都应给予妥善安置。
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完全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烈争论。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出席会议。
不出耀邦所料,烟台会议上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五人小组的指导思想,就打上了“两个凡是”的烙印。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的改正。
中组部的杨士杰、陈文炜等人则表示不以为然。
在闭幕总结会议上,杨士杰又特别就“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讲了话。他说:“反右”运动已过去二十年了。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只有“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
为使这一讲话更有力,杨士杰特地引用了胡耀邦刚进中组部时说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杨士杰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杨士杰还特别强调地说,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成、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被强抑已久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
可在当时,与会的许多人还没有觉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他们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因而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连采访会议的记者也分成了两大派:《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完全同意杨士杰和中组部其他同志的意见,而另一个特大新闻单位的记者则认为杨士杰等人是“两面派”。于是,会议仍以牵头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党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不久,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列为1978年的“十一号”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
不过在烟台会议结束时,杨士杰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等人曾表示对这个报告持有“保留意见”。
《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回到了北京,立刻向报社国内政治宣传部主任王泽民、副主任付真汇报了会议上的争论。王泽民、付真与报社领导胡绩伟、安岗等人火速商量后,给杨士杰打了电话,表示对仍然被“左”的色彩迷花了眼的人们的主张,不能仅仅“保留意见”,而最好正式写出书面材料送出去,继续据理力争。
接着,在中组部老干部党支部成员袁任远家里,陈文炜与王泽民碰了面。他们知道许多老同志都认为烟台会议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必须向中央反映会议真实情况,并当即谈妥,由陈文炜以会议参加者身份写一个书面反映。陈文炜回到中组部写好后,送请杨士杰过目,杨士杰签了名,立即派人送到了烟台会议主要牵头者的统战部。统战部有关人员看了这份材料,一再询问中组部送材料的同志:这是杨士杰的个人观点,还是中组部的意见?
送信人回来向陈文炜转述了统战部人员的询问,陈文炜说:“杨士杰是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他不代表中组部还能代表谁?”但为慎重起见,陈文炜与杨士杰专门向耀邦作了汇报。耀邦看了陈文炜书面反映的副本当即表示:“我完全赞成!”事后,耀邦又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并把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找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