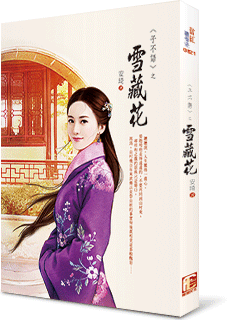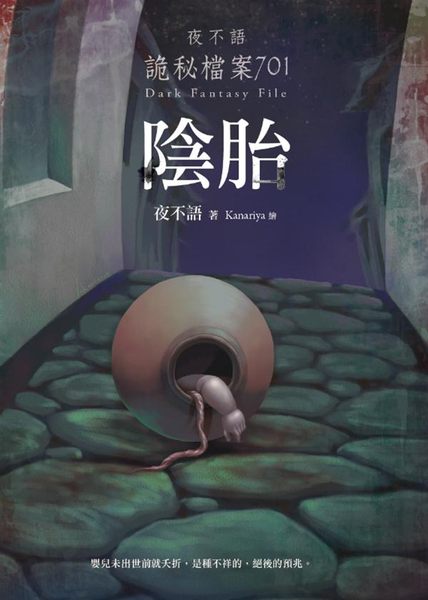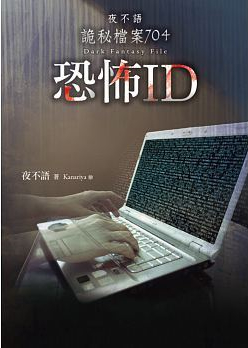天公不语对枯棋-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限制和防范;光绪天性懦弱,本来就没有采用政变方式来处置太后的打算;康有为虽然已到不惑之年,但在宫廷政变的想象力上,只有“扶皇帝登午门”,或皇帝在阅兵时“驰入”袁世凯营中、下诏命袁诛贼臣之类程式,与精明干练、深谙政治运作方式的太后相比,他仿佛是一个旧小说旧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
20日这天在平静中度过。早晨,皇帝在宫中第三次召见袁世凯时,康有为离开了生活数年的南海会馆,悄然“奉旨出京”。中午,袁世凯乘火车回天津。与此同时,皇帝接见了伊藤博文。在这两场活动进行之际,太后的影子始终就在皇帝的身边。由此可知,所谓袁世凯当晚向直隶总督荣禄出卖维新党人,荣禄又连夜赶赴颐和园报告之类说法,都是蛇足,可不必再论。21日太后重新训政,下令捉拿“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康有为、康广仁兄弟。24日,宣布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治罪。26日,上谕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此案,限三日具奏。同日荣禄进京。27日,慈禧太后召见荣禄。据当时担任兵部司官的陈夔龙回忆,28日清晨,御前大臣庆亲王奕特在家中密嘱他和工部司官铁良代表其参与审讯,同办案官员商量设法解脱杨锐、刘光第。这说明连庆王都未闻政变之说,而且已接到一些方面的营救请求,开始做疏通工作。假若此时听说谋害太后的“大逆案”,他是决不会插手营救的。
《天公不语对枯棋》 落尽夭桃又侬李阅世空有后死身(5)
约9时,陈、铁出庆王府。旋闻早晨某京堂封奏,请勿庸审讯,即由军机大臣刚毅传谕刑部,将谭嗣同等六人一体绑赴菜市口正法。被杀者,史称“戊戌六君子”。人们相信,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是告了密的。即便政变不因告密而起,但21日他在天津,还是把有关情况泄露给了荣禄。问题在于,他回到天津时,尚不知道太后会在次日重新训政。根据常识,训政之后的告密,在太后看来,虽然也属揭发,但更是大势所趋下的“坦白”。坦白固然欢迎,未必会被认同,反而会归入“脚踩两只船”、“首鼠两端”的另册。袁世凯日后的境遇是
受到信任和提拔,则他的告密应当在训政之前。比如袁世凯戊戌日记里就没有交代他19日的动向,而这也正是他获悉了康有为政变计划后的第一个白天,他去见过什么人呢?有人判断袁在20日回津之后即向荣禄汇报,22日通过杨崇伊将消息从天津带回北京,23日告知慈禧太后,但这种推论没有史料支持,而在24日捕拿新党人物时,也没有将谭嗣同特别列出,谭在抓人谕旨中的排名,位居四章京第三,不过是作为新党人物同案被捕而已。难道这个告密直到27日才由荣禄当面报告太后吗?这似乎能解释迟至29日,上谕中出现了康有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名,但没有细节,也没有涉及到谭嗣同。近百年来,人们翻遍了故宫档案,迄今没有找到一件关于此案的人证物证,因此也就无法真正回答袁世凯何以得到宠信的缘由。或说在政变后的某天,消息才传到北京,京津道上,往来之人固然很多,与太后取得联系的中转渠道,可能会是庆王,但我从常识推测,假如庆王听说了围园劫后的“大逆案”,又岂能分清谁是真正的参与者,28日他敢布置人开脱杨锐、刘光第?
其实杨锐是张之洞的人,而非康党人物。他在入值后的私信中说:“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而康梁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更动。每日条陈,争言新法,率多揣摩迎合,甚至万不可行之事。兄拟遇事补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见。今甫数日,即已如此,久更何能相处?拟得抽身而退,此地实难久居”,就是一个证明。而张之洞在听说杨锐被捕后,致电正在北京的湖北按察使瞿廷韶,要他请军机大臣王文韶、裕禄出面营救,指出杨与康党无涉,是另一个证明。杨锐死后,盛昱作《杜鹃行哀杨生也》。诗中有“翻云覆雨骤雷霆,竟与逆人同日死”;“茂陵遗稿分明在,异论篇篇血泪痕”之句,说的都是当时熟悉内情的士大夫的看法。这些旁证,使我产生一个疑团:光绪的密诏为何在他手中从15日压到18日?这期间,杨锐是否对皇帝密诏提出的问题已有建言,比如赶走康有为换取太后的谅解,所以他要看一下皇帝的态度,直至见到17日的明发上谕,他才把诏书抄给林旭。同时,他似乎也应当对朝中大臣有所沟通和作出铺垫。让大老们确定他与康党的区别。他有没有向谁泄露过这封密诏?此类猜测还可以提出许多。经过百多年来历史学家的细致考证,戊戌政变的种种细节,有的开始澄清,有的依然扑朔迷离,给我们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这正是历史研究永远吸引后人的原因,所以我们还可以一代又一代地继续探究事实真相。当然,有些真相恐怕是永远也无法搞清楚了。北半截胡同的北口外,是著名的菜市口,清朝著名的行刑地。那天我出了浏阳会馆后,在菜市口流连了许久。菜市口地处宣南的交通要冲,当年就很热闹。史书记载菜市口刑场“东至铁门(胡同)南口外起,西至丞相胡同北口外止,每逢秋后朝审,在京处决犯人众多时,由东向西排列。刽子手亦由东向西顺序斩决”。这是一种严酷的治术。而那时的居民,并不因为挨近刑场而感到晦气,大家都愿意观赏杀头的红差。这又是什么样的心理?在中国近代史的浩瀚人物中,谭嗣同是我景仰的英雄。他是在这里死的。谭嗣同一直被认为是康有为的忠实追随者,也是个亦儒亦侠的传奇人物。但从前些年发现的毕永年日记《诡谋直纪》中,我们获知谭嗣同其实并不支持康氏搞政变的那套想入非非、一厢情愿的思路。而最令人感动的是,当局势恶化之后,康有为走避了,梁启超走避了,他却和林旭相约不走。站在过街天桥之下,我不由默念起谭嗣同的著名遗言: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是多么高尚的气节和献身精神!在一同殉难者中,林旭是前南洋大臣沈葆桢的孙女婿(沈是林则徐的女婿),也是个激进的青年才子,死时年仅23岁。林夫人闻其死讯,亦自杀殉夫。杨锐是张之洞的门生,在改革观念上更趋持重。但临危受命,正气浩然,目击者说他就刑之时,血吼丈余,“冤愤之气,千秋尚凛然矣”。刘光第遇难后,尸身不倒,观者惊叹,皆焚香罗拜。他的嗣子,伏尸痛哭一日一夜而亡。更有御史杨深秀,在慈禧重新训政,朝中形势突变,维新言论万马齐喑,大小官员正准备调整自己立场倾向的9月23日,上奏诘问光绪被废原因,要求慈禧撤帘归政。这份梗直和勇气,令我肃然起敬。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可以继续探讨,为变革流血牺牲的烈士却是不可轻慢,更不可以忘却的。“戊戌六君子”是在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的仁人志士,他们永远值得后人怀念。如今菜市口的丁字路口,飞架着一座过街天桥。宽敞的马路上,车流和人流匆匆来往。路东,当年监斩官歇脚并代为保管杀头砍刀的鹤年堂药店早已迁到路西,原址改为百货商场,喇叭里正播放着流传了半个世纪的时代曲《蔷薇蔷薇处处开》。关太太告诉过我:从前鹤年堂是有权用死囚的颈血作人血馒头入药的。此说使人想起鲁迅小说中的夏瑜和华老栓。中医是种古老的医术,但有许多奇怪的药引和偏方。为什么会想到人血呢?我不明白。谭嗣同也是想到血的。大约,在最古老最神秘的祭祀仪式中,血是巫师手中祈祷胜利与祥和的象征。
%%%附记一
在完成本文之后,我于1996年3月8日,利用去京开会之便,重访宣南,为本书补拍一些历史照片。在原南海会馆,我得知关胜勋先生已在几年前作古,关太太被送入敬老院。汗漫舫的门紧锁着,大杂院显得更为破落。一位邻居妇女正色地告诉我:这里属于私人住家,是不能拍照的。而更多的人,以为我是房产商,纷纷向我打听动迁的消息。他们似乎只有一个愿望:找到有钱的开发商,快把这旧房子拆了吧。
1996年记
%%%附记二
2003年12月,我再次踏访宣南。今非昔比,从前破旧的城区,造起了高楼大厦。本来,宣外大街到骡马市大街就打住了,形成一个T字形的路口。现在,南北向的宣外大街穿过骡马市继续向南,铲除了菜市口胡同到南、北半截胡同之间的大片旧宅,新辟出车水马龙的菜市口南大街,也有人把它称作“传媒大道”。从前的一些会馆房舍,消失在柏油马路之下。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借谭嗣同的光,得以保留西面的院墙,原来胡同深处的四合院,现在成了突兀的临街房子。从1995年摄下的照片对照今天的景观,我发现会馆外墙被贴上暗红色的墙砖,显得不伦不类。而院子里,莽苍苍斋更加陈旧不堪。浏阳会馆北面,耸立起一栋栋据说为21世纪“传媒人”准备的高档住宅。一个居民问,这房子什么时候拆啊?我说,这是文物,大概不会拆吧。居民说,那老百姓在这儿怎么过?我说,前面不是盖了许多高楼吗?居民说,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是拆迁,也住不到那房子去。而北京的朋友告诉我,这里由于靠近菜市口,新楼房很难出售。
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还在,门前堆满了垃圾和蜂窝煤,旁边还有等待转让的小发廊。南海会馆对面的54号,是栋民国时期的西式两层建筑,一位在这里住了七十余年的老人说,这儿曾经是婚丧嫁娶轿子租赁铺,相当于如今为年轻人结婚提供豪华轿车的服务。这是目前米市胡同最气派的房子了,不知将来能否被有“文化眼光”的传媒大道开发商们相中,创办一个充满怀旧风情的婚庆公司?
2003年12月记
《天公不语对枯棋》 落尽夭桃又侬李落尽夭桃又侬李(1)
落尽夭桃又侬李——从八大胡同想到赛金花
一
1990年2月的一个下午,阴霾满天,似乎将要下雪。我在瑟瑟寒风中逛了一圈琉璃厂书肆,也没有找到可意的书。这时,我忽发奇想,决定到从前的八大胡同去漫游一回。“八大
胡同”是北京前门西南隅八条胡同的统称。清末民国年间,为娼优聚居的芳菲之地,名声极大,类似南京的“秦淮河”、上海的“四马路”,用一个笼统的地名作红灯区的简称。究竟哪八条胡同,就说法不一了。《清稗类钞》载:
京师八大胡同,……即石头胡同、胭脂胡同、大李纱帽胡同、小李纱帽胡同、百顺胡同、皮条营、陕西巷、韩家潭是也。……或谓有十条胡同,则益以王广福斜街、樱桃竹斜街是也。《都门识小录》则引用一首竹枝词作介绍:
八大胡同自古名,
陕西百顺石头城。
韩家潭畔弦歌杂,
韩家潭。
陕西巷、百顺胡同、石头胡同。
王广斜街灯火明。
万佛寺前车辐辏;
二条营外路纵横。
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我从琉璃厂东街迤逦东去不远,穿过桐梓胡同,来到樱桃斜街和铁树斜街,就到了八大胡同的地面了。寻找一番,得悉不少巷名在1965年已经更改。比如铁树胡同,便是当年的李铁拐斜街;大李纱帽胡同,改称大力胡同;小李纱帽胡同,改称小力胡同;韩家潭,改称韩家胡同。我不由想起王广福斜街,在更早的时候,是叫过王寡妇斜街的。当年清人评论说:改动数字,“地名稍雅,而失其真矣”。但在今人看来,保留这类地名之“真”,似乎并无意义,且看洋洋洒洒百余万字的《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就是不设“八大胡同”辞条,读者不难体察个中端倪。
这里是非常普通的旧城区。道路狭窄,街道两侧都是灰暗斑驳的围墙。透过漆皮剥落的院门看去,院里没有什么花草点缀,也没有影壁游廊的痕迹,见缝插针般挤满了低矮的红砖或灰砖平房,显得密不透风。那平房,多半也是简易式的,似乎没见到卷棚顶或硬山顶的大房子。与走在鼓楼、西四一带的小巷,没有特别的差异。间或有几幢二层楼的半中半西砖式建筑,由于年代久远,也已残破不堪。对比刚刚走过的按照清代街面风格“穿靴戴帽”,粉饰一新的琉璃厂东、西街仿古建筑群,再遥想当年笙管弦歌、缠头争掷的风流景象,今日的八大胡同便更显得寥落和残败,犹如一具早已僵死的爬行动物遗蜕下来的躯壳,看不到半点温柔乡、销金窝的风韵。我料想,这里的每个院子,都有自己悲欢离合、如泣如诉的往事,踌躇许久,终觉不便串入某家,去细询昔日金粉勾栏的详尽情况。
二
有学者认为,妓女是人类历史上除了祭司或巫师之外第二项最古老的职业。中国的妓院史可以上溯到两千年前。但在清朝咸丰、同治年前,朝廷禁律较严,士大夫涉略花丛、挟妓冶游,例须革职。道光十八年(1838年),庄亲王奕、辅国公溥喜、镇国公绵顺等王公大臣,到东便门外的灵官庙去吸鸦片狎妓女,被当场抓获,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道光帝下谕革去他们的爵位。因此,这一时期京师的女闾业并不兴盛。文人相聚,无可遣兴,常招“像姑”唱曲侑酒。所谓“像姑”,是指那些二十岁以下唱青衣花旦的男伶,语义上,是“像个姑娘”的简称。也有用其谐音,叫做“相公”的。——北京人的缩略语常使人纳闷,眼下时兴把每乘坐十公里付十元车价的“大发”面包出租车(的士),说成是“面的”,便同“像姑”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当时,大多是文酒之欢,称作“好色不淫”。作为一种时尚,未必均是后人理解的断袖之癖。像姑们的居处,就在八大胡同一带,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