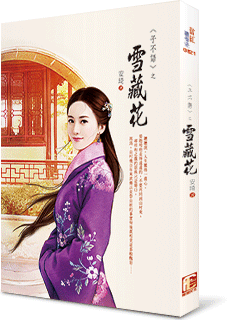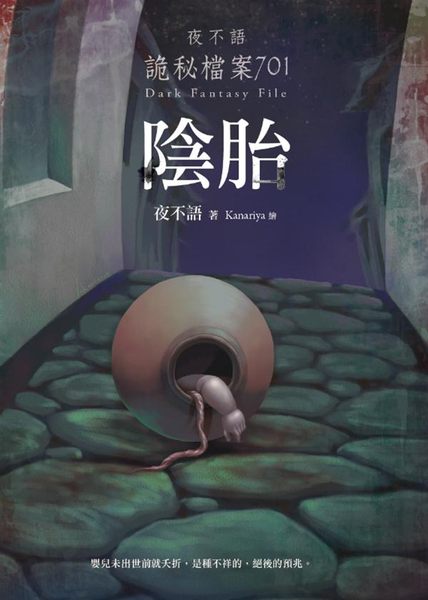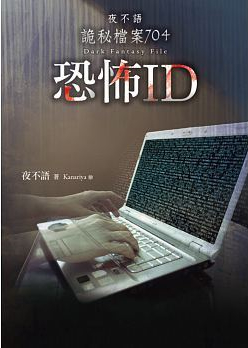天公不语对枯棋-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欲占三省,许之乎?抑拒之也?且中国非不振也,欲振作亦非难能也。前六个月吾告贵署曰:急收南北洋残破之船聚于一处,以为重立海军根本,而贵署不省。又曰练西北一枝劲兵以防外患,而贵署不省。今中国危亡已见端矣,各国聚谋,而中国至今熟睡未醒何也?且王果善病,精力不济,则宜选忠廉有才略之大臣图新政,期于未成,何必事事推诿,一无所成乎?
《天公不语对枯棋》 秋风宝剑孤臣泪难与运相争(4)
欧格讷显然书生气了。君主挑选宰相是为了办事,但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必然要虚化相权。恭王复出后的政治生态环境早已不同以往,加之十年赋闲的修炼,自然把一切看淡了,他又岂会再亟亟从事呢?
他的观念也在变化。到了戊戌年间,他更是多次谏言,反对变法。据说直至临终时,他还嘱咐前去探视的光绪,对主张变法的人,要慎重,“不 可轻信小人言也”。以致新派人物,将这位曾经倡导变革的老前辈,看成阻碍维新的死对头;而将他的去世,看成是立即推进变法的历史机遇。恭王的这种变化和结局,似乎也是政治舞台上许多老人的通例,对比青年时代的万丈豪情,真是不堪回首话当年了。
但恭王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对于他自己亲手写下的历史,有权力反思和发问。《萃锦吟》中,有一首“元夕独酌有怀宝佩蘅相国”的诗:
将茶代云觥,竹坞无尘水槛清。
金紫满身皆外物,文章千古亦虚名。
因逢淑景开佳宴,自趁新年贺太平。
吟寄短篇追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
据文廷式在他的著名笔记《闻尘偶记》中说,最后一联原来是“猛拍栏杆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诗意就大大值得玩味了。恭王何必要“猛拍栏杆”?“一场春梦”又指什么?他是否在含蓄地抱怨同慈禧太后的合作与结盟?假如没有这种合作与结盟,便没有北京政变和后来的洋务运动,那么,肃顺主持下的中国政坛又是怎样一番风光?
光绪的变法诏书,颁布于恭王死后第十三天,戊戌变法失败于恭王死后第一百十六天。光绪的一生,也是毁于慈禧太后之手,他和他的六叔,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悲剧人物。
恭王府花园虽是奕的旧居,但现在的陈列中,对奕只是简单提过,大多数参观者恐怕既不知晓、也无意弄清历史上的种种往事了。导游们更愿意津津乐道地谈论着电视剧里的和,不断强调这儿就是和故居,这对奕真是一种悲凉,对历史学家更是一种悲凉。离开花园的时候,我向独乐峰鞠了一躬,算是自我纪念了这位故去的老人。忽然想到,园子里为什么不为奕塑一座造像呢?
见过恭王的外国人说,他“虽是麻子,但是仪表堂堂”。见过他的京官陆龟蒙:《袭美留振文宴龟蒙抱病不赴猥示倡和因次韵酬谢》。
徐铉:《送萧尚书致仕归庐陵》。
刘兼:《江岸独步》。
宋齐丘:《陪华林园试小妓羯鼓》。
韩愈:《同李二十八员外从裴相公野宿西界》。
翁承赞:《文明殿受册封闽王》。
张泌:《寄人》。
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
何刚德说,他“仪表甚伟,颇有隆准之意”。都对他的相貌表示恭维。但从传世的照片上看,奕长得一点也不漂亮,面目中还带有点苦相。辽宁大学董守义先生撰《恭亲王奕大传》是本很好的传记,填补了国内学术研究的空白,但在讲到奕的容貌时,似乎也为尊者讳,说“奕前额宽阔,眉目清秀,鼻梁挺拔”,这就更无必要了。书中还引证何刚德回忆,“与奕共事多年的宝也说恭王‘甚漂亮’”。其实何刚德在《客座偶谈》中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原文是:“宝文靖尝对余言,恭王虽甚漂亮,然究系王子,生于深宫之中,外事终多隔膜,遇有疑难之事,还是我们几个人帮忙。”此处的“漂亮”,显然是指行事的手腕和气度。不知董先生以为然否?反正奕以亲王之尊,不需要靠相貌去找对象,长得漂亮不漂亮并不打紧。他一生共娶了八位嫡、侧福晋,个人生活还算是和满幸福的。
《天公不语对枯棋》 秋风宝剑孤臣泪半生名节——贤良寺·李鸿章(1)
一东华门大街往东走到头,穿过繁华嚣杂的王府井,对面是金鱼胡同。
金鱼胡同比一般胡同宽,长五百四十米,可算是条马路。著名的吉祥戏院和东来顺饭庄都设在这里。东安市场在胡同里也开有北大门。再往东,是和平宾馆,这儿本是清末大学士
那桐的府第。金鱼胡同中段与校尉胡同相交,沿校尉胡同向南到冰盏胡同(又称冰渣胡同)再往东转,那片毫不起眼的围墙里,便是从前的贤良寺。
贤良寺原在校尉胡同西侧,雍正十二年由怡亲王故邸舍地为寺,山门开在帅府胡同,约在今天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的东面。后身也到金鱼胡同。乾隆二十二年迁到现址,规模缩小了三分之二。
旧时,佛教和道教的庙宇宫观并不是天天对外开放的,更不收门票。一般多在初一、十五开庙,接受信徒膜拜和香火布施。也有一年仅开放几天的,如白云观是每年正月初一至二十日,黄寺是正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等等。平常的费用花销,除了靠香客布施和做水陆道场赚取些收入外,大多依赖出租“庙寓”维持。唐代元稹在《莺莺传》中写到张生寓普救寺,遇借宿的崔莺莺母女,就可看出这种房产生意的悠久历史。如今在北京卧佛寺两旁,有六七个精致的四合院落,提供开会租用,名曰“卧佛寺饭店”,很有从前“庙寓”的遗风。我对贤良寺感兴趣,是因为这里在清朝时,曾是高级地方官员进京时常借宿的馆舍,更是直隶总督李鸿章进京时的行辕。那时李鸿章虽开府保定、天津,却以文华殿大学士的身份而据相国之位,是晚清政坛上炙手可热的大员。史载,李鸿章当时外出,必有一百名身穿灰呢窄袖衣,肩扛洋枪的淮军卫队作前导,贤良寺门前冠盖如云,风光一时。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因签订《马关条约》和《中俄密约》,为国人垢病,又被罢去直隶总督的职务,挂着大学士和总理衙门大臣的头衔,在京闲赋;1901年庚子之乱时,李鸿章奉诏从两广总督任上北旋,与各国公使谈判和约,也都住在这里。《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说:“东城名刹最少,只有校尉营冰渣胡同内贤良寺。……自李文忠侨居之后,已成什官行台矣。”
李鸿章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大体说来,他从镇压太平天国起家,以一介文人投身戎马,匡扶行将倒塌的帝国大厦。他目睹时艰,看到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于是大声疾呼必须改变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鼓吹“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亲手创建了工厂、铁路和装备近代兵器的军队,努力地想把中国引导上现代化的道路。他是朝廷内部贤良寺内仅存的旧建筑。其背景上的大楼,是在海军衙门旧址上建造的对于世界大势较有了解的少数领导人之一,从承认中国国力及技术装备不如外国出发,力主在外交战略上实行“以夷制夷”。奉“自强”为宗旨,奉“守疆土、保和局”为圭臬,力主“忍小忿而图远略”,努力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争取喘息和发展的时间,甚至不惜以重大妥协来避免与列强发生直接军事对抗。他是当时公认的外交家,有的外国人居然将他称做“东方俾斯麦”。可惜从来弱国无外交,他的外交实践,往往是代表中国政府在屈辱的城下之盟上签字。
今天的国人对李鸿章的印象已是很淡漠了。有之,也不过是个奸臣卖国贼的形象。我却不能忘记这个长躯疏髯,性情诙谐、饱经沧桑的老人。所以,我一直想到他曾经生活过的贤良寺一游。
二
1988年的最后一个周末下午,北京天空的云层呈现出一片奇诡的红色,有人猜测是地震的前兆。没有明媚的阳光,城市显得灰蒙蒙的,无精煤渣胡同是冰盏胡同南面的一条胡同,西面与校尉胡同相交,“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就在煤渣胡同,借神机营衙署办公打采。才到四点,已是薄暮暝暝。我和作家钱钢在踏访清末“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旧址的过程中,无意间来到了贤良寺。
清代北京寺庙之多,令人惊讶。据《北京文物胜迹大全》统计,仅东城区,有名称有地址的祠寺宫观,就有二百五十个。如今,绝大多数都已湮没、拆除,或是改作他用。贤良寺也不例外,残破的山门上挂着“校尉小学”的牌子。进校一看,天王殿、大雄宝殿和藏经楼全被改作教室了,厢房则是教师办公室。雍正、乾隆题写的御碑、钟鼓楼不见踪影。打听下来,原来毁于“破四旧”的浪潮。寺庙的另一部分,是街道纸盒工厂和区教育局机关。
天很冷。黄昏的乌鸦在“哇、哇”地啼号着,给人肃杀的感觉。在用山门改建的传达室里,一位老校工边给火炉添煤,边絮絮叨叨地告诉我们,当年赛金花就是在这里,劝说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不要杀戮无辜平民。在我的记忆中,瓦德西的总部设在中南海仪銮殿(今居仁堂),赛二爷咋会跑到贤良寺与他会面呢?看来,北京的每栋房子,都有自己的故事和传说。我向他打听李鸿章的故居,得知就在旁边的西跨院,只是早已与小学校园堵死了通道。
从前,西跨院在冰盏胡同也开有大门,现今关着。住户们都从校尉胡同院墙上凿出的小门进出,门牌是4号。进得院来,发现这是座四合院的最后一进,已与前院分开。院子气派很大,与我曾见过的某些王公贝勒府差不多规模。由于长期失修,梁柱上的油漆剥落殆尽,只留下朽木的枯黄颜色。北京人对住房挨庙是有讲究的,民谚曰:“宁住庙前,不住庙后。宁住庙左,不住庙右。”李鸿章是外来户,大概不在乎这类规矩。不过他住在庙右,可真是倒了楣的。
我在院子里询问谁是老住户,人们便把我们指向东屋。东屋果然住着一位84岁的老人,叫王懋章,是唐山铁道学院的退休教师,曾在比利时列日大学留学。他的父亲王稼成(号寿琪),据说是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的第一班学生,被清政府派往比国留学,授过工科进士,当过京汉铁路的总工程师。老人听说我们来访古,很热情地把我们招呼进屋里。
据老人说,西跨院是李鸿章出钱盖的。李鸿章生前曾在北房居住,后来也殁于这里。又
说《辛丑条约》在这里草签。李鸿章和贤良寺方丈甚为投契,许多人通过方丈走李的门路,带携得方丈也显赫一时。李死后,院子送给庙里,算作庙产。李鸿章用过的绿呢大轿,还一直存放在贤良寺的藏经楼。民国初年,烟酒公卖局局长张小松娶了曾经是赵秉钧内阁国务秘书洪述祖(即谋杀宋教仁案主凶)的下堂姨太太做老婆,搬到这里住过。老人的父亲是从1916年搬进这里的,当初,院子美轮美奂,如今则彻底败落。而他家,“文化大革命”中从北屋被撵出,和侄子分住东西屋,“至今没有落实政策”。
我环顾四周,见屋内杂乱一片,毫无高级知识分子住所的优雅。只有门边的墙上,挂着一堆德国制造的温度计、湿度计、气压表,和老人额上的皱纹一样苍老。老人笑笑说,这东西在欧洲很普遍,他已养成习惯,从不相信电台播送的气象预报。每当出门去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和其他退休老人闲侃的时候,就从这些仪器中自己判断是否要带雨伞。
我请老人带我们看看院子。他打开房门,用一句好听的吴侬软语说道:“耐走好!”我才知道他原是姑苏人氏。屋外已是一片漆黑了,天上的星星也很寥落。我仔细观察了联结北屋和东西厢房的短廊,不由想起李鸿章幕僚吴永所写的关于李在贤良寺生活的一段回忆,说李:
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到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一伺者为之扑捏两腿……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天公不语对枯棋》 秋风宝剑孤臣泪半生名节(2)
如今,短廊里堆满了蜂窝煤、大白菜和各种垃圾杂物,一只积满灰尘的日本“东芝”牌电冰箱的包装纸盒昂然耸立着,主人还不舍得将它扔掉,大约是要找个好点的价钱卖给收破烂的。廊外装了个露天自来水龙头,停了五六辆自行车。真是“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旧屋尚在,人事全非了。
老人认真地执着我和钱钢的手说:“听说明年这片房子都要拆了。你们能不能向有关方面反映一下,这里可是文物啊!”我默然。对于北京市的市政建设,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三
李鸿章的晚景过得很忧郁。
闲居贤良寺的时候,他曾感慨地说过:“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这自然是为自己开脱。中日甲午战争,决非无端发生,中国的失败,也与李鸿章对整个事态的判断及对政治、外交、军事战略战术的运用失误有着直接的联系。但他的另一番解释,却是很令人回肠荡气、扼腕三叹: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