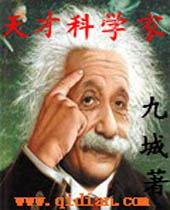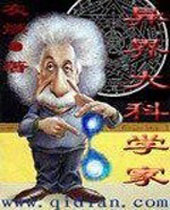献给非哲学家的小哲学-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个态度被延用到了对土地本身、对土地所生产的东西以及对土地所含有的东西的占有。但是,大部分国家的法制对这种占有规定了种种限制:在法国,一块土地地下的物产不属于这块土地的所有者,而是属于国家。
今天,在个人财产和国家财产之外,确定出“人类财产”,并承认由土地提供的自然资源属于全体人类,这应该是颇有道理的。
其中的道理从不可更新的资源来看尤为明显,石油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土地是从数亿万年前生活在地球上的微生物的尸体大量沉积开始产生石油的。一个漫长的腐烂分解过程将尸体变成了今天这种对我们来说极其珍贵的物质。这份由人类地球馈赠的礼物究竟属于谁呢?
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属于所有的人,既属于明天的人们,也属于今天的人们。挥霍石油资源,就像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所做的那样,这损害了我们后代子孙的利益,构成了一场真正的劫掠。把“人类共同遗产”的概念扩展到一切不可更新的财富上刻不容缓。这个概念已经被联合国采用,它无论是应用于地球周围空间存在的物质还是应用于产生自人类的杰作,都同样恰当。月球,亚眠大教堂亚眠(Amiens):法国索姆省的省会。该市的亚眠大教堂是13世纪哥特式建筑风格的代表作,也是法国规模最宏伟的教堂。 ——译注,还有婆罗浮屠寺院婆罗浮屠寺院(Borobudur):世界最大的佛教建筑之一,9世纪中叶建于印尼爪哇岛,是印度爪哇艺术的代表作。 ——译注,它们都不是哪一个国家的财产,而是人类所有人的共同财富。为什么不对自然奉献给我们一次,然而却不会奉献第二次的礼物抱着与此相同的态度呢?
第四部分自由
“只有冒着生命的危险,人才能保持自由。”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之集大成者。——译注
作为一位科学家,您看到,科学形成的是一种对自然现象清楚且准确的描述。而决定论是科学的原则。您因此否认自由吗?
对于自由的渴望是与思考未来的能力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惟有人类拥有这种能力。对动物来说,仅仅存在过去和现在。动物的行为,即使看上去是为了将来的某一个目的,其实也只是过去和现在事件的结果。发现将来,是由我们人类实现的,并且这一发现引起了我们对将来究竟是什么的疑问,不安与希望也由此产生,特别是产生了想使这将来符合我们心意的愿望。
然而这可能吗?事件发生的过程可以由我们的行动改变吗?任何答案都只能是无从核实的,就如同我们之外的任何现实的存在都无从论证一样。但由此引起的惟我态度岂不是否认真实地生活着的可能?而承认现实世界不单单是我们感官的一种幻觉,似乎更为可取。同样,我们似乎最好还是承认从今天到明天的过程中出现些波折是可能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介入其中,有所行动。
我们想要改变世界,我们又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逻辑上的困难正来自于此。我们由与其他任何物质相同的元素组成,进行相同的基本相互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将拉普拉斯的推理加以发挥,根据他的推理,宇宙在t时刻的状态决定了它在t+1时刻的状态。这样说来,任何自由都是虚幻的。
可是,这一推理没有考虑庞加莱关于“三体问题”的发现。一旦好几个决定性因素混杂在一起时,它们起作用所带来的长远结果是难以预料的。这结果延及所有“混沌”的现象,也就是说各种现象的进展紧密依赖于最初的条件。既然对这些起始条件认识的明确程度是有限的,那么预见长远的结果也存在一个限度。确认现实世界的现象难以预见,这并不足以表明自由是可能的,但这排除了自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有权自认为是自由的,至少在这个世界限定的种种约束范围内是自由的。这些约束,科学的进步可以使我不断地将它们描述得更好。
您有权觉得自己是自由的。可这自由的感觉难道不是一种幻觉吗?我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其实是被限定了的,比如说在社会的层面(社会文化决定因素、不平等、成见等等),而且从心理层面看,也是如此,我们的行为往往具有无意识的动机。只是我们对促使我们行动的真正原因知之甚少而已。
很显然,我所成为的这个人,是由我的基因遗传提供的全部信息和一切规则、行为以及周围人的看法共同造就而成的。我是具体机理与精神作用契合的产物。然而,这一产物具有如此的复杂性,竟至能够参与到自身的构筑中去。这种自我构筑使我们可以对我们现在所成为的人,尤其是对我们将来要成为的人尽一份力。
如果我只是单纯的外部影响的产物,那么我不过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物品,是我对之完全无能为力的一系列因果关系的被动结果。自我构筑的能力使得我从客体的地位转入了主体的地位。
我能够想“我”,也就是说,我能够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以第三人称谈我,这个看似悖论的事实标志着我拥有其他任何物种似乎并不拥有的奇特能力。所以,对我起作用的种种影响,我的先天遗传和我所处环境的种种限制,都成为或者说可能成为符合我自己选择的构筑物的材料。这些外部因素不再是促使我行动的“原因”,而是促使我进行选择的动力。
至于无意识的动机,它们仅仅是冲动,并非必需的条件。我们体内的激素是引起我们行动的根源,但是我们能够运用激素,而不是局限于受它们的控制。性激素诱使我们进行性交,可我们却从性交转入了温存和爱情。
您说自由是无法证明的,可是您进行推理时,似乎已经把自由作为了一个事实,甚至可以说是作为了一种价值。
自由是人类的一项创造,就像尊严、权利或者爱情一样。从我们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开始,自由一直都是我们所构筑的现实存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我们自己来给我们的价值取向划分等级,一个民主的社会进行的是集体的选择,这个集体的选择确定出价值体系:自由、平等、博爱,或者工作、家庭、祖国。
自由不是一件白送给我们的东西。极少极少的一点财富便可以使自由的行使变得容易些,空着肚子保持自由是可能的,然而却是难以实现的。法律摆在那儿,保障各种自由,但是自由却常常被那些敢于违反先前法律的人获得。
您现在能够给自由下个定义吗?它是我们体能和智能的充分运用?它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决定和完成我们主动实施的行为的能力?
自由只有通过参照每个人在他人帮助下进行的自我构筑才可以被定义下来。因此,自由与为所欲为的可能性没有关系,后者只是出于惟一的一个理由:想要那样做。那其实是任性。
自由,是建立与我们周围人的关系的可能性。因而,自由不是单独进行的。“他人的自由一开始,你的自由就停止”,这句著名的格言蒙骗了我们。起码必须有两个人在一起,才可能有自由,更确切地说,才可能将人人都满意的共同生活准则一天一天地确立起来。
所以,自由从来都不是永久享有的。它并非一件只需保卫就行了的战利品。我们必须不断地来定义它、实现它,使它适应不断变化着的世界的形势。
可能只有创造才是一种独立的行为,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建设性的行为。因为创造是单独进行的,所以它不大受共同生活种种限制的影响。诗人、画家,他们不需要去捍卫他们写作或者创作自己想表现的东西的权利。自由有必要介入的只是传播阶段。我们生活的这个商业社会,确实不大有助于传播无视传统或者仅仅是不随大流的作品。我们的社会满以为已经任随人们自由地进行创作,而实际上却将带来革新的人——比如莫迪格利亚尼莫迪格利亚尼(AmedeoModigliani,1884~1920),巴黎画派的意大利画家,其作品以人物形象为主,这些形象通过夸张变形而被拉长,给人一种线状的感觉。——译注——置于死地,把他们全打入到悲惨的“巴士底狱”之中。
我愿意引用弗朗索瓦·密特朗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Mitterrand,1916~1996),法国政治家,1981~1995年任法国总统。——译注的一句话:“对创造者的尊重与否是自由的晴雨表。”
您是同意伏尔泰的观点还是同意马拉的观点?
伏尔泰伏尔泰(FranoisMarieAronet,又名Voltaire,1694~1778),法国文学家、哲学家,启蒙时期的思想家。——译注说:“我憎恨你的想法,但我将竭尽全力使你能够把它们表达出来。”
马拉马拉(JeanPaulMarat,1743~1793),法国医生、作家和政治活动家,1793年遭暗杀身亡。——译注说:“与自由为敌的人没有自由。”
我们应该让狂热派、绝对传统派闭嘴,还是应该宽容些?比如说对于煽动种族仇恨,我们也应该宽容吗?
您怎么看通常进行的审查?这种——针对色情影片或暴力色彩浓烈的影片——审查一般是合法的吗?
当然,应该听听伏尔泰的话。但是我们不能回避“与自由为敌的人”提出的问题。
理想的情形是,我希望什么都能说,包括我完全否定的东西,例如亲法西斯主义或种族主义的言论。不过,我希望教育的普及足以使这些言论不至于伤害人。我们离这种状况还相差很远。因而,我们必须暂时依靠强制来与反对自由的人作斗争。
对于那些由于还未受过教育而脆弱、易受伤、没有防卫能力的人来说,问题就不同了。显而易见,尤其应该让儿童避开暴力和色情场面的侵害。
关于“伊斯兰教头巾”的争论已经平息下去了,但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我们可以在所谓昭示信仰的标志方面宽容什么?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态度?
学校是人们学习宽容的地方。于是,表明皈依某种思想体系的任何外部标记倘若支持了一种传布信仰的热忱,那么就应该被禁止在学校出现。
如果头巾只是一种衣着方式,那它不会带来什么问题。但是,“伊斯兰教头巾”是表明年轻的伊斯兰女教徒要忠诚于她的宗教信仰就应该佩戴它的一种方式。这样就关系到了给那些认为不戴头巾好的女人们造成的压力问题。根据这一点,头巾问题不能宽容对待。
政教分离是一切懂得尊重别人的观点和行为得到接受的结果。阿克纳东法老阿克纳东法老(Akhenaton):即阿梅诺菲斯四世(AménophisIV),约公元前1372年~公元前1354年统治埃及第十八王朝,在埃及创立了专一信奉太阳神Aton的宗教。——译注提出的一神论实际上是政教分离的基础。问题不再是以一大堆神的名义相互中伤,而是看到人类在其将来的统一性。
第四部分数学(与逻辑)
“数学是一门人们不了解讲的是什么以及不知道讲的是真是假的学问。”
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剑桥大学教授,一生致力于对逻辑学、数学和认识哲学进行理论思考。他也参与政治活动,在1914年,他是和平主义者,并倾向于人道的、自由的、政教分离的社会主义。他写出了大量著作,《意义与真理的探究》便是其中的一部。——原注将数学概念与逻辑概念联系起来,是哲学上的一贯做法。您觉得这样做有道理吗?逻辑是运用阐明了的并且视作已被接受了的规则来严密地展开推理的艺术。
数学是用其功能已通过实际经验表现出来了的符号将上述推理记述下来。这有点像中国的表意文字表示事物或概念的方式。
经验表明人们经常遇到无穷项之和,其中x是一个任意数:
x0+x1/1+x2/1·2+x3/1·2·3+……+xn/1·2·3·n+……
这时,用一个简单易写而且几乎不占什么地方的符号来表示这个和就方便多了。于是约定俗成地,这个符号为“ex”。
同样,在一个直角三角形中,人们常常要求一条直角边与斜边的长度之比,于是人们一般都把这个长度之比称为“sinusa”,其中a为这条直角边所对的角。
要揭开数学的神秘面纱,有必要看看想通过公式化来缩略推理记述的“懒人们”的发明。不过,这种公式化的活动只是一种简单的抄写活动,抄写人通过经验找到最好的办法来简化自身的工作。
相反,公理化要精妙得多,这种活动在于阐明人们在即将提出的推理过程中同意遵循的规则。
我们谈的离现实距离甚远。数学是纯粹抽象的,还是也扎根于现实之中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回答:两者兼而有之,我的上校。我可以通过创造“零”的经过来说明一下,这个奇特的数字奠定了整个算术的基础。
这边是三块石头,那边是三棵卷心菜。你能分清这两边吗?——当然能!我这边拿掉一块石头,那边拿掉一棵卷心菜。你能分清这两边吗?——当然能!我再拿第三次,看清楚了。你能分清这两边吗?——当然不能,什么都没有了。——好极了!你已经承认,如果一个集合是空的,用数学家的话讲,也就是如果一个集合的基数是零,那么它与另一个空集没有区别,只有一个空集,更准确地说,我把空集集合的基数叫做“一”。于是我们便创造了数字“一”。然后,再创造接下去的数字,就是小孩子的把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