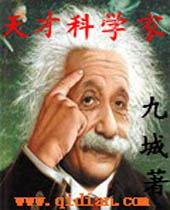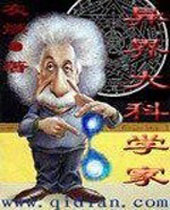献给非哲学家的小哲学-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续的推理,我们可以为一切罪行辩护!
然而,同种推理,反方向进行,也会走向荒谬。当然,我尊重婴儿的生命,所以,我就应该尊重胎儿的生命,尊重胚芽的生命,尊重受精卵的生命,尊重卵子,尊重精子!可是,夫妻双方没有赋予生命的卵子和精子不计其数,为它们的命运哀叹,恐怕也不是易事。
我们不能按上述方法看待堕胎问题。生物学只是描述事实,并不提供道德标准。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态度。我的态度是,如果年轻的母亲在考虑成熟之后,认为堕胎对她来说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我尊重她的决定。我把对母亲的尊重放在对她所怀孩子的尊重之先,而同时我对孩子也是非常尊重的。
这种思考活动,我不能孤零零一个人进行。关于这一点,就像我们谈到的基本问题,个人意识只有在集体意识中才能生根,因为我的意识是在与他人的接触中逐步发展的。
意识必然也具有时间性,具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人类主要的贡献,同时也是最初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的东西,毫无疑问,是他们想像明天的能力。的确,熊、松鼠看到寒冷来临,会采取预防措施,会积累脂肪或者食物以使自己能够挨过整个冬天。然而,这不过是由温度引起的生理反应。它们储存食物,是因为天气冷,并不是为了度过冬天。意识到明天将存在,并且能够对明天有所影响,是人类特有的能力。
那借用拉康
雅克·拉康(JacquesLacan,1901~1981):精神病科医生,伟大的精神分析学家。他于1964年建立了“巴黎弗洛伊德学院”,1980年解散了该学院,代之以“弗洛伊德事业学院”。——原注
的说法,您也是把意识视作“现象发展的顶峰”。这不是与神人同形同性论如出一辙吗?
假如我是氦原子核,我会惊叹碳原子的能力;假如我是碳原子,我又会惊叹……如此连续下去。到最后,就成了人类惊叹惟一比自己复杂,从而也比自己拥有更多能力的事物:人类共同体。意识,被赋予我,其实是因为我属于它。通过意识,我投身到宇宙朝渐趋复杂的状态不断跃进的过程之中,而这一跃进的过程正是宇宙演变的实在意义。所以,正是由于意识,一切日常事件才具有了意义。
说到底,在笛卡儿“故我在”中使我感到不妥的,是“我思”的自主性。因为思想只有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才能产生和发展。没有不需要外部滋养的意识。我成为我,是依靠他人。从某种角度上说,当我思考时,我就离开了自我,自我不再是存于皮肤之内。我是我与他人交织的全部关系。
那您一定同意弗洛伊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译注在《应用精神分析论》中说的话:“我不是自己居所的主人。”
这个说法好极了,不过弗洛伊德应该用让人高兴些的语气来表达这个结论。我不必为不是“自己居所的主人”感到悲哀。声称自己是“自己居所的主人”,是奥古斯都奥古斯都(Auguste,公元前63年~公元后14年),罗马帝国皇帝(公元前27~公元后14年在位)。——译注式狂妄自大的表现,奥古斯都就“既是他自己的主人,又是宇宙的主人”。万幸,世界并没有组织得如同一支军队,有着森严的等级和纪律;万幸,我的“居所”并不是一座兵营,有着围墙、布成方阵的床铺和维持秩序的卫兵。
我的居所,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都是一处开放的场所。过去的人、被遗忘已久的人不告而来,重新出现在这儿;样子常常显得奇怪的陌生人也来到这儿,搁下意想不到的财富;甚至不经意间积下的灰尘在被一股穿堂风拂起的时候,也会变成云,变成梦的来源。形形色色的人和物在我的居所中相互碰撞,自发地使这里成为一个宁静祥和的角落,那里成为一个叫嚷和争执的区域。不时地,命令的欲望显露出来,但除了死亡,谁又能强加命令呢?
居所里的每个房间都热情欢迎我,令我喜出望外,于是,“我”怀着越来越强烈的幸福感在居所里走动。地下室和顶楼想必藏着我不愿看见的东西,可能是几具尸体。有什么关系!“我”面对着窗户,它是敞开的。
因而,自我没有自己的居所,它存在于我进行的交流之中,存在于我与他人交织的关系之中。
它还依存于先天遗传。我不知道自己的过去,也就愈发无力做自己的主人。
自我们出生起,甚至在出生之前,我们的头脑就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结构,形成了一些系统,来支持我们的种种“智力”能力,比如记忆、想像、激情……一切都在这个由不计其数彼此紧密相连的神经元连成的复杂结构上留下痕迹。无穷无尽的组合发挥着作用,我们近百年的生命(也就是30亿秒而已)里发生的所有事情最终也不会使其穷尽。每时每刻,神经元系统中都有极小的一部分被用来感知和表达。在我们看来,这“有意识”的一部分是惟一真正活动着的。而事实上,我们整个脑部的思维活动一直在秘密地进行着,并且由我们先前历程中所保存的一切成果记录了下来。
无意识,则是指全部的思维活动在某一时刻脱离了感知和表达的对象。
既然我不是自己的主人,那您是说,我是无意识的奴隶?
不。我们经常犯的错误,是把无意识当成一个有着自己的性格,有着一定独立性的人,阿兰阿兰(EmileChartier,又称Alain,1868~1951),法国哲学家。——译注提醒了我们。给此概念命名的做法致使我们将其看做某个人。在科学领域,在说到“偶然性”一词时,我们也会犯类似的错误。我们将偶然性与必然性对立,也就是说与决定力量的作用对立,将偶然性等同于用来搅混牌局的小聪明,从而使得预计中的事情不那么确定。“偶然性”变成了活跃在状态转变过程中的演员,这与科学赋予这个概念的角色根本不吻合。
同样,无意识本身,不是演员,也并非什么怪物,它是对一个人的反应进行解释的众多因素之一。
真是复杂。无意识,就如您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额外的复杂因素。
举性欲的例子:激素、肾上腺素或者性激素,或多或少一点点,就可以使我们整个的神经元活动发生变化。但是,人脑的超复杂性使得人脑不会任分泌激素的内分泌腺和传送神经冲动的神经元之间只发生一种简单的因果联系。雄性动物看到雌性动物时,它的内分泌腺产生反应,脑部接收到信号并引起一连串的动作,因果的一致性促成了交配。人脑打乱了这一过程,将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介入其中,使得结果无法预料。由自然协调得很好的生殖器官活动改变了规则,其他的器官参与发生作用,特别是人脑,还发挥着回忆、激动、排斥、计划、想像等等职能。交配不再是中心环节,它只是一个细节,甚至只是一个借口,一个为了引起某些人称之为“爱”的激情的借口。
换句话说,与阿兰和萨特相反,您不打算借口无意识置疑了主体的绝对权力从而削弱无意识的影响。但是您并没有对此感到不安。
我也不对影响了我行为的无意识的无法预料性感到不安。我关心明天的天气,可是我很高兴自己不能预见它。我面对此类事情的反应往往令我自己吃惊。我思索其中的原因,但是我知道,一般说来,我只会找到一些片面,甚至虚假的理由。我要去看看顶楼,那儿藏着我的无意识,不过我知道自己无法找到它。我对这一切感到满意。毫不夸张地说,我就像是一艘小船的领航员,这艘小船被突然的、莫名的旋涡摇晃,然而我仍旧是它的领航员。“不可判定性”带来的笼罩在我决定周围的浓雾只是极其有限地限制我的责任。
我的无意识可能正在角落里暗暗策划着将在我身上引起的反应和将在我头脑中萌发的想法。它并不真的使我害怕。所有的“他人”也不使我害怕,他们侵犯我、反驳我、帮助我、爱护我、成就我、扰乱我,因此我不能没有他们。
第二部分人口统计学
“人人都是集体的影子。”
保罗·艾吕雅保罗·艾吕雅(PaulEluard,1895~1952),法国诗人。 ——译注
您曾经是国立人口统计学研究所人类遗传处的负责人,您还参加了对非洲孤立民族的研究。您在多贡人多贡人:黑非洲民族,多居住在马里(Mali)、尼日尔河湾及班迪亚加腊(Bandiagara)山崖地区。——译注、图阿雷格人图阿雷格人:南撒哈拉地区的游牧民族。——译注居住的地区呆过吗?通过跟他们的接触,您有什么想法?您的结论是什么?
我在国立人口统计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主要从事人类孤立群体遗传进化方面的研究。该研究在最初一段时间里是纯理论性的。它涉及到确立一些方程,来说明一个自我封闭群体遗传上日益耗竭的状况。在研究过程中,我渐渐致力于确定描述这种孤立状态以及遗传所处环境条件的参量。这就关系到测算、分析种群的人数,总结他们配偶选择的特点。因此,由人口统计学家整理出的概念和方法是非常宝贵的。
不过,这样只是构建了理论模型,必须将理论成果与现实对照起来。我有幸能够加入到研究队伍之中,那儿聚集着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像人种学家、医学家、血液学家……大家深入到地理或者文化上处于孤立状态的种群内部展开研究工作。这些孤立种群就等于实验室,在实验室里,理论模型所研究的过程正自然地进行着。
理论与现实对照最明白不过的结论,便是应该重新构建理论模型,在其中加入新的参量。逐渐,模型变成了更为有效的观察工具。
但是,孤立民族的文化与我们的文化是那么的远远相隔,当我接触到它们时,个人经受了极大的震动,面对这种震动,“科学”的进步实在是无足轻重。东塞内加尔的巴萨里人和贝迪克人、在马里与尼日尔边境地区过着游牧生活的图阿雷格人、格陵兰东部昂马沙利克昂马沙利克(Angmassalik):格陵兰东南部居民点,在昂马沙利克岛南岸。——译注
的爱斯基摩人,还有尼日尔河湾洪博里洪博里(Hombori):马里地名。——译注的多贡人,他们都启发我在琢磨漂亮的公式之外思索更加深入、更加关键的问题。这些男男女女,有着跟我们不一样的烦恼、牵挂和欢乐,他们使我不得不对这些概念的含义感到疑惑。
人口统计学家的工作是什么?他有哪些工作方法?
人口统计学是一门能够描述一个人类群体并分析其衍变过程的科学。在描述中,主要考虑两个个人特征:性别与年龄。人口统计学家使用的材料可以来自身份登记、人口普查、抽样调查或者其他带有特定目的的调查。人口统计学家从这些基本材料出发,确定一系列的商数和比率,这些数据确切地描述了对群体的未来和群体的死亡率、繁殖力高低都非常重要的种种特征。
特别是,上述方法还使人们能够通过假设对群体将来的情况作出预测。为了表明并不是宣布要发生的事实,而只是由假设推出结论,人口统计学家更喜欢说“预计”,而不说“预见”或者“预言”。
预计涉及的人口越多——最多是地球的全部人口——预计也就越准确。诚然,可能会出些差错,但差错往往可以相互抵消。当人们回头再看时,会发现过去的预计较好地道出了实际发生的变化。在1958年,联合国人口组织就相当成功地预测了20世纪最后数十年人口的数量:(单位:百万)
年份19601970198019902000
1958年的预计29103480422051406280
现实30143683445352016130
今天,仍然是这一机构,宣布到2025年人口的数量约计82亿,并且在21世纪后半叶将超过100亿。因此,有必要认真对待人口问题。
这些预计,既不应该看做是乐观的,也不应该看做是悲观的。它们纯粹而清楚,需要放到所有长远的计划中去考虑。因为,预计给出了变化的度,而如果我们还希望我们的子孙享有真正的人类的命运的话,这个度,我们是应当赋予人类社会建设的。我不认为这些数字应该像爱因斯坦提议的那样被视作一颗“炸弹”。威胁到人类的,并不是它们,而是我们无法从现在起就得出必然的、使人承认的结论:我们仅有一个世纪的时间来理清人口与可以妥善接纳大量人口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我责怪所有“决策者”,尤其是那些搞政治的人,他们的视线就只盯着下一次的选举,而我们生存环境的一场真正的革命正在酝酿之中。
人口爆炸是什么造成的?要采取哪些措施来避免超高出生率,缓解人类的繁殖?
我们人口数量的爆炸(20世纪初至20世纪末增加了三倍,最近40年间又增加了一倍)其实都归因于降低儿童死亡率的斗争所取得的进步。这些进步不需要高尖端的医术,它们主要是卫生条件改善和疫苗接种运动的成果。从前,婴儿出生率与死亡率保持平衡,而今天,我们因为在阻止儿童死亡方面取得越来越大的胜利,渐渐打破了这种平衡。要重新建立平衡,惟一的可能在于限制繁殖,这就意味着我们对生育的态度必须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生育在过去是一项义务,从今以后,它是一项有限的权利。
一个世纪略多的时间里,态度的转变在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现在,发展中国家需要完成同样的思想转变。转变越快,人口增长所带来问题的悲剧性越小。尽可能快速地达成平衡,符合所有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