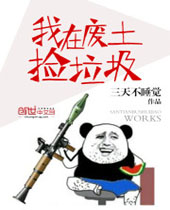在废墟上跳舞-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一脸颓丧地坐在我屋里,把发生的事情说得惊心动魄。但我似乎没多少兴趣听他说话,坐在那里安然地抽着烟。后来,他突然告诉我一件事,使我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说在我回来前的一天,有个公安局的来这里敲过我的门,同来的还有个年轻的小姐。
我仔细想了半天,心里才理出点头绪。通过分析判断,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李卫兵曾在这儿嫖宿的小姐被抓,供出了嫖宿地点。
我感到这地方再住下去,就会招惹说不清的麻烦了。
我下楼给李卫兵打电话,我说有重要事情要找他。他说,他正在忙一笔买卖,抽不出空。我说,你无任如何都要过来一下。他说,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直接说嘛,写作上的事你找小芹联系。我听到电话里有唧唧呱呱的声音,估计他在一个公共场所,不便说话,于是我只好把电话压了。
我又去找刘小毛,向他反复询问那个小姐长得什么样?刘小毛说,也没仔细看,我只是随意瞄了一眼,好像是圆脸,头发盘在头顶上。我一听,回想起过去李卫兵带来的那个小姐正是这种形象。我确定是那小姐在公安的逼迫下来指认嫖客了。于是,我再次呼李卫兵。他过了一刻钟才回电话。我刚拿起电话,就看见李卫兵的车已停在了离我十米远的地方。他摇下车窗,伸出脑袋向我大叫了一声。
我坐在车里,原原本本地把事情的经过给他说了一遍。他说,这点屁事就把你吓的。操,大不了交点罚款嘛。据说,公安部门每人都有罚款任务,说什么路上一个亿(交通罚款),桌上一个亿(赌博罚款),床上一个亿(嫖娼罚款)。这世道越来越邪了。他妈的,这不是变相鼓励你多嫖吗?你没看报纸吗?有个县派出所的居然还招小姐,还给她们配上呼机,鼓励她们多做生意,一有嫖客上门,他们就佯装去抓,所得罚款给小姐提成。他们的奖金全靠小姐啊。我不相信还有如此的荒唐事。李卫兵从车里拿起一份揉皱了的报纸丢给我说,操,你不相信,你自己看吧。然后他又说,现在发生的怪事比你们编造的还要离奇,可这毕竟是事实,人民的报纸党的报纸难道还有假吗?
从龙岩回来后,我呼过一次小芹。我们在一家酒巴见面。小芹的头发剪短了,发梢微微向上翘,脸庞显得比过去饱满多了,两只大大的眼睛在暗淡的灯光下,显得更加妩媚。我说,你为何把一头长发给活生生地剪了?她说,什么活生生的,你用词好狠。女人剪头发其实是想改变一下心情。她跟我说话的语气明显改变了,过去是热情、礼貌,现在是冷中带热,随意中带点倔强。我还感到她的眼睛有点深不可测的味道了。
周小雨也曾跟我说过类似的话。有一次,她把头发染成了栗红色,我一时感到十分别扭。我说,女人都怎么了,怎么有事没事的拿头发开心。她说,换换心情嘛。我一想,也就理解了。女人的身体能够改变的也只有头发了,头发是女人情绪的附属物,永远保持一种发型的女人几乎没有了。但我害怕她们把心情的故事写在头发上。
我说,过去人们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现在留长发的女人越来越少了,比男人的头发还要短,“和尚头”就更时髦了。头发短是不是见识就长了呢?这话显然毫无道理。
小芹说,如果是这样,我还想理个光头哩。
我笑了起来,那你就永远只有一种心情了。
她说,什么心情?
我说,尼姑的心情嘛。
她也笑了起来说,看来我真适合当尼姑了。
我开玩笑说,男人当和尚要六根清净,女人只要五根清净就行了。
她有点好奇地问,为什么?
我说,女人比男人少一根嘛。
她说,你们文人说话总往那东西上引。
我说,什么东西?
她不说话,低下头,拿着打火机打着火,然后又熄灭,这样反复了好几次。
我拿出一只银色的小发卡递给她。她突然醒悟过来,有点不安地说,这东西我用不上了。
我说,那我就收藏起来了。
她说,你愿怎么着怎么着。
在龙岩时,有一天,我竟鬼使神差地走到洋河的沙洲上,来到我和小芹做爱的地方。在那地方我突然发现了这根在太阳下发光的发卡。我捡起发卡,坐在那块巨大的卵石上,回想起我们做爱时的情景,心里还有种失落感。小芹躺下的地方还保留着身体明晰的痕迹,留下了几个明晰的手掌印。这纤细的手掌印显然是小芹的作品,在秋阳下,像远古时代的石刻,生动而有力,从掌形和纹路上,还可以明显看出挣扎的力量。
第50节:一个淫棍居然还教育起我来了
尽管李卫兵对嫖娼之事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但我的心里还是难以安妥。既然报纸上报道过多起荒唐的“处女嫖娼案”,肯定也有误抓嫖客的事件发生,只是误抓嫖客的新闻远没有误抓某个清白小姐“卖淫”有轰动效果罢了。这年头只是还没出现误杀某个贪官的报道。社会上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对贪官,只有漏网的,没有错杀的。
我对李卫兵说,你这地方我不敢住了,万一公安把我误当嫖客抓了起来,我有口难辩。
李卫兵说,操,你怕不清白,那你搬到桥洞里去住吧。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到公安局投案自首,还你一个清白?
我说,你他妈别胡扯了。这两天,我没心情写东西了,老在担心穿制服的人突然光临碉堡楼,把我请过去“说明白”,我能说明白吗?难道要我供出你?
李卫兵说,这样吧,你先找个地方把稿子写完,我好向老唐交代,拖的时间也不短了。
我说,这稿子也快使我精神崩溃了。吴迪回来后,邀我去办《生活乐园》周报,我答应了。你现在就给我找个地方,住上十天半月,好把稿子写完,我也好向你交差。
李卫兵摇了摇头,过了一会,他突然把车调转方向,说,你把稿子资料拿上,找个宾馆住上几天。操!
吴迪从龙岩回来后就到报社上班去了,在《生活乐园》干得屁颠屁颠的,像个大忙人。那天他夹着一沓新出版的报纸来找我,反复给我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思想工作。他说,报纸自负赢亏,就看我们有没有本事赚钱,报社政策好,报纸办得好不好对我们的能力也是个检验。再说,我们即使写作,也不能跟社会脱钩嘛。我翻着他带来的报纸,十几个版,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什么都有,社会时尚新闻也很热闹,只是感到做这样的事一定很累。对我来说,最难以适应甚至讨厌的还是和社会打交道,几年体制外的日子让我逍遥惯了,一旦回到集体的生活中,恐怕也难以找到艰苦创业、和同志们打成一片的心情了。我把这种想法一一给吴迪说了。不过我说的是一种模糊的心情,谈到眼前的报纸,我的想法居然还是一套一套的,让吴迪感到,我好像天生是个有办报经验的报人。我说,周报嘛,没必要每期像这样鸡零狗碎的,版式也不大气,做一个话题要力争做深做透,要激发读者参与的热情。每个版的策划要体现新、独、特,标题要动脑筋制作。我说了一大堆,吴迪的热情陡增,居然拿出笔一一记了下来,似乎很快就进入记者的感觉了。
我们说着说着就走进了旧城区的一家酒店。吴迪说,咱们这辈子干其他买卖也干不了了,办报纸还是条路子,印报纸等于印钞票。先赚点钱再说,这社会没钱,也遭女人嫌弃。吴迪说的句句话,都只有一个目的,要我马上跟他去“印钞票”。
我住在交通局下属的一个招待所里,别看这家只有三层的房子,外表灰旧,一点也不起眼,但里面的设施还是相当不错的,房间宽大,卫生间很豪华,据说是按星级标准装潢的。
住进来后的头几个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躺在宽大、弹力十足的席梦思上,居然想起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心事。我想得最多的还是周小雨,大半年过去了,竟毫无一点她的音信。她的决绝让我伤心,内心难以释然。我想起我们两年多的偷情日子,在没有未来的爱欲里漂浮,让生命能量彻底释放的堕落,是如此美丽。我在脑海过电影的时候,自然也想到了小芹,一个感觉不太真实的女人,我们短暂的经历,比未来还不着边际。我们根本就毫无未来,仅仅是在试探性地走过情感的沼泽。我记得李卫兵把我安排在这里时,还用神秘的带有警示性的口吻告诉我,小芹是老唐身边的人,住在交通局招待所,你的行为要注意一点,这儿的服务员基本上都是交通局的职工,难免别人说闲话。我对李卫兵说,你也别大惊小怪的,我能对小芹怎么样呢?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妈的,一个淫棍居然还教育起我来了。
住在交通局招待所里,我基本上闭门不出,也没跟小芹联系。李卫兵把我带来的时候,给老唐打了电话,老唐自然很快就同意了。
实际上,小芹早就知道我住在了局招待所。有天晚上,我出去吃饭回来,发现我的房间里多了一条红塔山香烟和十几包快餐面。我感到很奇怪,就去问一个值班的服务员小姐。小姐说她们也不知道谁来过。我说,真是奇怪了?小姐说,你出去没锁门吗?我说,锁没锁门我也记不住了。我很快就想到了小芹,这东西除了小芹送来,不会有其他人了。
招待所离交通局很近,我趴在窗台上就可以看见对面巍然耸立的办公大楼。我希望能够看见小芹的身影,还希望她以工作的名义来看望我。近水楼台边的月亮,反而可望不可得了。
这地方很不安静。晚上,招待所里的一家小舞厅吵得人心烦。当然,主要是我心不宁静,把情绪发泄到舞厅。如果再仔细追究,根本的原因还在小芹身上——我难以忍受那种欲罢不能的心境。
我把稿子铺开,写了几行字,胳膊就发麻。热闹中的孤独,像一只嗡嗡乱飞的蚊子,你怎么也找不到消灭它的办法。如果说在碉堡楼里住着有种与世隔绝的孤独,而住在一个公共的客房,四周的热闹就更让我有种过客似的陌生感和漂泊感。我是那种坚硬得不够柔软得也不够的情绪不定的人,用李卫兵的话说,我是个用错误对付生活的人。当我从他的嘴上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还吃了一惊,这家伙说话居然还有种哲理般的“深奥”。
我把笔一丢,就到马路上溜达起来。这里是繁华的市中心,往前走一百米就是更加热闹的文化广场。我坐在一处石阶上抽着烟,静静地观望着四周悠闲的人群,心里反而轻松了许多。在这儿曾举办过各种露天音乐会,我只记得叶雯在舞台的灯光下那洁白的身影了。在喷泉下,空气也在舞动,彩色的水雾像夜晚跳动的心脏,比一个梦还要虚幻。理想使人幸福地糊涂,可我们突然就清醒了,清醒得太势利了,也清醒得更加不知所措了。我们的生命在夜色下露出了丑态。
我想起多年前的一幕,也是在这个广场的草坪上(现在已铺成大理石了),我和一个写点小诗的女孩坐在月光下喝酒。在她一句玩笑的刺激下,我居然一口气喝完了一瓶酒,然后在草地上美美地睡了一夜。等我醒来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像个刚刚出生的婴儿,清醇得像早晨的霞光,我能够听到血液哗哗的流动声。我的影子在青草上的露珠里跳动……
现在我像个在草地里慢慢爬行的蜗牛,背负坚硬的躯壳,偶尔露出探头探脑的脑袋,来打量这个陌生的世界。
第51节:这叫“59岁现象”
回到招待所,我推门进去,一眼就看见了嘴尖眼红的李卫兵。他躺在床上吞云吐雾,远远地抛给我一支烟,说,老唐出事了。我张着惊谔的嘴,半天没有反应过来。我说,出了什么事?李卫兵说,他还能有什么事呢?肯定比什么吃吃喝喝、男女关系的事大,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小问题,检察院今天突然封了交通局的帐目,估计是贪污受贿的问题。
李卫兵又拿起手机打电话,一阵哇哇地囔着,不知他把电话打给谁的。我装出沉闷的样子,坐在那儿没有言语。其实,我心里顿时有种幸灾乐祸的轻松感。李卫兵说,前不久,老唐还向我借了五万块钱,说是急用。当时我就感到奇怪,他一般从不开口向我借钱的,再说我也从没拿钱向他贿赂什么,只是他儿子结婚时,我给了他两万元,算是送人情了。他在生馍细了我帮助,是事实,我应该感谢他。我说,你了解老唐多少呢?他正到了要摔跟头的时候了,某些官员好多都是?9岁的时候赶紧捞一把,这叫“59岁现象”。李卫兵说,现在事情还不清楚,谁也不要说。我明天通过朋友到检察院偷偷打听一下情况再说。你现在写了多少字?我说,快完稿了(实际上还差一大截)。李卫兵直摇头,操,你早点写完,钱也拿到手了,现在写完了还有屁用。我说,拿不到也罢,这东西把我折腾够了,报酬你看着办吧。李卫兵说,我给你的五千块,就算是给你的劳务费吧。
文章没法写了,交通局招待所我也没理由住下去,我满怀喜悦的心情又回到了与世隔绝的碉堡楼。我在楼下给吴迪打电话,把老唐出事的消息告诉了吴迪。我说,现在我总算彻底解脱了。他说,老唐坐牢,你有什么好高兴的。你的大作如果早出来,连你也成了遭世人咒骂的对象了。我说,三个月过去了,老子居然在给一个贪官写传记,想想,真滑稽,真是无耻!
我放下电话,一转身和刘小毛碰了个满怀。他说,这几天你跑到哪儿了?我去找过你好几次都没找到你。我说,我住在星级宾馆写作呢。我的话,令刘小毛羡慕不已。他说,在星级宾馆是不是每天都有小姐陪你睡觉?我说,那当然,要不怎么叫星级呢。刘小毛似信非信的样子让我感到莫名的得意。我又说,听说你谈了个对象,怎么没见到她到你这儿来?下次带来欣赏欣赏嘛。他说,你听谁胡说的,什么对象呀,是个迷路的哑女,我看她怪可怜的,就带到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交给警察叔叔了。我说,就你碰到这样的好事,你该不会在做人贩子吧。他说,如果我有


![天王[跳舞]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48/4876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