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长期封建专制下贵族所享有的特权地位,使法国社会其他阶层一直有着浓厚的贵族情结。这在18、19世纪的法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出身与血统代表着个人与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声望时,处于被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深感特权的重要。不仅政府高级官员认定自身在社会属性上倾向于贵族,企业主与专业领域的中产阶级也乐意将自己与地产主、官员和贵族联系在一起。以财富购得贵族名分为富裕家庭所热衷,那些工场主的新富们更渴望与贵族联姻,并热衷于购买破产贵族的不动产。有钱人不愿意将自己认作中产阶级,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等级中拥有特权的那一部分,害怕公民平等的概念会危及自己的生活,降低其社会地位,所以他们竭力表现自己与贵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更乐意把自己认作bourgeoisie,而不是中下层白领雇员与劳动者的middle class。
第三部分:法国 不谈阶级四法国中产阶级的特征(2)
法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似乎也支持人们拥有不动产。最近20年来,由于西方各国经济发展的强势受到遏制,法国中产阶级的工资收入也增长缓慢,与此相对的则是资本收入的快速增长。那些有房屋等家产的家庭,其家产价值大幅度上升。1990~2000年这十年间,职工工资购买力只提高5%,而财产税的税率却提高了25%。丁骥千,同前引文,第18页。这一情形更加强化了法国人对不动产的感情。
法国社会独特的发展历史决定了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传统贵族立场与价值观的崇尚态度。教育尤其是精英教育在对贵族精神的弘扬上作用显著。作为一个有着悠久血统贵族统治历史的民族,贵族地位身份的高贵与王权专制的不可动摇,决定了金钱不可能成为人们追求的唯一荣耀。贵族虽有着声望,却无权参与国家的行政管理;工商业资产阶级虽有可观的金钱,却缺乏社会对这一阶层的尊敬。其结果必导致有大量的公民珍惜精神享受,并推崇制造精神产品的人们。在这样的社会里,闲散的贵族乐意亲近知识,推崇艺术;渴望获得身份与地位的人意识到,自身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财富的多寡,高尚的情趣更可使他们得到财富之外的荣誉,也会在政界之外为自己创造一个无可争议的显赫地位。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291~293页。早期精英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知识阶层在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上都向贵族看齐,对艺术的崇尚影响了法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法国历代国王对艺术的爱好更加推动了法国文化艺术的发展。1699年,路易十四批准在卢浮宫举办首次皇家绘画和雕塑学院作品展,此后卢浮宫展览不断,还向许多优秀画家提供工作室,并对外开放。卢浮宫不仅吸引了法国的艺术家,更成为世界各国艺术家向往的殿堂。法国大革命使美术从宫廷走向大众:1793年,卢浮宫作为国立美术博物馆对外开放;七月王朝时期,在卢浮宫举行的巴黎沙龙成为一年一度的艺术盛事,常常吸引上万的观众。
作为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辉煌的思想、文化与艺术成就对欧洲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自18世纪始,巴黎就牢牢奠定了它“世界文化艺术之都”的地位。这与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发展,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在法国人口中占有了相当的比例有直接的关联。中产阶级人口的增加,保证了人文科学与艺术在法国拥有数量庞大而且固定的阅听人,为相关领域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基础。启蒙运动的先驱们,几乎都出身于不同的中产阶级家庭。孟德斯鸠的父亲是军人,祖父与伯父相继担任过波尔多法院院长,他自己也在27岁那年继承了伯父的职务;狄德罗出身于手工业者家庭;伏尔泰的父亲是个律师;卢梭的父亲则是钟表匠……他们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精神领袖,自在情理之中。19世纪的法国,文学、艺术大师群星璀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流派异彩纷呈。作家与艺术家们几乎也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莫里哀、博马舍、巴尔扎克、福楼拜、雨果、司汤达、大仲马、左拉、莫泊桑、雷诺阿、德加、马奈、莫奈……莫里哀(1622~1673),出生于一个巴黎的家具商家庭,负责向宫廷提供室内装饰;博马舍(1732~1799),出生于巴黎钟表匠家庭;巴尔扎克(1799~1850),出生于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法科学校毕业;福楼拜(1821~1880),青年时在巴黎学过法律,父亲是鲁昂市立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雨果(l802~1885),祖父是木匠,父亲是共和国军队的军官,曾被拿破仑的哥哥西班牙王约瑟夫·波拿巴授予将军衔,是这位国王的亲信重臣;司汤达(1783~1842),父亲是一个资产者、律师,外祖父是一个医生;大仲马(l802~1870),其祖父是侯爵,与黑奴结合生下其父,受洗时用母姓仲马;莫泊桑(1850~1893),出身于一个没落贵族之家,母亲醉心文艺;德加(1834~1917),巴黎银行家之子;马奈(1832~1883),父亲是内务部首席司法官。相比之下,作家中是左拉(1840~1902),画家中是莫奈(1840~1926)和雷诺阿(1841~1919)属于贫穷家庭出身。左拉7岁丧父,与母亲在外祖父的接济下生活,靠助学金读完中学,1862年进书局当打包工人,不久以诗作出众被擢升为广告部主任;莫奈一度随父亲居住在海边小城阿弗尔做杂货买卖,曾两次到巴黎求学,并于22岁时入古典主义学院派画家格莱尔画室学习,在那里结识了雷诺阿等人;雷诺阿则生于一个穷裁缝的家里,13岁便被送到瓷器工厂去学习手艺,学画瓷器、屏风等,他对绘画的兴趣即产生于此,并于1862~1864年间进入美术学校和格莱尔画室学习。他们的作品或以文字或以画面,从不同的角度对法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生活形态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刻画与展现。高老头、包法利夫人、于连……当时法国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产阶级各不同层次群体的代表人物,都没有逃过作家们的笔触。作家们对急于提升财富、地位、声望等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可悲、可笑与可鄙的行为所采取的或批判或讽刺或同情的态度,在精神上与贵族达成了和谐一致。文学所体现出的高尚情趣使法国贵族尤乐于与作家接近,更有许多贵族加入作家行列。作家、评论家、艺术家们也因此而成为等级森严的贵族沙龙的座上宾。文学、艺术从而吸引了法国许多缺乏财产和必要的社会保护的青年人,因为这条充满浪漫成功魅力的道路,可以帮助他们实现常规方式难以企及的自身价值,实现他们一生的梦想。
大众传媒的出现为大量来自巴黎和外省的中产或下层阶级的年轻人提供了梦想实现的机会。他们希望借此走上作家或艺术家的道路,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为到那时为止,它还一直是贵族或巴黎资产阶级的专利。作家和艺术家都知道,“只要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就会前途无量”,“因为从普通老百姓到资产阶级,从部长到王室,每个人都读报纸”,他们就是“通过报纸和连载小说无一例外地交了好运”。布迪厄,同前引书,2001,第67~68页。大量的中产阶级作者因报纸的兴盛而开始涌现,他们著书立说,迎合中产阶级阅听人的需求,向他们提供符合其口味的知识与见闻。法国历史最悠久的报纸《费加罗报》于1854年创办,今天其读者定位在财力雄厚的商界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被认为是最能体现法兰西“贵族风格”的报纸,而当年在第二帝国的严格审查之下,也曾布满了从沙龙、咖啡馆、舞台幕后搜集来的飞短流长;《国际先驱论坛报》1887年在巴黎创刊;今法新社的前身“哈瓦斯通讯社”创建于1835年《费加罗报》的前身是1826年创刊的《油灯》周刊;《国际先驱论坛报》是巴黎出版的英文日报,今天成为全世界新闻从业人员的所爱。“哈瓦斯通讯社”由夏尔·哈瓦斯创建;法新社是今天西方四大通讯社中资格最老的一个。……各类新闻出版物都在创办之初预设了一定的教育水准与休闲类型;其他文化机构如沙龙、大学、文学社、公共图书馆、俱乐部等,也都面向特定的消费群体,反映他们的喜好与价值观,因而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视觉与装饰艺术,对新书及新的文学作品的无尽的需求,现代报纸的产生,流通图书馆的迅速制度化……这些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都是中产阶级,由于急于将自己的财富在第一时间里转化为地位与不动产,以加强自身在统治集团里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乐意认同贵族文化。Doyle;William,“Reflections on the Class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61;No 4 (Fall;1990);pp743~748不仅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众如此,即使是控制了国家政权的拿破仑,也为赢得传统精英的支持,而鼓励因大革命曾一度销声匿迹的贵族沙龙重新兴盛,以平息上流社会政治上的不满。
第三部分:法国 不谈阶级五趣味区隔:文化资本造就的身份差异(1)
由于传统贵族所崇尚的高雅文化在法国具有的无可争议的地位,法国资产阶级对贵族声望与地位有着高度的认同,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法国人“爱贵族就像爱买彩票一样”,这促使他们努力占有大量的文化资本,从而得以确保自身高雅的文化品位,以与中下层中产阶级区别开来。法国中下层中产阶级意识到自身因各方面资本的欠缺,无法获得社会所承认的足够的文化素养,并实际导致其地位与声望的提升,因此他们总是竭力向社会的上层阶级趣味靠拢,同时又要拉开与位于其下群体的差异,各阶级间的趣味区隔以此凸显。Bourdieu;op cit
处于上层支配地位的阶级在经济资本、教育资质与文化实践等各方面所拥有的资本量都要高于其他两个阶级:他们有私人房产、豪华汽车或游艇,度假住宾馆,多数人有中等以上的年收入;他们的学历普遍高于劳动阶级,也高于中产阶级;在文化实践上,上层支配阶级中喜欢去剧院、听古典音乐、参观博物馆与画廊等的人也远远超过其他两个阶级。当然,布迪厄的重点并不在于阶级的划分上,他强调的是,实际上人们在文化实践亦即文化消费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趣味,才是把不同阶级区分开来的关键,而这与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具有等量经济资本的人不一定具有相似的文化趣味即是证明。因此,按照布迪厄的区分,无论从哪种资本的角度来衡量,中、高级教师在法国都属于支配阶级,处于社会的上层,自然也享有很高的声望与地位。
布迪厄依教育水平和社会阶级的相关性,以“非工作性阅读、去剧院、听古典音乐、参观博物馆、参观画廊、调频收音机、不看电视、阅读《上流社会》(Le Monde)、阅读《费加罗文学》(Le Figaro Littéraire)……”等为具体分析指标为法国各阶级划分出三个趣味等级:(1)合法性趣味(Legitimate taste),即对支配阶级所认可的艺术作品的接受与欣赏能力,这在对音乐作品的欣赏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在所有高雅艺术门类中,音乐最为“纯粹”——它什么也没有说,它根本就不需要说什么,然而它又实在蕴含了很多;(2)中产趣味(Middlebrow taste),这种趣味所接受与欣赏的,主要为那些二流作品,音乐方面如《蓝色狂想曲》和《匈牙利狂想曲》,绘画方面如雷诺阿,它们在中产阶级或支配阶级中的“知识分子”里最为流行;(3)流行趣味(popular taste),这里指的是对所谓的“轻音乐”或经过流行化以后的古典音乐的选择,如《蓝色多瑙河》。布迪厄在分析的过程中总是避免使用“精英”或“贵族”等字眼,所以我们看到,最高等级的文化趣味是一个社会的“合法文化”(legitimate culture),它由这一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所规定,因为它对大量文化资本或者学术资本的要求,因为它的纯粹性,而使“文化”具有了高贵的头衔与属性。Ibid;p227
在布迪厄看来,阶级所强调的不同生活方式,也就是韦伯所说的“生活的风格化”,是最具分析价值的,因为生活方式的差异最能说明个人生长的环境,自然也是阶级特征最具说服力的表现。它可以有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体现,在精神上它表现在最合法的领域如绘画、音乐等的喜好上,在物质上它则可以表现在最“个人化”的领域如服装、家具或烹调等的选择上。行动者在审美性情倾向和生活方式上的区隔特征在文化消费实践上表现得最明显。审美性情倾向的差异在物质上的指向是对生活必需品的选择。因为“没有什么比奢华物品,特别是文化物品更能表达社会区隔”,不同群体对必需品的趣味清楚地显示出阶级之别。劳动者对物品更看重的是其实用性,也就是物品的功能,而不是符号消费上的意义。对劳动阶级而言,必要性即是维持普通日常生活所需的那些必不可少的东西。与生存的必需无关的产品,他们常常不会费神去要拥有它。如果一个工人看到减价销售的手表要两百万(旧)法郎或是听说一个外科医生花三百万为儿子开个派对,他们会表现得不以为然,当然他们不是羡慕手表或派对,而是为那两百万没能花在更好的地方而耿耿于怀。
与马修·阿诺德将英国中产阶级称为“非利士人”马修·阿诺德在他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2)一书中将英国社会分为三大组成部分:贵族、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并分别以野蛮人(Barbarians)、非利士人(Philistines)和群氓(Populace)来指代。“非利士人”原为《圣经》中一与古以色列国争斗的民族,到了19世纪,这一词语有了引申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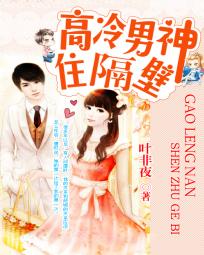
![[bl]捡来一只兽人攻-全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36/3657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