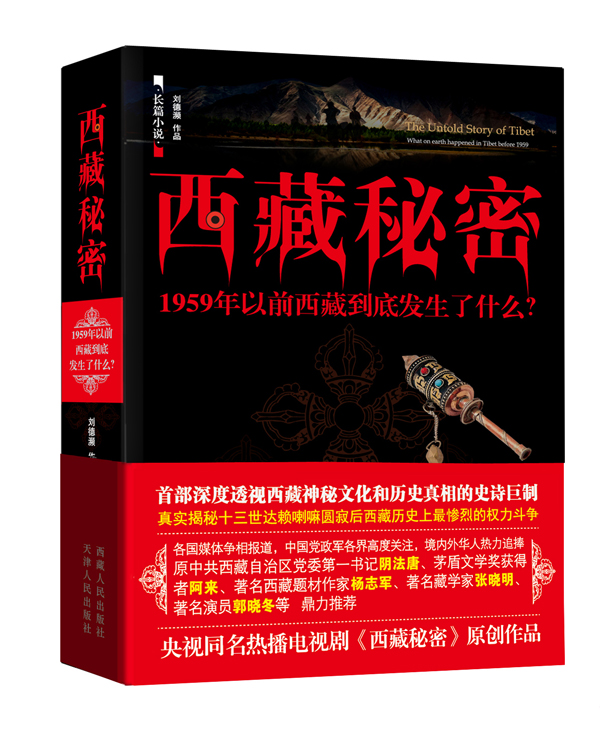飘过西藏上空的云朵-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尉宣布凡是存在老乡关系的,也就是只要是来自同一个县的就将打乱分配。
贵州的“瓜皮”分到了我所在的八班。“瓜皮”这个名字在我们进藏路上就被摔掉了。记得当时同车的战友问及他,有人就答:车过米拉山他就爬到另一辆车上走了。中尉点了两次“瓜皮”的名,没人答到。齐整的新兵队伍肃穆得像一座座灵塔。
第三部分:青春枕着西藏入眠往返米拉山 3
很快有个少校跑到中尉面前,不知说了些啥。我们只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劲,队列里有蜜蜂般的声音在空气中回旋……
第二天,从山上伐木下来,几个超期服役的老兵在地上抽烟神侃。从他们的话里,我由此想起了两月前车过米拉山的那个夜晚。我想,这一生我的那位战友他永远不会向别人答“到”了。
从此,除了整天的摸爬滚打,站岗执勤,我简直不敢单独出班的门,原因是出门就见山。我一直躲着那些山,还有半山腰被风刮得尖叫的黑鸦。
对于1996年6月来说,米拉山在我眼里成了雪域大地的一块无字碑。我站在这块碑前想了很久、很多。这不仅仅是一种思乡壮举。
那一年的米拉山没有雪,只有晶莹的冰凌,纯得像食品厂里的糖。它以一汪水的回忆流过中士1993年冬季的足迹。它没有了第一次邂逅的那种高高在上的神啸,而是以投降的姿势站在我面前无言。我久久地驻足,没有征服山巅的狂喜,没有怀古的伤悲;与山共舞的五色经幡,静静地依恋着高举天边的经杆。我在那些经杆下静静地坐着。我感觉有颗心和米拉山口高高隆起的玛尼堆贴得很近很近,所以我无法平静。我分明感觉脚下的灵魂在战栗,他用无声的誓言约束着一个士兵进行的生活制度。我仿若听见他说:与其做一只袅袅飞升天国的鸟,不如和米拉山守候一生。显然,这是去者与来者的对话。我体验过死,思考过生,在山面前,人的生命何其渺小!
山何时免于责罚一位脆弱的跋涉者。米拉山的空气弥漫着宗教的气息吗?苦于寻找通往西藏之路的人,你尝过“一边修路,一边进藏”的宗教吗?我们越是脆弱就越不能在山面前“竞折腰”,让我们在心里呐喊一百次:米拉山,我们是同你一样高的男人,米拉山,你和我们都是高原的守候者!
其实,人不应该只在山面前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我的长辈,我的前行者,在山面前是顽固不化的。尽管那是一个朴素的年代,他们见山不顺眼就必须挥舞十字镐钎,才有可能求得生存发展。我是后来者,我在说山的时候,山也在以另一种姿态审视我。我的父辈们同样会以走过西藏,或重临战场的目光审视我用青春与高原这一番对话。
但在山面前,我不是百依百顺的,也许我只承认我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战士。从进入西藏的第一天起,我就相信童话是蕴含真实生活的三维立体图。
一个战友已成了高原的一部分,或者说一个战友为奔赴另一个战斗集体从这座山出发了。我认为“瓜皮”之死正是“白天不懂夜的黑”所致。川藏线——这条被太阳烤晒得能挤出油的金光大道,夜晚毕竟还是少了些光和热。我后来得知“瓜皮”来自贵州贫瘠的毕节,他家也有眼睛不好使的白发娘亲,还有得了颈椎骨质增生而不能耕耘农田的父亲。我们进藏前在一起集训时,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一个喜欢朗诵英雄史诗的士兵,手里常拿着一本红色的英雄诗抄。他的与众不同遭到了大群川兵讥讽。他们都是些城镇入伍的,先是暗自里喋喋不休,后来竟面对面地指责、挑衅。
记得那天吃过晚饭,这帮城镇兵邀我在食堂后门的泡桐树下碰头。能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很激动,尽管心里有些担忧。我在那儿等着,至于等他们做什么,为什么要等他们,我一点也不知道。
“瓜皮”拿着一个大饭盒走出食堂的后门。嘲弄声便开始了,咄咄逼人的话从这帮城镇兵嘴里不断涌出。我先是不知所措,然后,在他们的怂恿下加入了其中。我的冲动竟然使我移花接木:你知道别人看不惯你什么吗……更有人冲上去猛拉他的衣领。纽扣掉了。大家都朝我一阵喝彩。
我不例外成了受害者,现在忏悔算不算觉醒!
虽然你已经走了,但我绝不能再叫你的绰号。因为那是一个喧哗与骚动的年代。为了澄清一个不再错误的事实,让我们在一座山面前,抱愧地叫一百遍你的名字吧——吴光荣——吴光荣……吴——光——荣……我们说你是英雄,所有死在米拉山的人,都是站立的英雄。
但米拉山却是一块无字碑。
我还想提一件事情。
军嫂雪儿是在我即将要离开那支山地快反部队的前几天看见的第一个女人。她不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她只是我在那个“只听黑鸦叫,不闻姑娘笑”的边远连队接待的第一个怀孕闯过米拉山的“非常”军嫂,而且是连队驾驶员李老兵的老婆。她来的时候挺着五六个月的大肚子,连队官兵都外出执勤去了。李老兵开车送连长休假去贡嘎机场还没回来。
雪儿一边收拾大包小包的行李,一边惊讶地对我说,米拉山厚厚的积雪把车的路都堵死了,满车的旅客只能下车推着车走。说完,她一声长叹:高原不仅是高原啊。
我问她:李老兵放心你来么?
她说:他当然不肯,只因我想他,肚子里的孩子想他,我要让肚子里的孩子一落地就能见到父亲,这对他很重要。
雪儿是个美丽的护士。从她来的那天起,我就有事没事地找她聊天。她仿佛知道的事情很多很多,她的出现给连队带来了新鲜气息。
我对雪儿说:我好想回家,好想早点回到内地上大学去。
雪儿说:这年头学校好多老师都下岗了,都在外面为生活奔波。有的学校已经三五个月没给老师发工资了。只要你肯学,连队也是大学校嘛。
雪儿的话让我为自己难过、伤悲。我在伤悲、难过的时候,雪儿还在不停地说,一副滔滔不绝的架势。我专心致志地听着。我满以为雪儿从内地带来的是一片繁荣景象,没想到听完之后让我忧伤一场。没想到我穿上军装来西藏当兵才几百天,外面发生的变化让人并不乐观,我真是个失败者。难怪昔日的同窗都来信骂我:笨瓜,不好好念书,要去部队讲什么奉献?
第三部分:青春枕着西藏入眠往返米拉山 4
雪儿喝了口水,抬起头问我:你咋不说话呢?
我一直没说话。我来到这个很难看见女人的边防就不怎么说话了。我以前是会说很多话的。我摇着头对雪儿说:我在听你说呢!
雪儿望着我不说话,好像她已把话说尽了。于是,我找些话来对她说:雪儿嫂,我真佩服你,现在佩服,以后也佩服,反正只要我还能正常思维我就佩服你。嫂子,你不仅是我看见的第一个怀着孩子闯过米拉山的勇敢的嫂子,还是我们西藏最美的嫂子,你是第一个穿越我们男人世界的伟大女性,你和那些轻装上阵来西藏走马观景的女子就是不一样,我们佩服你。
雪儿听了哈哈大笑,问我:佩服?你也佩服我吗?我不是一个好护士,也不是你们所说的好军嫂,更不是你所夸赞的伟大女性,我怀着孩子不要命地来西藏干啥呀?不就是在李老兵转业前带孩子来看看他工作的西藏么。
可你这样来西藏是很危险的。我说。
危险是危险,可你们西藏军人天天生活在危险的地方却从不说危险。我来了,我看到你们这些将青春交给西藏的娃娃兵,我就会想起李老兵死去的孩子。雪儿流着泪说,我对不住李老兵。
李老兵是成过家的人,不幸的是他爱人剖腹产的时候死在手术台上。那时我是值班护士,他爱人上手术台之前,医院一直在焦急地等待李老兵来签字。但医院最终也没等到他。由于流血过多,李老兵回来只看见三个归去的生命——他爱人和双胞胎。在李老兵难以接受现实的日子里,我走进他的生活,我和孩子来西藏接李老兵回家……
此时,我看见雪儿嫂的眼睛红得像兔眼睛。雪儿嫂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大概有些累了。看样子,她在盼望李老兵早点回来。晚上的熄灯号又响了。我站起身来,说:嫂子没事就休息吧,李老兵很快就会回来的。
雪儿嫂笑了笑,说:你也应早点休息。
四天过去了,李老兵依然没回来。按理说去机场来回顶多两天足够了。第五天、六天、七天,李老兵还是没回来。他甚至不知雪儿已到连队等他一周多了……
晚上,我做梦也没想到,传来的竟是有关李老兵翻车米拉山的噩耗。这种事虽然在米拉山常出现,但李老兵是一个老车手啊。他在部队干了十三年,年底即将转业走人了,米拉山真是有眼无珠呀。
这件事雪儿知道如何得了。
我跟着指导员悄悄赶到了李老兵出事的米拉山现场。站在山下,远远地观望米拉山口以下的“之”字形,修长修长的,看上去真像个巨人的脖子,而离脖子最近的就是吸光了所有氧气的山嘴。李老兵就是驾驶空车从这个缺氧的嘴边坠下悬崖的。冰雪在这个季节厚着脸皮紧紧地巴在我和指导员的脚上。我们顺着冬天滑下的那条伤痕看去,东风车已报废成了几块零星的散铁。
李老兵你在哪里?
我们分头沿着那条长长的伤痕找去。这时,一辆军车倏地停在路旁。车上走下三个人,其中一个是中尉。他穿着没有肩章的训练服,手里提着文件袋,朝我严肃地点头。一个上午过去了,我和指导员打消了还能找到李老兵的念头,于是消极地顺着一条小道往下滑。就是这一滑,我看见了血红的东西。指导员在前面滑,我在后面跟着指导员滑过的痕迹再滑。我对指导员说,有血你快看。指导员来到我指的地方,急忙扒开大团大团厚厚的积雪,我们看见李老兵早已成了硬邦邦的雪人。
中尉猜测,李老兵是跳车捡到命后被雪冻死的。
我很想把李老兵埋在米拉山突起的雪堆下,可指导员生怕风会把他吹走。我问随风而舞的经幡:你这条吉祥的飘带,为何总飘不走苦难啊?
雪儿知道李老兵再也不能回来后就好几天没说话。雪儿说什么也要去米拉山看看,就是天塌下来也拦不住她。雪儿根本没把米拉山当回事。
雪儿终于不辞而别。操场上吹出一阵凉凉的风。连队的官兵都回来了。
我沿着雪儿的足迹追去。我发现巨人的脖子上有一个少妇的身影,她从自己脖子上取下一条又一条哈达挂在了那块隆起的雪堆上。风一吹,看上去像一片片雪染的经幡。
而不远处就是风雪弥漫的海拔5 030多米的米拉山口。
两个多月后,一名男婴降临在油菜花开的川西平原,他的名字叫——李米拉。
当我第十四次站在海拔5 030多米的米拉山口的时候,是七年后的又一个正值老兵退伍、新兵入藏的冬季。我注视着这些倒下的英灵。吴光荣走了,李老兵走了,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从这里走了,只有我还活着。我活着的时候又来到了米拉山,这时,我耳畔响起了一首无声的歌:
除了真情/我还能给你什么/除了善良/我还能给你什么/梦想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也让我们一次次地错过……
第三部分:青春枕着西藏入眠往返米拉山 5
放眼望去,拉萨城头一辆辆载着新兵的车正向米拉山驶来,而山下也正好驶来一辆载着大红花的欢送车……
这就是历史的交接点。米拉山,上苍把所有该铭记的东西都放在了极地的苍穹。可我想把米拉山写进悲情的军旅,兵之歌将在无限的希望和绝望中结束——
在冬季 一个起风的子夜
我枯萎的枝头挂一轮残月
绿风的席卷
犹如我残缺在狂风中的翅膀
我独自走着
却有淡然如水的眼神
从面颊一茬茬滑过
我不敢安静地读这些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和我一千四百六十个页码的日子
军旗请把脚下的碎片燃在某个雪天
燃给那个天堂里爱枪的雪子吧
实在无法徜徉更多的心情
我已远征莽原
在与秋天的理想树走过季节时
我想象着大雪纷飞的日子
载着光荣花的军用卡车停在米拉山口
会有一群唱兵歌的鸟
高举神圣的风采
2002年12月一稿于拉萨
2003年11月定稿于成都
第三部分:青春枕着西藏入眠旋转的布达拉 1
旋转的布达拉
我瞻仰布达拉,我转动布达拉。
布达拉藏匿着历历在目的阴影,墙壁内侧全部用宝藏垒成光闪闪的眼睛,谁在沉睡的酥油灯下声声吟唱?捧读经文的人,为何看不清脸,轮回了一个又一个季节的转经筒,在人声鼎沸中渐渐地幻灭成夕阳西去的一抹暗影?历史的宫殿在蓝星球上旋转了多少漫漫岁月?我不得而知。
许多年来,有一个痴心妄想的诗人无数次走过它的广场,发现布达拉从来都不曾为自己的仰望静止一刻。墙外的阳光,落落大方。
那么多手掌贴着它的肉体。
那么多喧嚣呼吸它的灵光。
那么多箭头伸缩它的内部。
——它懂得百无聊赖的人间吗?我把自己站成阳光挂靠大地的影子。在一座明亮如水晶铺盖的广场上,两手空空地站在布达拉的眼睛里。站在远远的地方,慢悠悠地观望着一些形式多样的人和一座圣殿的红与白。
我看见的布达拉是旋转着的。
你很可能赞同,或保持怀疑。
其实,这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每天下午五时后,当拉萨河水被轻轻的风吹出皱纹,一座城市年轻的面庞便开始慢慢变老。这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