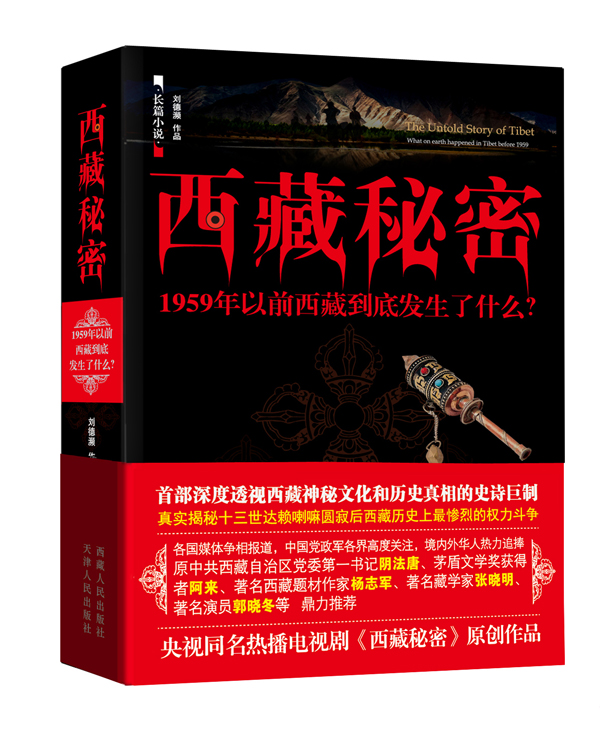飘过西藏上空的云朵-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统统收藏我的世界。在风的背后,在远处的月光下,我知道比月亮更明亮的是藏羚羊的眼睛。多年以后,每当在黑夜里行走,那些擦亮“可可西里”这个名字的眼睛就成了照亮我文字的灯。
在风里,在风的阻力与推力下,我走近了一只受伤的藏羚羊。其实,我非常害怕见到藏羚羊。因为在那些枪声夜起的风里,藏羚羊对人影早已有了防备,而我的闯入或多或少对藏羚羊都是一种不可拒绝的惶恐。
我刚蹲下身,一个声音从高高的石堆里冒出来——“阿啧啦,阿啧啦(惊讶)。”
我看见一个美丽的藏族少女,她望着我,满是惶恐的脸上堆着仇恨。
我连忙问:小波姆(姑娘)啦,你在做什么?
她回答:我的藏羚羊,我的藏羚羊在流血呵!她把怀里抱着的一只幼小的藏羚羊给我看。我抚摸着那可怜的藏羚羊,它的眼睛在风中一眨一眨的,浑身都在抖动。但我丝毫没有发现藏羚羊那流血的伤口。虽然我听懂了少女说的汉语,但我想她一定还有一些表达不当的词,让我不明白她的意思。
没想到她见我不语,伸手扯住我的衣裳大声吼:血,血,血你有吗?她捂住自己的胸口,突然跪在了我面前。
我嘘了一口气。这的确让我很惊讶,“血”,难道她指的不是藏羚羊在流血?可能她是说她的心在流血,可可西里在流血。
她坚硬的发丝被风吹得很弯,她耳边的九条小辫子已被风解散,她的声音在风中挣扎,风不可能将她吹倒,她的眼睛是高原天空纯粹的宝石,她在向我苦苦祈求:你别再伤害羊了,好吗?
看着她绝望的表情,我久久无言。耳边的风小口小口地吞噬着我想要说的话。沉寂的片刻,仿佛可可西里的心都停止了跳动……
我抱起脚下那只断腿的藏羚羊,踩着风的翅膀,越过可可西里那美丽的青山。
背后仍有风吹来,吹来诉说着藏羚羊和那美丽少女的哭泣声。
风过可可西里,风比草原寂寞——
我看到生命如此苍凉。
乘风而去的藏羚羊呵,你可听见一位持枪者的呐喊!
第三部分:青春枕着西藏入眠少年的诗恋 1
少年的诗恋
我在西藏捉摸青春的时候,青春已死亡。我在平原上仰望西藏的时候,青春却死灰复燃。
——题记
正好青春年少的时候,为了诗还真差点与小M结伴走进那所培养诗人、作家的有名学府。然而,只怪当时的我,一心不在写诗上,成天是我想唱歌我就唱。毫无诗意的现实就在我渴望诗意的年轮深处折断了我的翅膀,那时我只会单纯地笑,简单地哭。
现在,我如同一个没有梦想的人,每天站在造化弄人的现实里,看着时光如轮胎在灰色的水泥路上,刹出一条条如铅的斑痕,然后我只听见一颗灵魂发出阵阵悠长的叹息,我看见了岁月如飞刀,一刀一刀地剥落了青春。规矩的工作,身边凌乱的人和事,已不容我真诚地写下内心最飘逸的句子。我想流泪,唯恐城市的霓虹灯看见我流不出一滴泪。我试图通过这些飞不起来的文字找回我青春时候哭过的泪痕。我把左手交给右手,时光就在我眼前断裂开来。我看见我仍在对理想生活展开翅膀尽情地飞翔,飞了很远。我又看见自己淹没在我背后的人群之中……
当岁月就这样轮到我回望青春年华的时候,我才发现没有可乐、没有CD、没有麦当劳、没有情书、没有电影,甚至没有诗意的青春是多么多么的残酷呵。
我在西藏捉摸青春的时候,青春已死亡。我在平原上仰望西藏的时候,青春却死灰复燃。我坐在成都盐市口对面的派派思喝着红茶,望着玻璃窗下移动的人群写下这个句子的时候,和我失去多年联系的小M突然给我发来了短信。她让我马上进入互联网,看白先勇先生发在《联合早报》上的小说《Danny Boy》,我看了Danny的青春真不是滋味,我感觉城市的空气忽然在软绵绵的阳光里摇晃起来,那颗垂危的小生命在时光的洪流中接受命运无情的劈波斩浪,最后送走他的却是一个老人跪下来为他祈祷的《圣母颂》。
那忧郁的世界,那遍地开花的死亡呵。
诗意的青春又是怎样的青春呢?诗能养活一个七尺男儿吗?这是小M十五年后从马来西亚回到故乡探亲时问过我的话。我一直没有回答她。在我看来,她已走出了我的世界,因为我一直活在诗的世界里,就像彼得·潘,可以永远不长大。而小M已经彻底长大,像天上长出的云朵,裸露地白在人间。
我想她终于落入了烟火之中。
我想我仰望的西藏天天天蓝。
这样想着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诗。最初写诗,真正地写诗,始于新兵连的季节。具体地说,应是我穿上草绿的军装持枪走进青藏高原的第一个冬天。那阵子,只为突然远离了朝暮相处的故乡而写诗,感觉写诗就像在与亲人和朋友窃窃私语;以为将一些生硬的文字集拢或散去就是青春不败的姿势;甚至还坚持写诗来抗拒蓝高原上无边寂寞的袭扰。
我不知自己为什么爱诗胜过爱这身军装。
应该说,军营是座桥梁。虽然我载着兵的翅膀,但我仍可以在空中飞来飞去。一次次的飞翔,让我看懂了一些天上的风景,那些让我曾在地面上久久仰望的云朵,原来是蓝色的雪,我在空姐递给我擦汗的那张柔软的白纸巾上写下了:青春的云,蓝如雪。
我从拉萨飞到成都结识了不少像诗一样真诚的兄长,有地方的,也有军中的。我们一起把古典的现代的欧美的先锋的过时的诗句串起来当晚餐烧烤,我们拒绝用沸腾的火锅汤来煮我们的诗歌,我们只需要坐在街区的草坪上吃“冷淡杯”喝“528”,我不知读不懂诗的父亲是如何看待我写诗的。反正,在母亲眼里,写诗就是等着挨饿的表现。
不过,我还是在日常工作中把诗句擦拭得比枪杆子还亮。而今,我可以说我是诗人了吗?如果说,是,我顶多也只能算个缺德的诗人。能说名副其实吗?凭什么作证?凭那些加盖有“中国当代作家文化中心”或“中国协会”钢印的诗社聘书可以么?又如:仕江诗人,你的作品号《XZC3》已被输入微机系统,请收信后在15天内寄证书、工本费及邮资共38元,逾期不办。我又惊又喜:当诗人原来是要交钱的?我以诗人的名义和真诚,迅速将刚从邮局取出来的稿费飞一般寄往北京9799信箱57号。
两个月之后,一本《心之城——青春美文集》终于款款飞落我掌心,压模封面引人注目,但进入排行榜上的全是些陌生面孔,诸如四川的邓浩、广东的曾喜欢……他们都让我大惊失色。很快我就发现“他”不是湖南那个常写美文来吸引青春读者的邓皓;“他”也不是那个离开西藏去了北京还继续吃西藏故事饭的写手。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由唐之主编,印有纵横出版社字样。
我不认识唐之,也不知北京9799信箱57号里到底住着些什么样的人。也有可能全是诗(死)人,敲门才知空空如也。人在高原,对外界传来的信息首当其冲的反应仅仅是个猜想的过程。
在蓝高原上的小木屋里写诗,我没猜透,装运诗歌的脑袋如高原反应般剧烈地疼痛起来。我在那本《心之城——青春美文集》里找了半天,居然没有寻到凌仕江这个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的名字。
所以,我哭了,我看到成批的像我一样年纪轻轻的孩子都“诗”(死)在那条通往想象的独木桥上,我看到曾经流着红色的血,染红大海山川、染痛过人们眼睛的大诗人,我看到他们手中紧握的大笔都锈蚀了。我哭了,也不只是哭了,我哭:时代没有让我成为书写时代的诗人。
感谢那些坐在笼子里,纺织千丝万缕的青春网来捕获诗人的人。他们渴望一网打尽,他们不是人,但他们却有批准你是诗人或不是诗人的权利。或者,感谢他们本身就是用心良苦的“诗人”。
当懵懂的青春不再懵懂的时候,我撕毁了一张张不约而至的诱导之网。
第三部分:青春枕着西藏入眠少年的诗恋 2
但事情还是来得偶然了些。1998年的冬天,在风雪弥漫的青藏高原上,我把手中的枪交给了另一位稚气未脱的小战士。我说:“你帮我站一班岗,我的诗瘾来了。”我提起笔,在蓝高原上的小木屋里写诗,故乡的山坡却传来阵阵诵诗声;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并不忧伤地抚摸着我内心的蓝高原,诗潮澎湃。他们品着我的太阳雪,结伴而行前来踏访我驻防的太阳城——拉萨。
九九之冬,十月的天空,波澜壮阔的雪在我紧握的枪管里熟睡了;站在冰天雪地的屋脊上,眼睛紧紧咬住雪原的背影,忽然想起一位与雪有着特殊感情的伟人,一如去年今日,我不由想起《想起诗人毛泽东》。去年的今日,在蓝高原上的小木屋里写下《想起诗人毛泽东》的时候,我根本不会想到中国诗歌学会、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书法报社要联合为一首小诗颁奖。当我从《中国青年报》上获悉全国的获奖作品名单时,才将“不信”准确无误地替代了“信!”“信!”在此之前,我只记得有战友常常主动跑邮局帮我寄稿子。
我又惊又喜:原来当诗人还可以收到奖金的。
小M给我来电,说她去了日本,不过她说她对樱花一点都不感兴趣,她此时就站在富士山面前。
这句话反倒让我想起家乡房门前生长得很淳朴的那种花来。我记得它有个特殊的名字叫六月七,那些金色的花朵大都开在六七月之间。我现在想那种花多像我们曾经穿得单薄的衣裳呵。可我离开家门就再也没看到那种花了,现在想看,就像看不到的青春一样,朵朵笑逐颜开地散落在天涯。
相聚只会越来越少,重复导致越来越麻木。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回望自己的青春绝对不是少年老成,因为我仅仅是在一场青春的回忆中触摸人生隐去的闪光部分,至少我是缪斯纯净而虔诚且清贫的抒情者和守望者。虽然我不曾像其他诗人扛着流派或时髦的旗帜,在刊物上重复地流行或演出。后来我固执地认为曾经以热烈的情绪来铺垫诗句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写作诗歌本是不宜热的,它须同我们所身处的时代一样,冷静,冷静,再冷静。“冷”是指词语的骨(质)感,也可称之灵魂,“静”则是诗歌的纯洁,也可称之肉体或者声音。我不喜欢派不派的称呼,我的诗歌多数是在蓝高原上那间冰冻的小木屋中挣扎出来的。我挣扎过几年,只让一个小集子给自己的青春诗歌作了总结,取名《唱兵歌的鸟》,听说我的士兵兄弟和将军朋友至今还记得“自从把你当作一生的偶像/我就忽略了/哪天是生/哪天是死”这属于《军人》的句子。
我现在不怎么写诗了,但我把那些零零散散的落在他乡城市的一块块丑石;和一朵朵喊着我名字原路飘回的雪花,当作陪伴我青春的心灵后花园里的小摆设,我视生命对待生命,视朋友珍爱她们!
她们如今成了我散文的主角。
冰天雪地九月的苍穹河流
我和一发子弹躺在逶迤的高原怀里
黄昏一个深厚铿锵的声音
响起在战争远逝的岁月
我站在每一天太阳升起的地方
接过诗人珍贵的精神食粮
从杨家岭的早晨到《沁园春·雪》
我熟悉的背影在历史中定格
平仄的诗绪让一个世界
在雪里飞落
其实,有时我也想,在青春的雪地上同诗一样活着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士兵之心能抵达冰雪之心吗?有人说:孩子现实点再现实点,你就可以过得安逸一些。
诗到底为谁而活?至今仍未找出一个准确且又有效的答案。诗,已到了无法再写的地步。于是,在子夜降临,我就休笔入睡。往往到了这种时刻,我就会因饥渴所困,手脚僵冻而支撑不住。 毕竟我只是一名心甘情愿爱上缪斯的小小士兵,蓝高原上的小木屋里不产暖气,也不产我老家那里的乡亲爱吃的小葱猪油面(这个命名只习惯于我叫。家乡人通常的待客语气是,来嘛来嘛!再吃一碗,跨过阳沟吃三碗)。只有那杯洋溢着诗情的夜阑茶,还有那支勉强自己点燃的希尔顿(我至今还没学会抽烟)陪伴我左右。
我深感写诗真是件实实在在的苦差事,我还没有撞到一个与我同样执著爱诗的女子。女子总比男子聪明、实惠。尽管她们中也有不少诗歌的革命者。比如我尽量不再提起的小M。可是她突然给我来电话了。开始我并不知道是她打来的电话,我的来电显示上第一次没有显示数字,而是两个让我胆小如鼠的汉字——秘密。她在电话里一开始就骂我,为什么从未听我说一句我喜欢她、我爱她之类的话?她特别纳闷。这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我无法把握她所在的地理位置?她还骂她自己,她说她是个不干净的女人,说我还是个纯洁的男孩,她告诉我,你慢慢地等吧,你要的像纯净水一样的女孩子会主动来与你合成的。
这是小M与她的老外分离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也是在她骂过我之后从朋友的语音信箱里知道的——她又做了华人老板的情人。
爱诗不如爱钱,谁说钱又不如诗呢?就连我也不这么说了。但我离开蓝高原上的小木屋后依然想过诗歌的明天,我想诗歌的情景有点渺茫,我几乎不写诗了,到了2004年。我移情别恋地爱上了散文,我离南方以南的父母很远、很远……
最后,我还在想,是不是让岁月随随便便地将一页青春翻过,任纯洁的灵魂不再纯洁就可以融入大多数人的生活?可我没有做到。我就连这种看上去很容易很幸福很简单的生活也做不到,我到底能做到什么呢?
我问我自己。
你这个一手持枪,一手写诗的年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