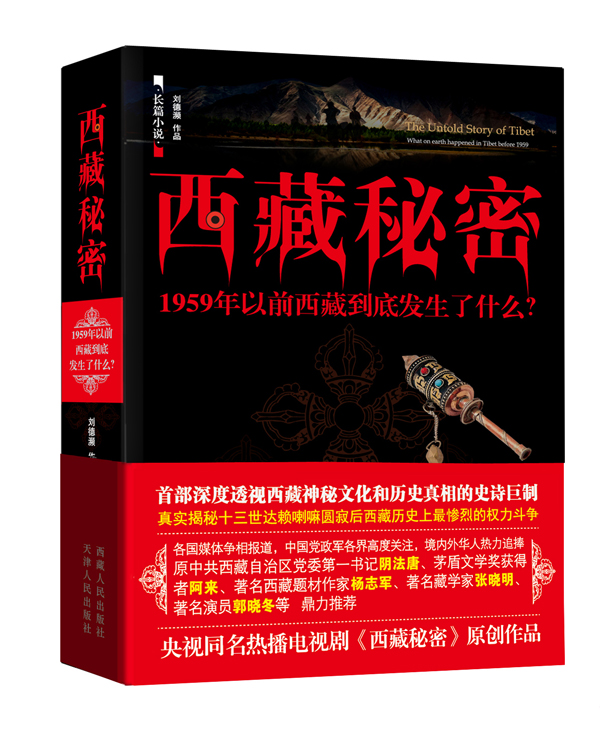飘过西藏上空的云朵-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掌声欢迎吉班长的到来。
掌声之后,吉老兵特意朝我笑了一下,这个笑,笑得非常隐蔽,也许除了我没有任何人看见。
从此我叫吉老兵叫吉班长。
我每次叫他吉班长的时候,他总是以笑来回应我,还是那种不带一丝声音的笑,好像他一笑就证明了与我是好兄弟。后来,渐渐地我也习惯了不喊他班长,有什么事先冲他笑一笑,然后把事情坦然说出来。这样就像从喉咙里取出了一团堵得难受的棉花,轻松自然。
吉老兵来到我们班后,我几乎失去了所有出公差的机会。这时我的身后已经添了两个新兵,其中一个新兵是另一个新兵的老兵,他俩常常形影不离,但我每次看见干活的还是那个衣服穿得崭新的兵,他的军装新得就像破土而出的嫩芽。看着他们可爱的样子,我常常想起我刚到这个边防连队时的那些捉摸不定的心情。
我从未想过我的兵之旅会从这个遥远的边防连队开始,我从来以为我就比别人幸运,我一直想进入城市中的军营,比如拉萨,比如离这个边防连队只有十公里的边镇。可两年过去我和大家还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一起投弹,一起长跑,一起吃饭,一起在午后灼热的阳光下,扛着十五公斤重的红缨导弹,忍着满目汗珠子,追踪两颗在空中移来移去的红弹和绿弹。想着这些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像原野的雪包围了连队——茫茫又茫然。我在黑夜里站岗时问天上的寒星,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我拒绝三年之后原路返回,我总是在想,我何时才能离开这寂寞的边防呵。
吉老兵有事无事拍拍我的肩:仕江,打起精神来。一个人在部队的时间其实是很短暂的,你们的班长已超期服役两年了,如果今年再提不成,还不是只有走的份,我今年也该打道回府了。你还是抓紧这短暂的时间去火炉边看看你的书吧!
我看书,看什么书?看来看去还不是那几本破书,不是《西藏简史》,就是《格萨尔王传》,上面的内容简直让我厌倦不堪。
吉老兵默然地立在阳光下,望着我久久说不出一句话。
老兵退伍后的一天早上,连队突然紧急集合。指导员拿着花名册点名,宣布强鹏接替吉老兵工作——喂猪种菜去,同时宣布:八班的凌仕江,到连部当文书。当时,我和强鹏对视了一眼。队列还没解散,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我和强鹏身上。我用眼睛的余光看了强鹏一眼,感觉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心情一定不好过。
回到班上,吉老兵帮我打理生活用具的时候,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嘿嘿笑了一声。我第一次听到吉老兵的笑声,我的思绪久久定格在那么多的笑声里(其实只有吉老兵在笑)一时回不过神来,想不通在这边防连队里,人,怎么可以长时间失去笑声?究竟是什么偷走了那么多欢快的笑声?
住在连部的第一个晚上,我兴奋得无法入睡。从床上翻腾起来,到排长那里买了一包方便面送给通信员,目的是让他多给我几枝蜡烛。我用刀片裁下几张薄薄的白纸,伏在烛光下,涂了几张中国画贴在会议室的墙上,然后站在对面的墙角看墙上的画,眼前突然跳出一个成语——蓬荜生辉。我又看见了那台沉睡在尘埃里的电视机,它孤独的样子像文物陈列在古迹斑驳的博物馆,它的孤独你不懂。
白天,躲在冷冷的值班室从窗外看出去,依然能看见他们在树下“升级”或“拱猪”,只是树的另一侧多了几个新兵举着傻瓜相机在那里东拍西拍。有一天,他们拍到了我的窗前。
“老兵,让我进会议室和墙上的画合张影好吗?”
“当然可以。”
“老兵你真好!”
“老兵,这拐弯的秋天河流是你画的吗?在这样的画下留张影真的很有意思呵。”
“记住,这就是我们山脚下美丽的尼洋河。”
新兵们一个个争着要与“尼洋河”合影。想不到透过窗子看见墙上几幅粗制滥造的中国画也值得他们如此兴高采烈地合影留念。他们真的是不甘被这枯燥的边防生活打败呵。
第三部分:青春枕着西藏入眠感念西藏边防 5
山东班长休假回来的头一天晚上,我们连队发生了一件事。
强鹏被关进了旅禁闭室。得知这个消息,连队许多战友的脸上都笑嘻嘻的,我像是看见了冬夜里的一场雪。指导员铁青着脸,气呼呼地让我换上便装同他一起去边镇,取人。
这是我当兵两年多来首次上边镇,也是我穿上军装七百多个日夜后,首次穿上便装。便装是指导员从他的床头柜里找出来的,上衣是一件白毛衣,裤子是一条灰色的灯笼裤。我穿上这一身后,指导员咧着嘴朝我笑了。战友们看见我,跟不认识的人一样。两小时到达边镇后,我们直接去了旅禁闭室,我听见那森严的石头房子里不断传出哭喊声和尖叫声。指导员让我站在门口等着。几分钟后,强鹏跟着指导员从石头房子里耷拉着脑袋走了过来。
我说:强鹏怎么啦?这么远的山路,你是怎么到边镇上来的呢?
强鹏做了个鬼脸,歪了歪嘴,新起个砣砣,连看我一眼的动作也免了。
指导员黑着脸,说,今年的先进连队肯定没搞了,回去我再跟你小子算账,你强鹏,兵当老了,牛B得很呀,居然敢在夜里偷跑边镇了。
破旧不堪的吉普车载着指导员、强鹏和我向着连队方向拐去。透过车窗,我想看看边镇有多大,可车速太快,我只看见路边几间木板组成的店铺,里面挤满了穿着臃肿的边民。刚到边防连队的时候,我天天夜里把边镇的灯火想成故乡繁华的城市。其实每一个初来边防连队的新战士都有过夜里遥想边镇的记忆。特别是从城市里入伍的强鹏,几回回夜里把边镇想成辉煌的北京。
这是回到连队之后强鹏头顶水碗面对墙壁站着军姿告诉我的。
指导员让我守着强鹏站军姿,一个小时军姿后,再让他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写出来。一番吩咐后,指导员就到刚休假回来的山东班长那里去了。
我守着强鹏,指导员走出门后,强鹏头顶的碗咣当一声落在地上,碎了。水,从他的脖子里落了一身。我愣了!强鹏笑了。
“老子当兵三个月就去过边镇了。”
“就你小子牛,怎么去的呢?”
“包地方老板的车呵。”
“你小子钱多。”
“嘿嘿,老子还要去。”
“先把事情的经过写出来再说。这是指导员的指令。”
“我不写你又能怎样,我只是去边镇上给我女朋友打了个电话,反正老子又没杀人放火,有什么好写的。”强鹏话完,一转身就走。
指导员匆忙走进屋来,正好与强鹏撞了个满怀。“强鹏,你给我站好!”
强鹏忧郁的眼神对视着指导员那冒火的眼睛,身子摇晃不定,哑口无言。
我对强鹏说:“你还是趁早把事情的经过交代出来吧,指导员会帮你解决困难的。”
“我交代个球。”
指导员一脚朝强鹏弯曲的腿上踢了过去:“站直了别趴下!跟老子牛B哄哄的,谁不知你有个漂亮的女朋友,这就是你炫耀的资本吗?有脾气把导弹射击考核跟老子拿个第一回来,训练场上你拉稀摆带。”
强鹏伏在桌子上半天也没把事情写清楚。指导员接过他写的事情经过瞟了两眼就一把撕烂,扔在了空中。“新起个砣砣,平时牛B哄哄的,几个简单的字也会写错,你还有什么牛B的嘛。”
强鹏的头死死地朝地上低着。
见此情景,我走出屋来到曾经待过的班上。连队来了好多战友围在山东班长的周围。我看见山东班长的眼睛红肿红肿的,像毒蜂蜇过的。他在战友们的问询中不时抽泣着——
“我下了火车没有直接回家,直奔那家人去了。门,反锁得死死的,三米多高的围墙,我一个前扑直飞进去。遇到他家的人,不管是谁,我一拳就打倒在地……”
在场的人听得不动声色,可山东班长越说越激动,捏起拳头就朝窗户打去,玻璃哗啦一声,碎了,像大头鞋踢碎冰块的声音。
吉老兵把我拉出门,在耳边说了句悄悄话:“你知道吗,他那个公安局的哥哥被人杀了?”
又一天,起床号刚响,连队突然响起急促的哨声,我从床上爬起来,提着裤子飞快地跑到操场。指导员首先是全连点名,然后喊强鹏出列。强鹏拿着手稿向大家宣读了他的“检讨书”:“……我不应该私自跑到边镇上打电话,我承认我错了,下次不再犯……”
事隔四天,强鹏一阵风似的跑来向指导员报告:猪圈里的大猪小猪统统死了。
一周后,连队支委会决定给予强鹏严重警告一次,关禁闭六天。死一头猪,关一天。
不久,连队飘来一封信。指导员说,信是一位市长夫人写的。信中提到一位名叫强鹏的边防军人,在电话里威胁她和她的女儿,说只要你再来信提出分手,我就回来夺了你全家的命。我们接到电话后,一直过着不安的生活。希望部队对此人的思想高度重视,给予必要的教育。
这封信是我离开边防连队的前一天飞到连队的,过了些日子我便坐在边镇里的旅机关大院将强鹏这个人直截了当地搬进我的小说。他当然很牛B,是小说里的锋线人物呢。
关于强鹏这个人,如果你想知道他更多的故事,可以借助于小说。在我的小说刚刚变成铅字的时候,听说我的山东班长终于提干走了。我不知他当了干部后是否还会对我有成见。
不过,后来吉老兵向我透露的消息让我十分意外:山东班长对我的成见其实不算成见,只因为我那时太受人喜欢了。
听到此话,我早已在远离西藏的内陆城市原谅了西藏边防上的一切,包括我自己的过去。
第三部分:青春枕着西藏入眠感念西藏边防 6
西藏的边防线是遥远而漫长的,但那只是我从军以来待过的第一个边防连队,也是我军旅生涯中的最后一个边防连队。就是这个曾经带给我无限寂寞的名不虚传的边防连队成了我青春旅程最开始的阶梯。我从这个阶梯出发走向边镇上的旅机关大院,又从那个边镇跋涉到三百多公里外的圣地拉萨。可没过几年,拉萨就成了我梦中回望的地方。我在平原上的一座喧嚣浮华的都市常常寂寞得把遥远的拉萨想念,想念我丢在边防连队的尼洋河、挂包、水壶、青春、照片、吉他、竹笛、大头鞋和格桑花,还有从野地里挖出来晒得干干的红景天。有时,我也会想想那些比我后到边防管我叫“六阿哥”的连队兄弟,想想别后数年他们去向何处?想想转眼就过了这么多时光他们是否已习惯沉默,是否会在某一天的某个地方突然想起我?就像此刻,我因为边防而想起他们,如此自然,如此刻骨,如此念念不忘……
回首在西藏边防连队的日子,不知不觉我就成了一个彻底沉默的人。本以为离开边防后,我会有快乐的心情说出许许多多快快乐乐的事情,可遇到那些没有边防生活经历的人我怎么也开不了口说出西藏的故事。也许只有提起笔的时候才会情不自禁地说出来,这种说话方式居然成了我生活多年的习惯。特别是在与西藏纠葛的情感文字里,我总是一发不可收拾地写教育感念,有时想早点就此打住却怎么也刹不住车,就像写作此文,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边防的寂寞成了我人生一笔难得的财富。纵然它曾带给我无边无际的孤独,可我要感谢那个寂寞让我如此充实的连队。是它的寂寞造就了我在今天这个只有花钱才能办事的时代还能静下心来抒发青春和梦想,是赶不走的寂寞让我选择了在寂寞中审判自己的人生价值并为之在沉默中崛起。我常常庆幸自己的豆蔻年华能在寂寞的西藏边防线上度过,我甚至设想我当时不是生活在边防连队而是生活在喧嚣浮华的都市里,也许永远没有机会体味什么是真正的寂寞,相反,或许会沾染上另一种空虚而让青春一晃而过。
但实际,融入都市的我真的就不寂寞了吗?我常常听到邻居的哭泣,我不让邻居听到我的哭泣,我想看看邻居的脸,可对面的门紧紧反锁着,这一锁就是几年。时光锁住了一颗心,我不能抵达一扇门。虽然距离只有几步,可这成了心与心之间无限的遥远。短短几年的都市生活气息已让我确切地体会到了人世间最无情的寂寞。它像一股强烈的冷空气不时地横扫你的心窗,提醒你关闭,要你提防意外受伤。现在想来,西藏边防连队的寂寞算不上寂寞,就算寂寞也是一种美丽,那是一种吆喝一声就能听到雪山回响的充实。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回到了拉萨。
这是我离开西藏几年之后第一次回到拉萨。刚下飞机,我在贡嘎机场碰到一个十分熟悉的人——他即将登上飞机。我们相互对视不下五分钟,最终我还是喊出了他的名字——吉老兵。他一回头,眼里泪花闪动。我手上的行李沉沉地掉落在地。这简直就像导演安排的一个特写镜头,但我分明相信这是命中注定的一次不谋之约,是一种时光集合了多年才创造的奇迹。与我们在边防连队时相比,吉老兵明显老多了,他黑红黑红的脸上布满了像藏族人一样深刻的皱纹,可吉老兵看我一阵,却说:依然年纪轻轻的。因为我们的偶然重逢,吉老兵特别央求机场工作人员给他换了下一个航班。对此我十分过意不去,但又有种说不出的兴奋劲。当我充满好奇地问起他为何还没离开西藏时,他只是淡淡地说:“边防需要我,我离不开连队。”他略有伤感地告诉我,过去那个边防连队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搬进了新的营房;他又到了种菜班;那儿已经不吃咬不动的干菜罐头了;连队又来了一个喜欢写诗的兵,昨天刚满十九岁,长得特别像我,但眼睛没有我忧伤。
我突然想起一张脸,一张流满泪水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