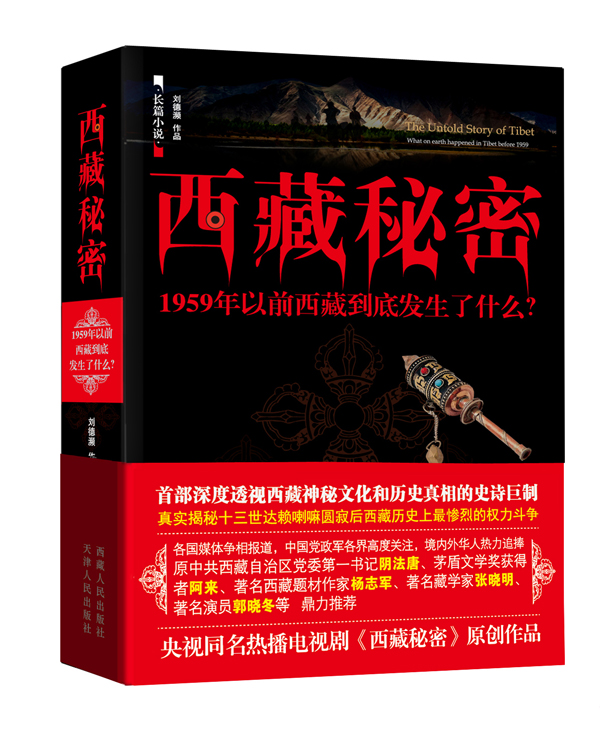飘过西藏上空的云朵-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码砖”,照样赚钱。的确,她早就把包产地全丢了,几年工夫,她成了全村有名的女赌神。许多从外面回来的大、小老板,都要找她切磋。一天,我亲眼看见她赢了五百元整。她真走运,摆着架子点燃香烟,吞云吐雾……不一会,店主叫她接电话。她站起身子朝我说:凉峰坳的操哥(有点钱、讲究穿着的年轻男人)找我到那边焖鸡咧。果然,一个骑摩托的伙子忽地出现在眼前,她利落地跨上后座,神态风光地向我招招手,一溜烟便消失了……
还有一次,我在这个山口听人唱卡拉OK。到头来也没听懂他们唱了些啥。有一点可以肯定,乡下的空气比起城里实在是鲜活得多,但我仍感觉有种说不出的沉闷。在我的乡下,年轻人都很热爱唱歌,特别爱唱迟志强的那首《铁窗泪》。我看见三个男子为同唱这首歌将一只麦克风扭成一团。先抢到麦克风的人张开嘴就吼“月儿弯弯照我心,我在狱中想伊人”,他不认识歌词中“伊”字,唱成了“女”人,像是在呼喊离他而去的爱人名字,心中不免悔恨难当。再后来,他们争着要唱《杜十娘》和《追求》。有个快乐的单身汉拿着麦克风,甩甩头,走起太空步,故意制造些矫情的哭腔,结果鬼哭狼嚎,那嗓音,就像干得没有一丝水分的青城山的老腊肉。即便这样,从没出过远门的大老爷们还夸他唱得好,说什么声音越大唱得就越好。于是,唱歌的人还自诩道:我在广州大型露天卡拉OK唱得更风火,好多靓女给老子递鲜花咧。
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子嚷着要唱《祈祷》。但她给店老板说的并不是“祈祷”两个字,而是把它说成“斤寿”。店老板翻遍碟库也没找到她要唱的“斤寿”。我在一旁忍不住笑出声来。你想想看,“祈祷”从她嘴里变成“斤寿”,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么?再说中国内地歌手又有哪一位唱过《斤寿》这首通俗歌曲?她扫兴地叹了一声,对着我说:在海南的时候,我唱得最好的就是斤寿这首歌,每次唱完都有人鼓掌。她换了一首歌,音响刚开始,她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屏幕,屏幕上的字跑得飞快,她踩不准调子,嗓子坚硬得没有女人应有的柔软性,更不懂得怎样在关键的地方处理高难度的抒情音调,只会尽全力地干吼,好像只要吼上去就有人夸。
诗人们常说;诗在诗外。在我看来,这个一天学堂也没进过的女人其功夫全在歌之外了。这是不是乡下女孩目光短浅的表现呢?不过谁也管不着,包括她的父母。也许这是她自我表现的最好机会吧。她后来唱了些什么,我记不起了。反正我听累了,夕阳也羞得蒙上了脸。
天刚黑,我得回家。刚走几步,店铺前一阵闹哄哄。我回头一看,原来有人对骂起来。仔细一看,那个“女赌神”嘴张得大大的;揪着一个三十上下的男人吼着:我日你娘!快把那二十块钱给老子!
三
下午,阳光暖融融。
一个头裹白帕子的老者坐在自家门外,膝上坐着一个穿开裆裤的小男娃。老者愁眉不展地夹着一枝劣质香烟,一边替小男孩抓虱子,一边数落:文武呀,你吃穿老子好几年,你爸妈在广州不寄一分钱回来,你狗日的长大了千万不要没良心哟。小男娃若有所思地抓抓脑袋问道:爷爷,等我长大了给你买好多好多叮叮糖,好吗?老者闷闷不乐地说:你狗日的小小年纪就会学卖乖,等你买叮叮糖,老子恐怕早就入土喽。小男娃皱皱眉,晶莹的泪花哗地淌落:爷爷不要,爷爷不会死,我不能没有爷爷;长大了,我一定给你买叮叮糖,一定呵。老者爱抚小男孩的头,脸上好不容易挤出一丝笑容。此时,堂屋里的黑白电视机里正唱着:“郎君呵;你是不是饿得慌,如果你饿得慌,对我十娘讲……”突然,屋里走出来一个纳着鞋底的妇人对着电视破口大骂:你儿才饿得慌,狗日的出去几年,一分钱不寄,还甩个包袱给老娘。说着,她啪地关掉电视机,牵着小男娃的手就向菜畦走去。
还有一个起风的傍晚,吃过晚饭,我依然郁闷地在一条小巷子里踱步。此时,没有一个夜归人,村人为了节约电,都已早早入睡。但有一家人的灯还亮着。我走到窗前,虽然看不见脸,但却能看见窗内的影子在说话。
她娘,快洗脚睡吧?男的把桶提到女的面前后就将衣服放在床头,慢慢躺了下去:哎,身子骨酸疼得很啦。
女的一边洗脚一边怨叹:嗯,日子过得真快呀,俺椿树嫁到他张家已快二十年了,从没做过丢人的事吧,妈妈的没良心,狗日的是不是想再坐一回牢哟,去广州有了钱就变坏,又找一个女人谈恋爱,生了孩子人家找他要房子,她爹,你说咋整?
你看看,你看看,又来了,他总不敢把老子的女儿整死,整死了他也没有好日子过,老子早晚要送他进班房,只要他断了老子每年的八百块钱。
女的说:谁要他的臭钱,还是先把他告倒再说,否则在广州还和椿树天天闹离。
再闹老子就去广州接回来。
男的说得斩钉截铁。曾经当过村支书的他,怎么也没想到,如今这世道说变就变,因为有了钱,一切都可以再变,况且,城市的流行病无孔不入,早已悄然地蔓延到了乡下,该染的都被染了,还有少数的隐蔽在竹林掩映的小院里。
第二部分:梦里故乡飞花丝雨在我的乡下 4
活并痛着!
张家大院里有一位驼背的老婆婆。打我记事起,她便孤独地和儿子过着艰涩的生活。据说,她的男人是土改期间被活活饿死的。后来,大女儿嫁给了队长,幺女让村支书的儿子捡了便宜,十五岁就生了孩子。
在我的乡下,孩子总是孤独的。那天,这个孤独的孩子拽着几本书像根草似的歪在车站一眼就认出了我:凌六爷,好久回来的?回来好几天了,好久不见你今年多大了?十四岁了,读初二。打多少分?英语经常不及格,其余都在八十多分。他回答我的话,我却在想着他小时候的可爱模样,但我怎么也不敢相信,瘦骨骨的他就是那个曾经人见人爱的胖娃娃。我问:爸爸呢?他支支吾吾地说:自从妈妈和他离婚后,他就到广州打工去了。你不想他吗?他去年过年回来耍了十五天,得了梅毒,我们乡下打针很不方便,他就急着回广州了。我问:你外婆现在跟谁过呢?跟谁过?舅舅去外地打工,几年也没音讯,水都没人挑给她喝,死了……
我想,孩子你是不是太可怜了,这大冬天的,谁来为你单薄的身子御寒?孩子你不仅缺钙而且缺爱呀,你是祖国的花朵,可你为什么还要背负这么多期望和痛苦呀?
我想再问点什么,他跳上三轮车走了。
我的乡下啊
究竟是谁在欺骗谁
究竟是谁在为谁伤悲
四
不知什么时候,乡下就只剩下这些走近我笔端的老人和小孩了。这是社会飞速发展中我来不及想的。面对这样的选题,我曾怀疑过自己的思想。但事实就是这样,在我的乡下我触目所及之处只有老人和小孩。母亲还告诉我,虎榜山下有个老头子死了,找不到小伙子抬死人上山。而我感到尴尬的却是狼来了,老人和小孩已无还手之力。我还亲眼目睹过从广州打工回来的一对青年夫妇,他们的小孩几年不见已不敢认爸爸妈妈了。女的手里捏着一块巧克力,男的手里抱着一个大玩具,可孩子不但没有走近他们,反而一阵哭嚎,跑得远远的。尽管这对夫妇找了很多钱,但买不到儿子的一声叫唤,内心深处或多或少有些悲哀。
回家过年显然萧条和冷清了许多。极少有人在这几天不远千里而来,与亲人朋友推杯换盏喜相逢。多数远走他乡的村人都在外过年,照他们的话说是花几百块车费回家,不如去超市购物,这样实在是爽得可以。
其实真正回来了的又急着冲出门去。于是大年初二就提着大包小包的各奔东西。春去春回来,乡下过年就只剩下个朴拙的形式了。我好不容易从西藏军营回来探望父母逢上过年,心里别有一种滋味——
谁的心晾在外面忘了收
我的乡下
谁的眼泪在飞
我的乡下
谁的教鞭停止了歌唱
我的乡下
现在让我想想,这些年出门在外的都有谁还在坚持回乡。乡下究竟还有多大诱惑?好像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当兵的了吧;好像只有我和他还挂念乡下。
数年前,我还是个光着脚丫常常行走在田野里捉泥鳅的大男孩。而前面提到另一个当兵的则比我年龄要大些,但他却过早地放下书本当了一名挑灰桶的小工。我远征西藏的第二年,他弄到一张初中毕业证照样参了军。多年后我们都留在部队,过着制式化的生活。据说,他一直在帮首长开车,而我在机关执笔文书。我们不愁吃穿也不为生活茫然随波逐流,而且每年还可享受正常探亲,少则五十天,多则八十天。岁月常安排我们在同一时间从两个极端的方向往一个叫乡下的地方赶。我们虽然相逢,但却少有交流。
有一次他全副武装的出现在村口向我打招呼:好久不见,你这些年都去哪儿了?我如实答道:还在西藏。他说:真好。我说:好。没几天,我们又在车来车往的站台相见,我很想再问你好,但他却躲进车,鬼撵似的消失了。我想,也许是我们回乡的举动各异吧。他喜欢穿军装,挨家挨户串门,小孩子见了都相互转告:公安局的来了,还不赶快跑。那些小孩子的妈妈见我就说:那个人回来老戴公安局的大盘帽,怪吓人的。她们还问我:你也在部队怎么从没见你穿一套回来呢?我无言。许多人都这样将同一问题把我问得哑口无言。有时,我放慢脚步,也想说几句,但却不知从何说起,这样我与村人的交流被迫少了许多。其实打个招呼,说一句你好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见了他们就不知说啥好了。有时,顶多递一个微笑就走过去了,如果缘分再让我们相见,大家点点头就行了,甚至微笑也可以省去。所以我想军装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场合并没有农民着装自如,随意,亲切……也许村人更愿意关心庄稼,毕竟他们的命运和土地息息相关。
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里,军装只不过是一种颜色罢了,不值得在我的乡下如此高高在上。这在村里人的眼睛里早已有过说明。
还有一个人,我还能想起一个五年来未曾谋面的同龄人。他是二十世纪典型的用钱堆出来的大学生。他们家其实早就出过另一位大学生,就是因为那位大学生才有了他这个大学生的诞生。贫寒的家为了这两个大学生耗尽了两位老人所有的心血,最后没办法只有拆房子卖梁。第一个大学生参加工作后的所得工资全部堆在了第二个大学生身上。他终于毕业参加了工作。第一个月拿了一百八十块钱的工资,他哭了,心想这么低的工资何时才能还清上大学时欠下的债啊,于是一气之下去了广州,而且一去不返。如今在一座新城拼命回收着上大学花出去的钱。五年过去,他把包里塞得鼓鼓的,第一个大学生却不幸下岗了。他在与我通信中说,生死也不回那个乡下了。他还告诉我作为出生在先辈大教育家吴玉章先生故居的年轻人,出门在外就意味着出息,如果常回家看看则意味着倒退。诚然吴老先生的乡下实在是太穷了,但听说吴先生在中国教育事业上作出了很大贡献,家乡人民敬仰他,特别在自(贡)荣(县)路途经的双石镇口为此立碑塑像,并请来吴老的弟子杨尚昆为此题词——“吴玉章故居”。
第二部分:梦里故乡飞花丝雨在我的乡下 5
有一天,我路过“吴玉章故居”,看见吴先生仍正气浩然地观望着自己的故乡。尘埃染遍了他伟岸的身躯,潮湿的气候模糊了他年轻时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目及之处,都是些破烂不堪的小街和教室。教室里许多静静观望着空白黑板的小脑袋们不知吴老先生何许人也,这难道不是故土的一种羞辱吗?他们只知道自己的老师被拖欠了半年工资不来给他们上课了。
我回乡也遇见过自己的老师,他过去教我们写方程式,现在改行叫我们掏钱坐他的两轮车。
五
尽管这样,作为一个从麦田中走出来的少年,我还是把乡下当作了灵魂栖息的牧场,我还是把每年坚持回乡看作一种使命,我还是有一种感觉,觉得学会回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我早预料到,公路两旁的村庄迟早会像孤零零的坟墓,田野上丛生的杂草迟早会像麦芒一样刺痛我的双眼,父辈们悉心经营的田园会像我记忆对应的风景,但我也清楚地知道乡土好比父母,不热爱故乡的人,走得再远不也是一种狭隘吗?在世界屋脊的屋檐下,我不止一次地产生过许多失败的悔悟。比如我为什么要一个劲地闹着出来?为什么又要编织惊奇的谎言闹着回去?回去了看见空荡荡的村落又控制不住地一路奔走?有时,去也是为了回,但回却并不一定都是为了去。有时,远离故乡越远心儿就越软弱。但往往刚刚踏上回乡路,看见这块和那块被城市文明遗弃的土地,心情就像是在逃,但软弱之人从来都不会抹杀回乡的念头,只要出现一线希望心儿就想飞。
有一年,我三次从军号穿过的西藏飞回乡下,其中两次出差原路返回,还有一次则是庄严地向上级报告——我要回乡。可没等几天上级却以工作繁忙为由不准回乡,回绝了我的报告。我便去找领导诉苦:我的乡下正遭遇着百年不遇的大旱,我的父母亲几天没喝一口水了,我的心儿都快急死了,我的……别我我我的了,你们的都是我的,军人的故乡有难嘛,哪个兄弟不急呢,梦里都在急呀,你不回乡,我不回乡,谁去关心咱爹咱妈。慢慢地,很是通情达理的领导说着,很潇洒也很郑重地在我的报告上签了字——速去速回。
记得我走进村口的时候,碰见正在编织毛衣的邻居张嫂,她说:哟,你又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