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22-央视女主播徐俐-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让我捡起来再交给他:″小俐,走两步,给伯伯拣起来″。这样的″游戏″每天都要玩好多回,我不记得我是不是烦过。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美丽心得六岁那年我瘸了(2)
治腿的时候住了多长时间院不记得了,反正严重的一瘸一拐的时间有大半年。我小时侯喜欢认字,五岁多就上了学,小学五年,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我换过四个学校,双百的成绩一直伴着我,如此看来,瘸腿并没有耽误我的学业。院长兑现了他的承诺,在一年之内治好了我的腿,我又成了文艺积极分子,为此我终生感激他。
但是,如果没有治好呢?如果不是在部队医院,主治医生不是院长,而院长又没在德国留过学呢?
我小时侯的照片很少,怎么找都只有极有限的几张,而且张张没有笑脸。有一张十来岁的时候和父母及姥姥的合影,因为非常瘦,眼睛显得很大,脸上有一种忧郁而落寞的表情,心事重重,一副不爱说话的样子。
带着瘸子的心理阴影,我上了中学。那时的中学一边上着文化课,一边还要学工学农,一学还好几个月。我念初中的时候十一岁,比同班同学平均小两岁,身高也差得远,刚一米三九。我确实看上去很小,是那种小精灵似的小。可以想象,妈妈不放心我的年小体弱,她跟老师说,徐俐曾经是个瘸子,不能干太重的体力活儿,也不能走太远的路,老师一定要多照顾。其实妈妈如果不说,除了身高矮点,我和其他同学没什么不同;要命的是她说了以后平时也不起什么作用,我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关键的时候就把我害惨了。
十四岁那年,部队来学校招小兵。我因为能歌善舞,表面上看去喜气洋洋,在学校也算个扎眼的人物。我记得招兵的叔叔见了我,见我一副伶俐相,非常喜欢,问这问那的。我开始憧憬穿上军装的样子。当时中学毕业以后,只有两条路,要么留城等待街道分配工作,要么上山下乡去农村。关于留城,一家只能留一个孩子,我哥哥已在他十三岁的时候考取了文工团,所以留给我的路只有一条:下乡。那时没谁愿意下乡,想的都是千方百计地不去。如果能当上兵,就是最好的前程,何况是小女兵,名称听起来都是娇滴滴的,到了部队该多神气呀!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班主任告诉招兵的叔叔:她妈妈说她曾经是个瘸子,招去了怕是不合适。老师没有恶意,她只是向部队负责。
剩下的事情就不用说了,我相信我妈妈的肠子都悔青了。为了补救,妈妈带我去医院做了一次检查,医生证明我的腿确实看不出什么功能障碍,但是,那又管什么用呢?
因为瘸腿,小朋友给我起过外号,叫我徐俐拜子,长沙话发音拜子就是瘸子的意思。这个外号叫的时间不长,但留在心里的时间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自己是个拜子,成年以后看见不会走路的拜子,都会无意多看他们几眼。记得后来上班,天天经过同一条路。一天有个男青年主动和我打招呼,说我长得周正,提出为我画幅素描。男青年说他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家就住在马路边,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尽管当时我很忙,但我还是答应了,因为他是个拜子。
现在我给所有人的印象是,乐观、自信、开朗,其实在这层明亮的基调下面,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性格里还有一层淡淡的、外人难以察觉的灰色,这层灰色和我的瘸腿以及由瘸腿造成的各种成长烦恼密切相关。没有人知道,瘸子的阴影伴随了我的整个青春成长期。学校有过一次拉练,大约走了六七十里,我没有听从老师的劝告,和大部队一起走了回来,那条腿就比另条腿疼的日子要久,但我一声不吭。学农要挑塘泥,满满的两簸箕塘泥甚至超过我的体重,我就小心翼翼地尽可能把重心放到另一条腿上,拼命坚持着,没有让任何同学看出我内心的谨慎和担心。事实上,在我快速发育的那一两年,我的这条腿是跟不上另一条腿的。有段时间我几乎天天比腿,怎么比,一条腿都比另一条腿略短一点。那种焦虑我不会跟别人说,完全独自承受了。淡淡的性格的灰色使我在二十岁以前趋于内敛,即使以后在某些人看来我自信到近于张扬,但那层内敛作为一种自我约束始终都存在于我的血液里。我因此很少不清醒,很少做出错误的判断,万一真的错了,也不会错到不可救药,总有挽回或补救的余地。
两条腿终于长齐是在我彻底停止发育以后,那种如释重负的感受简直无法对人明说。我曾经是个瘸子,格外在意自己行动的正常;我害怕重新再成为瘸子,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小心呵护。其实成年以后,当我穿着高跟鞋,昂首挺胸乃至气宇轩昂地走在人前的时候,瘸子的阴影早已不在,说出来都像是别人的故事。今天之所以提起它,是因为它曾经作为我生命的重要底色长时间地存在过,它困扰过我的成长,它在我的性格上打下了挥之不去的灰色烙印。其实,绝大多数人对我的性格是有误判的,曾有采访者惊讶:你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喜欢简爱呢?只有不美而自尊的女孩才会喜欢简爱呀!采访者的经验是,漂亮的女孩都喜欢郝思嘉。我不难看,但我不喜欢郝思嘉,我喜欢简爱。从十五岁到现在都是如此。
上面是两年前我写的一篇散文。文字里透着浓重的自我怜惜的味道。
从我一生都喜欢简爱这个角色来看,自尊是我为人的基本起始点,不管别人如何,我得拿自己当回事儿。
一个多病、瘦弱、忧郁的小女生是如何自信和美丽起来的呢?大约就是源于自尊。自尊,让自己一生都比较努力,因为努力,信心也就有了。这是后话。我想说的是,人们称道的徐俐的所谓美丽,都是在一个多病、瘦弱、忧郁甚至自卑的小女生的基础上生长而成的,这点可能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美丽心得宁可穿破,不可穿错
爱漂亮一定有遗传。
我小时候的衣服大多是妈妈做的,那年月的人们大都兴做衣服穿。我高兴的经历之一就是陪妈妈去商店买布。妈妈手巧,不是一般的巧,妈妈做的衣服经常比买的好看得多,所以我们家的孩子出去总比别家的孩子漂亮。
妈妈精心打扮自己的儿女,给我这个做女儿的留下的印象就是:女孩子应该永远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妈妈自己就是那年月的美女。她自己会做会收拾,她走出去也比别家的女人漂亮。妈妈的漂亮观念纯粹来自于她的直觉。比如,她不懂什么叫身体比例,不知道身长是七个半头长的说法,但她知道多长的衣服配多长的裤子才叫和谐。妈妈的直觉好极了。
改革开放以前,爱美就是封资修,所以大人小孩没有任何有关穿衣戴帽的知识启蒙,一切都是自己懵懂琢磨。
妈妈唯一的穿衣理论就是“宁可穿破,不可穿错”。这是梨园里角色穿衣的规矩,不知妈妈如何懂得把它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梨园行里,行头错了,角色就错了,自然错不得,此话在梨园行里就是最起码的穿衣规矩;到了现实生活中,若是再遵循这个理儿,简直就牛得一塌糊涂。
妈妈爱看戏,懂得戏里穿衣的道理,她的聪明在于她会触类旁通。她说我们小时候有身经典的打扮:她亲手编织的红毛衣毛裤,再配一条镶了荷叶边的白色围裙,头上扎着红绸子,像个小公主,人见人爱。
记得我在上中学时,有一身打扮始终是自己的最爱:在人们清一色的蓝色外衣里,我总配上一件洗得干净叠得整齐的白衬衫。外衣被妈妈做成收腰西服型的,白领子翻出来,加上我因为练过舞蹈而亭亭玉立的身姿,显得格外精神和清爽。
我们长大以后,如果妈妈发现我们穿得不顺眼,为了让我们把刺眼的换下来,她就会抬出那句八字箴言:宁可穿破,不可穿错。虽然什么才是不错,道理不甚明白,但概念已经有了,就是这辈子穿衣要讲究,要小心谨慎。
记得有次是为了穿裙子。妈妈做的裙子大都过膝长,妈妈认为我穿短裙不好看。她给我设计的经典裙装是:白衬衫配深蓝色华达呢的六片裙,衬衫收在裙子里,显出细细的腰身,而那六片裙长度过膝。每年的夏天,我基本都是那样穿的。妈妈也喜欢给我做纯白色的连衣裙,裙长也过膝一点,白裙配上我的长发,飘飘的。可能是穿长裙的次数多了,我想换条稍短些的穿,妈妈一看就急了:脱下来,不好看,长裙显得腿长,不要穿短的。记得那次我换的是条西服短裙。妈妈一生都坚持认为我不能穿短裙,后来,当我懂得比例协调关系之后,发现妈妈的坚持是对的。不是我绝对不能穿短裙,而是穿长裙长裤更加漂亮。我说过,妈妈的直觉特别好,在她眼里,我穿短裙就属于穿错了,无论如何要不得。
不仅是穿衣,对女儿家的言谈举止,妈妈也要求极为严格。妈妈说过“笑莫露齿,坐莫摇身”的话,那是她奶奶教给她的,后来她发现在我们身上行不通,就降低标准,要求我们行正坐直,举止不能有败相。比如我在学校练过几年舞蹈,而且还是芭蕾,学跳《红色娘子军》。功夫没太出息,舞者的八字步倒是学会走了,那八字步在妈妈眼里就是败相。坐着的时候,我无意识就把两腿分开着摆,那是练功开胯留下的后果,妈妈一看就不顺眼。她常在我完全无准备的时候,朝我的腿上使劲儿一拍“把腿并上!”生疼的同时还被吓了一跳。看妈妈的决心,我不改是不行的,因为我不可能不在她眼前走路。那时我已在电台上班,电台机房的地板是五十年代铺就的木地板,地板的拼缝当然是直的,我觉得顺着拼缝练习走路不错。于是每天,男声在里面录音,我在外面等候时,就顺着拼缝从屋子的这头走到那头,不知走多少遍。走了几年,居然把八字步改了。不仅改了外八字,妹妹说我走过了,好像有点内八字的意思。当然这也不可以,又往回调,终于调正了合适。
我身上的败相是被妈妈一点儿一点儿抠掉的。好像十来岁时,我上牙床的左边多长出了一颗虎牙,像巩俐在《红高粱》里那样,我自己觉得很好玩,但那绝对就是妈妈眼里的沙子。我不可能不在她眼前笑啊,没商量,拔了。我怕疼,总是一拖再拖,妈妈急了,话变得难听起来,从那时我就知道,什么叫姑奶奶急了。记得是我自己一人去的,妈妈认为这样的小事不需她陪着。我去的是省军区的门诊部,一个年轻的男医生在我的上牙龈打了点麻药,拿着一把不知叫什么的钳子,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我那颗虎牙除去。看医生的费劲,还是早去的好,岁数大了再去,拿的可能就不是那把钳子了。我一生就拔了那一次牙,记得最清楚的是拔完以后留下的牙洞,像插秧时漏掉的一个秧穴,很显眼。我觉得那秧穴很好玩,老用舌头舔。妈妈看着又碍眼,规定我不许舔牙洞,而是要不断地把被虎牙挤进去的正常牙齿,用舌头往外顶。我现在的一口整齐的牙齿,其实是妈妈帮着长好的,她使的劲儿比我自己大多了。
妈妈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告诉我什么是女儿家的败相。比如,我有个玩伴儿,说话时好先吸一口气,吸得很响,像刚吃了朝天椒。她如果要连说四五句,至少会被辣上两三回。她一辣,妈妈就什么事也做不下,只看着她,示意我注意听。玩伴儿走后,妈妈一定要再夸张点地把那辣声学上几遍,还说,如果在同人谈恋爱,别人会烦躁的。我正处于青春期,这样的告诫很管用。
那时候总有小伙子借各种理由来我家串门儿。有天来了个说话用糖嗓儿的,听得妈妈浑身不自在。糖嗓儿走了以后,妈妈说她恨不得拿筷子在糖嗓儿喉咙里通通,要不会憋出人命来。妈妈说话经常又形象又夸张。当然,糖嗓儿一类的人是断然不能考虑的。妈妈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才育出个没败相的女儿,怎么能轻易地交给糖嗓儿呢。糖嗓儿不知道,只顾天真着来。可怜。
因为妈妈的严格要求,我的举止做派里,怕是没有太多不顺眼的东西。走路挺挺的,虽然不是笑不露齿,但怎么笑也不至于难看。记得在长沙台的时候,有个同事刚养了女儿,他说要向我妈妈取经,如何才能把女儿养成我这个样子。他认为我的性格好,各方面看着也顺眼。我把他的要求向妈妈转述后,妈妈开心地一通朗笑,得意极了。
直到我出嫁,妈妈一直都是这样管教的,从手势表情,到身姿举止,一样不拉。可以这样说,我上电视以前,已经有了一副被妈妈细抠过的身架子,那是一个很好的基础,余下的事情全靠自己的造化了。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美丽心得我理解的职业装(1)
经常有同行问我,出镜的职业装都是如何配置的。其实我对职业装的全部判断和审美,都来自在西方电影和电视剧中看到的白领丽人的形象,以及透过小说对她们展开的合理想象。
西装本就来自西方,女式西装又脱胎于男式西装。作家乔治·桑在女人都穿雨伞式长裙的时候,刻意穿西服,被人视为女扮男装。女性西装的出现,是女性走向职场的需要。为了表达女性在职场干练称职的气质,女性的穿着似乎也在向男性看齐,女式西装其实就是男性西服的微小变异,那种中性化的气质符合办公室对女性的要求。所以,越是大白领,女性的着装越像男性——齐臀边长的上衣,宽松笔直的长裤,和男性西装差异很小。这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潜规则。为了同男性有区别,女性能做的文章就是西装内的衬衫或者内衣。那是一个可以做文章的地方,尽管场地不大,但内心春秋足以彰显。除此以外,各种首饰的搭配也是女性的性别权利,只要风格分寸得当,男性是不会怀疑女性的职场能力的。
这是我通过各种渠道形成的对职场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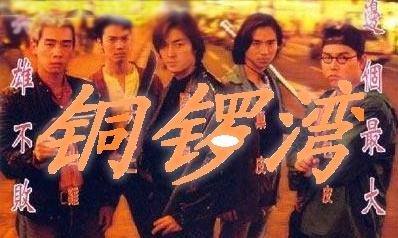
![埃提亚[更新至 第229章大地权杖胡戈第的黑暗阴影(下)]作者:上帝不在天堂.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