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22-央视女主播徐俐-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正明亮,为什么不看呢?
现在听起来如此简单不过,但那是在近二十年前。二十年前的观众确实少有选择,我们给了他们一个不一样的理由,他们就天天守着我们看了,所以我们就红了。
就我个人而言,红了的最大变化就是不管什么人都变得喜欢你了。曾经的邻居,他们的儿子喜欢我,他们觉得我没有继续考大学,所以儿子不能和我在一起。后来发现上了大学的儿子也不比我这没上大学的混得更好,父母再见我的时候,脸上竟多了许多的热情。多没意思的事。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职场风云在长沙台的日子(5)
能推的应酬全推了,能不露脸的地方尽量不露(我一定得罪过不少人),我的清醒是不管别人如何,我仍旧是我。我厌恶眼前的浮华热闹,我不是一个得意忘形的人,或许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至今都没有过一刻自己真正认同的得意。得意是需要本钱的,要大本钱。自认为本钱不够,所以得意不起。
说来奇怪,尽管在长沙电视台工作了六年,印象却是浅淡的,除了因露脸而红,再没有其他记忆更深刻的事。也许,我在业务上花力气最大的都是在电台时,有了电台的底子,在电视上露脸并受欢迎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我的搭档
我的搭档叫刘学稼,湖南电视台的编导,一生不着家,老在外面跑着,前几年在新疆拍片,遇上车祸,才过五十岁,永远漂在外面了。
刘学稼外号刘瞎子,高度近视,戴着厚厚的眼镜片。刘瞎子拍出的画面极美,我曾经对他说,画面美到那种程度,人就会产生剪了它的欲望。刘瞎子听了得意大笑。听说因为视力太差,他最初并不扛机器,后来发现与其与人合作不顺心,不如自己全打全包。所以,凡是刘学稼的片子,编导、摄像、撰稿都是他一个人。
刘学稼是个才子,举止洒脱,性格率真。他爱湘西,爱到了命里头,他的《湘西系列》专题片在全国电视圈里有过不小的影响,有舆论把他说成了“电视沈从文”。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拍湘西,拍了五六年,湘西是先长在他心里,再落在他的镜头里。他拍的湘西有种特别的灵性,是一种特别的湘西的味道,那种味道只有去过湘西的人才能真正懂。
刘学稼是为了给他的专题片配音才找到我的。
他起先听广播,听到有一个叫孙敏燕的女人声音很特别,那是一种他认为有可能的声音。可能有饱满的热情,可能有涉世的沧桑,可能有辽阔的气势,可能有似水的柔情,他需要这样的声音。
见到我的时候,刘学稼有些意外,他没想到我那样年轻。过于年轻而城市化,能读懂既荒蛮又壮丽,既敞亮又诡秘的湘西么?我看出他在犹豫,甚至是失望。我没太往心里去,做出视而不见的样子,心想,你请我来的,总得让我试试吧。
“沅陵城很小,在地图上就是一个小小的点。”完全散文化的句子,我开始了。
“太好了,就是这样!”刘学稼大叫,他兴奋无比,简直就是狂喜。
刘学稼嗓子极好,每到一处,当当的金属声宣告他的存在。当他喊出“太好了”的时候,即使有着厚厚的隔音墙,我都听得分外真切。
刘学稼从不吝啬对别人的赞扬,有时候你能感觉到,他在赞扬你的同时还在感激你。也许他太爱惜自己的片子,他不允许片子有半点瑕疵,当他仰仗的不可控制的外在因素,比如配音、配乐,都如愿地在他面前实现的时候,他的感激溢于言表。
也许我生在湘西,骨子里有同那块土地契合的东西。刘学稼说我解说的情感色彩非常准确,深情、厚重、含蓄而不张扬。
当然,他也知道我读过沈从文、黄永玉的很多书,那些书成了我声音的背景。
刘学稼同别人合作的特点之一,就是一旦认准你,就彻底信任你,他等待着他信任的人给他的作品赋予更多的东西。我时常在完成他片子的时候体会到一种创作的快乐,只要我能感受得到,我就尽情地发挥,刘学稼从不干涉。他真的很少否定,或许我已经不需要他再否定什么了,我太懂得他的东西,我只管表达就是。后来,刘学稼认为我的解说属免检产品,我录音的时候他不再监听,就同其他人抽烟聊天去了。
刘学稼的《湘西系列》基本由我解说完成,有些内容偶尔换了男声,他觉得声音固然贴切,但总少了点他需要的表达特质,因为少了那一点,成了不是他想要表达的湘西,于是,换了男声又觉得遗憾。
他总说,徐俐的声音修养好,难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全国电视专题制作呈现出异常瑰丽的景象,刘学稼的《湘西系列》以他特有的才气和诗情画意征服了同行,成了专家学者时常挂在嘴边的佳作,还获得了政府大奖。
好的合作者可遇不可求。在电台,我看重同编辑霍红的合作。霍红有才气,也有鬼气,她的灵动和激情一现,常使我暗自惊讶。我和霍红有女人之间的惺惺相惜,那种相惜成就了我们最终的默契。默契有时与生俱来,是某种生命特质的相互靠近。我在电视领域的最好搭档应该就是刘学稼,和他的合作,开拓和丰富了我的业务领域。我是善于学习的人,我常在他的片子中得到配音以外的更多东西。刘学稼从不怀疑我会是一个好编导,他对我专业的强烈认同,进一步增强了我的自信心。后来,当我自己独立采访制作一些小型专题片的时候,《湘西系列》片的综合影响彰显无疑。
我的第一部片子是对几对再婚老人的记录,一播出,就接到了刘学稼的电话,说我的起点高,风格好,要我继续做下去。
之后两年,我调到了中央台,同刘学稼的联系少了。听说他总是四处拍片,一会儿海南,一会儿新疆。他活着似乎就要拍片,他似乎永远无法停歇。走向天国的一刹那,刘学稼仍旧孑然一身,他其实有妻有儿,但他早早地离开了他们,他自我放逐着,他的生命似乎永远没有固定的巢,他漂泊在了自己的路上。
刘学稼书生意气,各方面不善经营,听人说他总是把日子过得颠三倒四。现在的刘学稼已到了天国,天国是否寂寞,天国是否开心,到天国可以好好休息了,愿刘学稼安息。
《八角亭》
1994年回到长沙办事,顺便同过去办公室的同事短暂一聚。饭后我想叫车回妈妈家,同事陈志强说,我们开车送你去。我看见一辆不大的吉普车,有些旧,没有牌照。我说,没有牌照被人截住了怎么办?陈志强眉毛一横,说:“哪个敢拦《八角亭》的车?!走吧!”陈志强的话得到其他同事的热烈附和,看得出,这辆没有牌照的车,他们就这样天天开着,大概一次也没有被拦截过。同事如此气粗,我就乖乖从命了。
《八角亭》是一个节目的名称,类似中央台的《焦点访谈》,是我离开长沙台前做的最后一个栏目。
我大约从1989年底开始主持《八角亭》节目。1988年生完孩子,我考虑着下一步究竟该干什么,是继续万金油似的什么都做,还是下到一个部门去,专心做一类节目。考虑再三,我辞去播音部主任的职务,调到了专题部,担任《八角亭》节目的记者和主持人。
《八角亭》一周播出一次,节目时长约二十分钟,通常由两个小主题短片组成。专题部大约三四个记者,每人轮流负责一期节目,我也一样。
我们的节目全都是自采,个人确定选题,个人拍摄编辑完成。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职场风云在长沙台的日子(6)
我在《八角亭》做的第一个节目,就是上面提到的对几位再婚老人的采访,我一开始就啃了块硬骨头。
我在市妇联的内部材料中得知,再婚老人的状况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这些老人在承受着巨大社会压力的同时,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得不到保障。我记得我拍摄了三对老人,其中在长沙农村的一对拒绝拍摄,因为他们害怕后果不堪承受。那对老人是顶着儿女的极大压力走到一起的,但是他们的生活因为儿女的不合作而异常艰难。我去的时候,老人们紧闭大门,任人怎样呼唤都不打开。后来门终于开了,大妈走了出来,我看见她的眼里有泪水。我想问她几个问题,但是,面对摄像机,她别过了她的头。我要摄像记者长时间地盯着老人的背影(在当时普遍的认知上这属无用镜头,而现在已经司空见惯),我理解老人的顾虑,也承认现实的无奈,后来我在解说词里说道:面对摄像机,您何时才能回过您的头?之后,我起了一段音乐,像《辛德勒的名单》的主题曲。
刘学稼说这期节目风格好,是因为我把节目做得比较沉实,有种悲悯的东西。
还有印象的是另一个选题。
那些年造纸行业很不景气,长沙最大的造纸厂天伦造纸厂停产了。对于下岗,人们还不像现在这样司空见惯。当时造纸厂的很多工人不得已离开工厂谋生,因为社会氛围还不习惯接纳失业人员,工人们谋生艰难,尤其在心理上极难适应。有一天,得到造纸厂复工的消息,我就和另一个记者赶去了。我们看到很多工人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对他们而言,复工就意味着回家,就意味着活着的希望。我没有想过我的那个节目究竟要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我只是想忠实地记录复工的过程,很多工人接受了我的采访,他们表达了对曾经生活无望的恐惧,对失而复得的珍视,我录了很多同期声。我永远记得那些接受我采访的工人们的表情,那是些害怕失去的脸,喜悦的背后潜藏着深刻的忧郁。那时对着电视镜头说话是罕有的事,但工人们都不拘束,仿佛他们终于找到了机会,他们想表达在他们的眼里,工厂是他们的命根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亲过。
或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正面接触过那样多的失业者,工人的表情给了我强烈的刺激。我仿佛比工人们更加渴望工厂命运的好转,我给片子取的题目就是“天伦启动了!”天伦终于启动了,一批在生活边缘挣扎的人们终于又有了机会。尽管愿望良好,但轮子最终运转如何我不得而知。我只是在复工的那一时刻做了一个记录者,也许那是政府为国营企业的复生而作的最后一次努力。我想打个电话问问天伦现在是否还在,听说工厂所在的位置早已开发成了旅游区,那里地处岳麓山下,湘江水就在门前流过。
当中央台的《焦点访谈》节目创办播出的时候,我心里有种久违的亲切。也许当初《八角亭》的节目定位没有《焦点访谈》这样明确,八角亭是长沙的一个地名,属旧城最繁华的地区,给节目取名《八角亭》,就是想反映和报道社会生活的焦点问题。我的印象是,焦点二字当时并没有最明确地进入记者编导们的意识,大家只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选题。当我的同事开着无牌照的吉普车载着我在长沙的大街小巷穿梭的时候,我知道,《八角亭》的定位一定清晰明确了,他们为自己赢得了无冕之王的地位。他们一定做过很多有影响力的节目,至于为什么不给自己的车上个牌照就另说了。
我怀念在《八角亭》的日子,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只有那一段我可以被称之为记者。1998年大洪水,我从北京下到湖南岳阳重灾区采访。一天晚上,听说一条大堤有险,我和同行的资深记者迟明泉打过招呼,就径直往险堤上奔。迟明泉扛着机器跟在身后,因为我走得太快,把迟明泉落下了一段距离。等到我们会合的时候,迟明泉对我说:你要当记者一定是个好记者。那次在灾区的采访,我和迟明泉合作得很愉快,我采访写稿,他拍摄编辑,任务完成得很好。我告诉迟明泉,我确实当过记者,在长沙台已经干了两三年,到中央台反而做得少了,长久不做,一来和一线生疏了,二来采访能力也会下降。迟明泉由衷地表示理解。他宽慰我,女性别太累,当主持人挺好。我想过,我的激情和敏锐也许可以帮我成为一个不错的记者,我确实应该做得再长久一些,或者开始得再早一些。在主持人和记者之间,我没有高低判断,两者我都欣赏,我只是因为在1992年调入中央台,记者生涯戛然而止,最终较为单纯地坐到了镜头前而有些遗憾(1992年我把在中央台只单纯地播新闻,视为在业务上走回头路,心理上一度极不适应)。记者是拥有双倍人生的人,在了解别人的过程中探究和发现自己。缺少记者生涯的主持人是单薄甚至是苍白的。虽然以后我又陆续做过一些采访,但总量还是太少。我喜欢意大利名记者法拉奇,看过她的一些书,当我读到她写的《人》,我在想,天哪,她究竟拥有怎样的人生啊。羡慕啊。
朝南的办公室
在过去工作的记忆里,总有一间朝南的办公室。办公室在大礼堂里用木板隔断而成,二十来平米的面积,除四五张简单的办公桌外,两张藤制的宽大沙发椅算是屋内唯一的舒适品。过去没事儿的时候,我喜欢去那间屋子坐坐,闲聊,或者在藤椅上晒太阳。
那里时常像闲来的茶馆,自在又轻松。
办公室里都是广播电视报的编辑,和每天扛机器编片子的人比起来,办报纸的人相对安静,那种不急不躁的劲儿让人羡慕,在上窜下跳的人堆里显出他们偏安一隅。
早晨,太阳爬上窗户边的时候,编辑们该到的都到了。
曹大姐往往是最先跨进办公室的一个。我至今记得曹大姐进办公室就撒水扫地的样子,麻溜溜的,一会儿办公室就干干净净了。曹大姐走路快说话快,说完话还有一个习惯性的问语:“你讲是不?”或者是“你觉得咧?”但是曹大姐只要在办公桌前坐下来,就格外地心无旁骛,时不时扶着她厚厚的眼睛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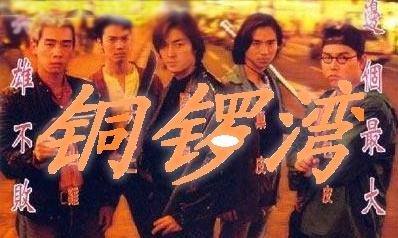
![埃提亚[更新至 第229章大地权杖胡戈第的黑暗阴影(下)]作者:上帝不在天堂.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