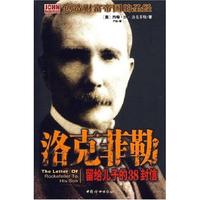3857-非常年代的非常爱情-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时候,有一支猴儿兵悄悄向花果山进犯。其首领就是花果山的叛徒、长得又酷又帅的小公猴。我们前面说过,这只小公猴在仙桃林登上猴王宝座之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终于操练出一支精锐勇猛的猴子兵,今天向觊觎已久的花果山发起百里偷袭。
仙桃林的短尾猴们蹦蹦跳跳地来到花果山下,美猴王立即下令:不准喧哗,不准响动,一百多只猴哥像一片无形无声的影子,贼溜溜地向花果山腹地挺进。当美猴王看见花果山的猴兵猴将们躺在草地上睡午觉,老猴王更是鼾声大作,睡成一头死猪,以为自己逮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高兴得一颗心儿快要跳出胸口。可是,就在它要发起总攻的千钧一发之际,趴在一棵老枫树上的一只金丝猴突然发出一声尖厉的嘶叫:
“唧、唧、唧──”
咳,美猴王作为一国之君还真嫩了点。它怎么忘了花果山的猴儿国即使在举国酣睡的时候,也是有一名特别警醒的猴子兵放哨的。说时迟那时快,花果山的金丝猴们刷地一下都从草地上蹦起,奋勇抗击来犯之敌。老猴王像子弹一样射出去,直取宿敌美猴王。
这是一场兵力悬殊的恶战,没有几个回合,仙桃林的猴兵猴将们溃不成军,落荒而逃。有几个逃得慢的当了俘虏,在对方的拳脚相加狠牙利爪之下颤抖成一片片风中的枯叶。猿猴群落之间的战争,跟我们古老祖先部落之间的战争也有相似之处,那是兵对兵、将对将的较量。美猴王与老猴王过了几招,立即发现自己对老猴王老朽衰迈的估计显然是过于心急了。老家伙还力大无比,拳脚也十分了得,刷地一爪子捅过来,美猴王只觉得屁股蛋上被炭火灼了一下,立马撕开一道口子,喷涌的鲜血把山野的小草都染红了。幸好美猴王四肢矫健,跑得飞快,身躯庞大而臃肿的老猴王赶不上它的速度,只能虚张声势狂怒咆哮,眼巴巴地看着它的叛将逆臣落荒逃去。
唧!唧!唧!──我们胜利了!
唧!唧!唧!──我们胜利了!
老猴小猴公猴母猴们在草地上翻跟斗,在树梢头荡秋千,胜利的欢呼直冲霄汉,震撼山岳。
刘福田托蔡桂花到茂财叔家求亲,遭到王秀秀拒绝,丢尽了面子,气得好些天虚火攻心,牙根红肿,痛得整天嘶啦嘶啦的像吃冰淇淋。他思来想去,就怪到吴希声头上。她王秀秀要不是迷上了这个上海知青哥,还能瞧不起我刘主任吗?刘福田便盘算着如何整一整吴希声。但是,吴希声在队里干活也好,在夜校教书也好,总是兢兢业业,小心谨慎,一时也找不到他的岔子。现在好了,吴希声竟敢背着公社去县里报考文宣队。这不是自己撞到他的枪口上?
“听说你去县里报考文宣队了?”刘福田坐在一张太师椅上,眼睛不看吴希声,只顾埋头卷喇叭烟,说话的口气不咸不淡的。
“嗯。”站在办公桌另一头的吴希声点了点头。
那张太师椅原是从一户地主老财家没收来的红木家具,宽大出奇,古色古香,虽然好看,可是靠背和扶手都没有一点弧度,三面都是硬邦邦直统统的直角,坐起来极不舒服。春山爷忌讳自己一坐上去就像个地主老财,一直没派上用场,扔在屋旮旯里积满了灰尘。没想到刘福田一来蹲点就看上了这件年代久远的老古董,叫通讯员洗洗擦擦,成了他独享的宝座。吴希声偷觑一眼刘福田,觉得坐在那宝座上的家伙的确高人一等,在心理上先矮了一大截,惶惶然地连忙把目光收了回来。
刘福田把烟卷好了,划了根火柴点上,美滋滋地吸了口:“哼,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跟组织上说一声?”
吴希声说:“我跟大队党支部报告过,春山爷给我开了介绍信。”
“哼,你有嘴报告杨春山,就没嘴跟我说一声?”刘福田的手指头敲得桌子笃笃响,像个大首长装腔作势地强调说,“我是公社主任,又在枫树坪蹲点,你也不跟我打个招呼,是不是目无组织?”
“这、这……”一顶大帽子压得吴希声不敢抬头,话也说不清楚了。不知怎的,他见到刘福田就像小鬼见阎王,心里发怵。
“嘿嘿,也不拉泡尿照照自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刘福田冷笑一声,利刃般的目光直刺吴希声。
希声摸不着头脑。他暗自琢磨,这话是讥笑他自不量力去报考县文宣队呢,还是指责他跟秀秀谈恋爱?或者,两层意思兼而有之?
刘福田又阴阳怪气说:“吴希声呀吴希声,我可警告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好,你想跟姓‘共’的斗,不会有你的好果子吃!”
吴希声觉得这话更加费解:刘福田明明姓“刘”,怎么自称姓“共”?难道他能代表共产党?他就是共产党?
看着吴希声像惊吓的小羊羔样瑟缩着,刘福田开心极了。那一瞬间,他想起小时候,他的那奸刁枭恶的悍妇阿婶,也是这样虐待他,作弄他,用竹梢鞭子把他抽得浑身鲜血淋淋的,还一味地咯咯狞笑。当了公社主任的刘福田现在不能用竹梢鞭子抽人,可他那阴毒的目光在吴希声身上扫来扫去,刻毒的话语一句句从嘴里蹦出,更是伤人不见血。
“三天内,你给我写份检查来。”刘福田觉得眼前的对手太不够分量,没必要多费口舌,说完几句笑里藏刀的双关语,就朝吴希声挥挥手,“你可以走了,我没工夫跟你磨牙!”
第二部分 山盟海誓苦槠林中(2)
这次短短的谈话,叫吴希声几天几夜缓不过神来。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报考县文宣队大概不会有希望了。果然,吴希声左等右等,一直等了十多天,总等不到县里的通知。而枫溪公社一起去县里参加面试的,一个厦门知青,一个福州知青,几天前就打起铺盖卷住进县文宣队。吴希声等得无奈,只好悄悄去了一趟县城。他在文庙长廊尽头的一角,在一间小房间里(其实那不是房间,只是用几张旧景片围起来的一角小空间)见到了那个在此蜗居的戴眼镜的主考官。
“眼镜”支支吾吾,说他只管面试,录取的事无权过问。你去问县宣传组吧。吴希声一副要哭的样子,苦苦哀求着,老师,我的面试成绩如何,你总可以给我透点消息吧?“眼镜”说,这次面试不打分数。吴希声说,我来县城两趟,从枫树坪到县城单程是八十里,两个来回,得走三百多里路呢,老师,老师,你谈谈对我演奏的印象,给我指点指点,总可以吧?“眼镜”看见泪珠儿在吴希声眼里打转转,心里也很难过,犹豫半天,才拍拍吴希声的肩膀说,小伙子,实话告诉你,我原来是省歌舞团乐队的指挥,做音乐工作二十多年了,我还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棒的小提琴手。真的,你的演奏简直好极了,无可挑剔!无可挑剔!……“眼镜”说完这些话,马上又有些后悔失言,连忙捏着嗓门补充了一句,不过,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不算数的,不算数的!吴希声却大惑不解、满腹委屈,眼泪汪汪地问道,老师,那文宣队为什么不肯录取我?“眼镜”于心不忍,又轻轻地拍拍吴希声的肩膀,听说是政审没通过。唉,小伙子,这事你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呀!这年头,政治第一,政治第一!……
吴希声已经记不起是怎样离开“眼镜”老师的。但他永远不能忘记,走出文庙大门,踯躅于一条窄窄的小巷,他昏昏沉沉,竟分不清东西南北。突然咚地一声,撞在一根电线杆上,脑门鼓起个毛栗子般的大包,当时竟一点也不觉得痛。
对吴希声来说,这真是当头一棒!它不仅意味着将无限期留在枫树坪“接受再教育”,还彻底扼杀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当小提琴家的美梦。如果说,肉体是人的生命的一半,精神是人的生命的另一半,只有肉体与精神完美的结合,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有价值的生命,那么,在精神支柱完全垮了之后,吴希声的生命只剩下一个没有意义的躯壳了。
吴希声回到知青楼,关上门,从墙上取下那把法国维约姆牌小提琴,忍了许久的眼泪如两柱飞流直下的瀑布,哗啦啦挂满了忧伤的脸。他把小提琴高高扬起,想一家伙砸个粉碎完事。忽然,他听见小提琴奏出《圣母颂》的旋律,同时响起恩师丽达诺娃语重心长的声音:
“记住这支曲子吧,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你会变得有力量的。贝多芬说,‘谁能了解我的音乐,谁便能超越常人无以摆脱的苦难。’孩子,坚守高尚的音乐,你在苦难中就会坚强一些。”
吴希声硬是把泪水止住,心情稍稍平静了些。他想,贝多芬真是了不起的大英雄!他从二十五岁起就患了耳疾,几年之后完全失聪,这对全靠听觉寻找创作灵感的作曲家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然而,贝多芬此后的创作仍如汹涌的喷泉,《英雄》、《命运》、《田园》……一部又一部交响曲与协奏曲,都是无与伦比的杰作。自己能用贝多芬的音乐来“超越常人难以摆脱的苦难”吗?吴希声的回答是否定的。自己尽管耳聪目明,年纪轻轻,却比聋子贝多芬和瞎子华彦钧更加不幸!因为,他现在被扔在一个黑洞洞的地窖里,看不见一丝光线,听不到一点声音,他心如死水,还能与神圣的音乐结缘吗?
也不知怎的,吴希声竟莫名其妙地埋怨起“眼镜”老师。唉,老师呀老师,你还不如把我的演奏贬得一钱不值呢,你干嘛要说我的演奏无可挑剔?你干嘛要向我透露“政审没有通过”?不幸对于吴希声来说,原先只是懵懵懂懂的。他以为他们这一代年轻人都是与音乐无缘的,现在,他被孤零零地从一大群不幸者中剔除出来,就显得尤为孤独和更加不幸!
由政审不能通过,吴希声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自己的父亲。现在,他不能不对自己的父亲有几分埋怨几分憎恨了。父亲呀父亲,你莫非真的是个叛徒、特务?你莫非真的是个反动学术权威?你可把你的儿子害苦了呀!但是,当吴希声把自己慈祥而威严的父亲细细地想了一遍,他心中的怨忿却慢慢打消了。
从稍稍懂事的年龄起,吴希声所看到的父亲就是了不起的英雄。吴希声家里有个不大不小的琴房,父亲在钢琴跟前坐下,或是一拿起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萨克斯管,无论什么乐器,他都能奏出美妙的乐曲。最叫希声永世难忘的,是听父亲执棒指挥的大型音乐会。这一天,父亲长着络腮胡的双颊必定刮得泛起青光,穿上黑色笔挺的燕尾服,像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从容不迫地登上指挥台。他炯炯有神的目光环视一下整个乐队,然后轻轻举起那根灼灼闪光的银质指挥棒。霎时,一百多人的交响乐队寂然无声。父亲的指挥娴熟流畅、激
情澎湃。小希声首先惊异的是父亲那个硕大神奇的头颅,怎能记下各种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交响曲总谱。该快的快,该慢的慢,连一记小鼓,一声小号,都毫不含糊地给以关照、暗示。他知道,父亲那个交响乐团的弦乐、管乐和打击乐的演奏员们,比如恩师丽达诺娃,都是些技艺超群的人物,但是在父亲的指挥棒下,一个个都心领神会,配合默契。这都因为父亲指挥细腻、到位和绝对的权威。父亲不仅仅靠指挥棒指挥。他有时会收起握在右手的银质指挥棒,只用一只左手,愤怒时挥舞铁拳,抒情时用一根食指作蜻蜓点水状。父亲忧郁或含笑的目光,脸上放松或绷紧的肌肉,上扬或下垂的眉毛,也无时不在传递指挥的信息。小希声甚至发现,父亲蓄起一头披肩长发,也不是为了显示一个音乐家的风度,这在指挥乐队的时候自有用场:当乐曲静如流水,微波不兴,父亲的长发也按兵不动,柔顺垂肩;当乐曲掀起狂风暴雨,炸响震天惊雷,父亲的长发便像黑色的火焰在风中飘扬。这支训练有素的交响乐队在父亲的指挥下,把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等大师的传世之作,化作春水在溪涧流淌;化作鲜花撒向听众心灵的田野。每次演奏完毕,全场有如凝固似的沉浸在一片肃穆之中,然后才突然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父亲这才缓缓地转过身来,脸带谦恭而庄重的微笑,面向森林一样站起来的观众,一次又一次鞠躬致谢。而后,他怀里便拥满了鲜花,也拥满了成功的喜悦……
像老师丽达诺娃所说的,父亲就是个“心里有高尚音乐”的人,我吴希声的“政审”怎会不能通过?父亲难道真是个坏人?这个问题搅得吴希声头疼欲裂。蓦地,他又想起“文革”初期曾经听说过,父亲在三十代和江青共过事,心里陡地一惊,隐隐约约感到父亲的问题和那个叫蓝苹的女人也许不无关系,要不,父亲关在清队学习班里怎会遥遥无期?
第二部分 山盟海誓苦槠林中(3)
吴希声在斗室里转来转去,像只关在笼中的小兔,怎么也找不到出路,惊慌了,恐惧了,浑身觳觫,大汗淋漓。啊,总算理出个头绪了:你以为你是谁?还想跳出枫树坪?还想子承父业?还想当小提琴家?还想怀抱鲜花获得崇高的荣耀?你做梦去吧,吴希声!
吴希声轻轻抚摸着小提琴。从旋首、琴颈、共鸣箱,一直抚摸到底角板和尾钮,像抚摸心爱的情人,引起心灵阵阵颤栗,一串串热泪洒在小提琴的面板上。然后,他又把小提琴擦拭干净,小心翼翼地收进琴匣,再悬挂在小床对面的墙壁上。吴希声已经死了拉琴的心,不会再拉琴了。让心爱的小提琴和高尚的音乐,永远深藏在心底吧!
啊,永别了,我的音乐!
王秀秀得知吴希声被县文宣队拒之门外,立即去知青楼安慰他,同时掩饰不住心头的喜悦。王秀秀说,文宣队有嘛了不起?不收就不收呗,我该去买一串鞭炮放一放!
希声有点生气,咦,你怎么幸灾乐祸?
秀秀说,哥,我们在汀江边起过誓的:你要是考得上,你就算我哥,我任你远走高飞;你要是考不上,你就是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