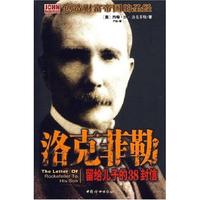3857-非常年代的非常爱情-第4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是,又过了几天,却听说学习班有了重大的突破。据派到知青楼站岗的基干民兵透露:突破口是从大软蛋张亮那里炸开的。张亮是吴希声最好的朋友,两人从穿开裆裤时起,就在一个幼儿园玩耍,在一个小学和中学读书,情同手足,无话不谈,拎出点违禁犯忌的只言片语,再加油加醋,上纲上线,还不是小菜一碟?听说,张亮那小子写的揭发材料,码起来足有一筷子高哩!
像个刚用搅屎棍搅过的大粪缸,张亮的名声很快臭遍了枫树坪。
张亮还没走过半个村子,心就发虚,腿就发软,呼吸也有些急促起来。他发现,村里男女老少都用愤怒而鄙夷的目光瞅他、盯他,恨不能吃了他。张亮吓了一跳,脑壳涨成巴斗大:我的妈呀!莫不是大家都把我看成了卖友求荣的陆谦了?把我看成背叛同志的甫志高了?准是这样!张亮已经看到有人在一旁窃窃私语,甚至隐约听到“叛徒”、“告密者”这样一些指桑骂槐的诅咒。
张亮晕晕乎乎地往前走,迎面碰上瘦骨伶仃的王秀秀。张亮张了张嘴,想表示一下问候,或者说点什么。
秀秀眼一瞪,朝地上吐口水,呸了一声,又跺了一脚,转身走了。
张亮满脸羞惭,不愿再与人碰面,更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他急匆匆往村外走去,却发现一路上遇到的家禽家畜们对他也态度大变:鹅公们一看到他,都是拧着脖子翻白眼;牛牯们看到他,一双双铜铃似的大眼球里充满了蔑视;鸭嬷们一碰上他,就嘎嘎嘎的,尽是怪里怪气地冷言冷语;狗牯们碰上他,像见到贼,汪汪汪地吠个不停。……张亮想,我的天呀!全村男女老少和家禽牲畜们都抱成了团,嘲笑我,唾弃我,挤兑我,还叫我怎么活哟?
张亮再也不敢走出知青楼,整天在房里呆着。可是,他不愿见人,有人却偏偏要见他。有一天,瞎目婆张八嬷拄着藤条拐杖来到知青楼,见人就问,希声放回来没有?希声放回来没有?张八嬷说,她在新疆当军官的小孙子又来信了,要请吴希声读信写信。
知青们都推说不知道,这事要问张亮。张亮是上海知青。张亮躲避不过,透了点消息,说吴希声还关在县公安局。这下可惹了大祸。张八嬷手中的藤条拐杖立时动了怒发了威,戳得杉木楼板嗵嗵响,用有眼无珠的眼睛对准了张亮:不是讲摔死秀秀小崽子的是只小猴哥吗?怎么还把吴希声关着?是哪个黑心肝的落井下石?是哪个烂肠子的在后面捅刀子?连吴希声这样的老实人也敢欺负,要遭天打雷劈啊!……
瞎目婆看不见张亮脸上无地自容的表情,愣哭愣哭,愣骂愣骂,张亮一声也不敢吭,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人掏了出来,用一根竹竿高高挑起,在光天化日之下曝光示众。
张亮知道罪有应得,一直忍着,而且极想求得人们的谅解,就讪讪地说,阿婆,你孙子的信,我来帮你读,帮你回吧。
哼,瞎目婆冷笑一声,我怎么敢劳你大驾?你又会说,又会写,还是忙着给公安写材料吧!刘福田会给你记功发奖招工招干哩。
张亮满脸羞红,恨不得一头撞死在石柱子上。
在这支以“红五类”为骨干的上海知青队中,张亮是个异数。他是上海滩一位丝绸大亨的阔少爷,“文革”初期向往革命的疯劲是全校有名的。“红五类”们纷纷参加红卫兵的时候,张亮连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权利也没有。可他是个死心眼,人家不让戴,他偏要戴。张亮拿一块瑞士梅花牌名表跟一位“红五类”同学兑换了三块毛主席像章。第一块是铝合金的,大红漆底浮雕金像,张亮激情满怀地别在一件旧军装的左胸前,可是被造反派看见,立马就摘下没收了,连那件旧军装也不准穿。那个年代,不缀着领章帽徽的军装是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标志,他妈妈的,老子革了命,还有阿Q的份吗?张亮并不灰心丧气,而是再接再厉,把第二块像章──一块瓷都景德镇烧制的白玉瓷质彩色宝像,小心翼翼地别在内衣里,可是再次被造反派发现,又毫无道理地收缴了。张亮不屈不挠,当着众多造反战士的面,撕开自己的内衣,把第三块像章──一块有机玻璃制成的具有夜光功能的宝像,径直别在自己肌肉鼓鼓的胸脯。锋利的别针扎进细皮嫩肉,血如泉涌,张亮胸前红了一片。同学们都惊呆了,连连退缩,远远站着观望。只有扎着两根小辫、身穿旧军装、腰束军皮带的蓝雪梅走了过去,使劲拍着张亮的肩膀说:
“行,张亮!你是我们战斗队的一员了!”
然而,张亮依然不能像“红五类”的红卫兵那样为所欲为,叱咤风云。因为出身成分像古代囚犯的鲸印一样烙在张亮的脸上和心上,批斗起那些出身高贵、历史光荣的“走资派”来,他还是有些自惭形秽底气不足。张亮惟一值得一提的,是带头造他资本家老子的反。除了贴出一批又一批杀伤力极强的大字报,他还带领蓝雪梅们到自己家抄家挖“浮财”。张亮
自充内线,提供情报,一挖一个准。不管他爸他妈埋在夹壁里还是藏在地窖里的“封、资、修”垃圾──从绫罗绸缎到奇装异服,从金银首饰到珍珠玛瑙,从古玩名画到线装古籍,从冬虫夏草到朱砂玉桂,从洋参鹿茸到熊胆虎胶,从金条银元到法郎美金,──全被搜出,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接着,有些付之一炬,有些上缴国库,有些被人顺手牵羊,饱了私囊。那个漂亮的攻坚战战果辉煌,轰动全校,张亮也就出足了风头,成了与“反动”家庭彻底划清的“可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
可是,后来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领袖蓝雪梅还是怕张亮吃不了苦,为了要不要接纳张亮参加自己的知青队,颇有一番踌躇。张亮突然又来了牛劲,郑重其事地递给蓝雪梅一封血书:“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扎根农村不动摇,誓做革命接班人。”这是张亮撕下一件白衬衫,割破手指头,用自己的热血写下的二十九个大字。
蓝雪梅记得,张亮咬破了的手指还来不及包扎,他举起血肉模糊的手指,就像举起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蓝雪梅大为感动,立即吸收张亮参加奔赴闽西老苏区的上海知青队。
第四部分 犹大的悲哀人比狗辛酸(5)
现在,上海知青队的最后一员──张亮,呆在锅清灶冷、四傍无邻的知青楼,感到极度的恐慌和悲哀。他把自己在“文革”初期的疯劲傻冒全都回忆起来了。咳,我一个劲想跟上潮流,一个劲想脱胎换骨,到头来怎么还是处处遭人唾弃?天啊,长达八年的知青生活,简直像一场噩梦!八年了,我学会各种农活,能一口气抡一百二十五下大锤,却远离书籍,把学到的知识都还给了老师;我轰轰烈烈、死去活来地爱过一个善良的姑娘,却留下终生的屈辱;我结交过一个同甘共苦、绝顶聪明的朋友,却把朋友送进了大狱……
张亮一想起吴希声这会儿关在大牢里受苦,就觉得他那只左手的大拇指隐隐作痛。他非常痛恨这只大拇指,常常把大拇指竖起来,看见一圈圈螺纹上还残留着印泥的红痕,那是永远洗刷不了的污斑。
他妈妈的,这是一只多么倒霉的臭手呀!就是你的屈服,老子这七尺男儿才成了一只断了脊梁骨的哈叭狗!难怪乡亲们和知青们都朝我瞪白眼吐口水啊。
一天夜晚,张亮看见一辆吉普车进了村,发现刘福田那小子不知有何公干回到枫树坪。张亮心里一动,突然冒出个疯狂的念头。张亮灌下半斤地瓜烧,喝了个半醉不醉的,怀里揣上一把军用匕首,踉踉跄跄闯进大队部。
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张亮像一具可怕的僵尸,突然戳在刘福田跟前。
刘福田吓了一跳,从那张古色古香的太师椅上站起来,哆哆嗦嗦地呵斥道:“哎,张、张亮,你,你,你有嘛事?”
刘福田惊慌四顾,想随手抓件防御的家伙,比如扁担、木棍什么的。这个愣头青张亮,一口气能抡一百多下大锤,他深更半夜闯了进来能有好事吗?可不能不防着点儿。
满脸通红的张亮,把浓浓的酒气喷到刘福田苍白的脸上:“姓刘的,快把我写的那份揭发材料还给我,那些屁话都是我胡编乱造的。”
刘福田说:“所有材料都是公安局拿去的,我怎么要得回来?”
张亮说:“那就立马把老子的招工手续办了!”
刘福田用鼻子哼了一声。他发现张亮原来是有求于人的,而自己正是掌握权力被人求着的人,高高在上的权威感又回到他身上,口气便硬了起来:“嘿,还老子老子呢!这事由你说了算?”
张亮两道灼亮的目光刷地一下射向刘福田:“你小子别忘了!造大寨田的时候,你说过谁表现好,给谁招工;叫我写揭发材料的时候,你又说过,写了材料就给我办招工。咹,刘福田,你没忘记吧?”
“就算我说过这些话,那又怎么样?”刘福田眯着眼十分不屑地瞅着张亮,“哈哈,就凭你这种态度,你还想……”
张亮嗖地一下从裤兜里抽出军用匕首,往办公桌上一拍,昏暗中飞起一道蓝幽幽的寒光,把刘福田还没说完的话吓了回去。
“你,你,你敢行凶?”刘福田凶巴巴的脸一下就黄了,“张亮,别、别乱来呀,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哼,一个孬种!”
张亮说着把匕首掂在手里,另一只手搁在桌上,咔嚓一声,一道血光飞溅,一个大拇指剁了下来。这个大拇指,正是在揭发材料上摁过犹大式手印的那只左手的大拇指。张亮已经恨它厌它有许多日子,今晚终于找到一个机会给它严厉的自裁。那个脱离了主体的大拇指仿佛不胜委屈,在桌子上蹦了两三下,才老老实实地静卧在桌子上,像一块涂了红糟的猪蹄肉。
刘福田倒退两步,吸了口冷气,胆战心惊地直摆手:“张、张亮,别、别犯傻,别犯傻!有、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啊!”
张亮手上的军用匕首在空中挥了挥:“姓刘的,老子现在是个残疾人,按政策,应当招工优先。”
张亮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条洁白的手帕,这是他早预备好的,从容不迫地拾起血肉模糊的断指,裹了起来,郑重其事地递给刘福田。
“你就把这个交给县知青办和人劳组,向他们要个招工指标。万一要不到招工指标,就给老子办残退返城手续。”
“成,成,我一定尽快给你办!”刘福田已经吓得快瘫了,战战兢兢说,“这个,这个,就不要了吧!”
“那也行。”张亮把那只血糊糊的手指头装进兜兜里。他想,老子留着做个永久的纪念也好。哼,这个可耻的大拇指!
第三天拂晓,天才麻麻亮,左手大拇指上缠着绷带的张亮,已经走在灰蒙蒙的山道上。除了刘福田,谁也不晓得张亮就这样满怀悲愤地离开了枫树坪。
一勾残月慢慢西沉,几点寒星摇摇欲坠。东方天际亮了起来,一抹曙色包裹在浓雾中,像打烂了的鸡蛋黄发出浑浊的微光。张亮走在露湿裤管的小路上,步履蹒跚,泪雨滂沱。他的伤心,不仅为自己,也为蓝雪梅和吴希声,为整个上海知青队。
第四部分 犹大的悲哀黑色星期五(1)
张亮走后第二天,春山爷和秀秀搭上一部进城的拖拉机,去县城搭救吴希声。本来,春山爷不肯带上秀秀。秀秀愣哭愣哭,死缠活缠,说希声坐牢是她害的,不见希声一面,她死不瞑目。春山爷只好依了秀秀。
坐在拖拉机车头,春山爷时不时摸一摸娟娟给他缝的青花布袋。布袋里装着一份“万民折”──那是吴希声的命根子。春山爷特地到枫溪镇求一位教过几年私塾的老先生,写了一
份有理有据,言辞恳切的申诉书,为吴希声喊冤请命。春山爷挨家挨户征求意见。全村乡亲念着吴希声教夜校、算工分、协助春山爷连续多年搞“瞒产私分”的种种好处,念着他和秀秀演绎了一个凄婉感人的爱情故事,两百多户人家的成年户主,全都毫不含糊地在“万民折”上摁了指印。无数带着印泥芳香的指印,像清明时节的映山红开得满山遍野,既轰轰烈烈又阴阴惨惨。
进了城,春山爷带着秀秀直奔红军干休所。春山爷当年的一位老首长,如今离了休,就住在这里颐养天年。老人八十来岁,是1929年春天毛委员和朱军长率领红四军入闽时的老红军,全县人都尊敬地叫他“红军爷”。
“文革”前,县里的干部有谁敢违法乱纪多吃多占的,只要红军爷哼一声,谁就得身子哆嗦更弦易辙。因为红军爷当年任过红十二军的团长,他的许多老战友如今都是中央和部队的大首长。老百姓都说红军爷只要花一张八分钱邮票,或者拨个长途电话,就能通天,就能为民申冤,就能把天大的事情摆平。春山爷心想,请红军爷向上级革委会呈上“万民折”,再凭老人威镇乡里的名声,十有八九能救吴希声一条命。
红军爷戴上老花镜,把“万民折”认认真真看了一遍,轻轻摇头叹息道:“唉,没用了!我听讲,这个案子已经判下来了!”
“噢!”春山爷和秀秀心里凉了半截,“判了?怎么判?”
红军爷张了张嘴,满嘴雪白的假牙滑稽地措动好几下,才吐出冷冰冰的两个字:“死罪!”
春山爷看见秀秀的脸一下就白了,身子一晃,差点栽倒在地。春山爷连忙搀扶秀秀在椅子上坐下,又给她筛了一杯热茶。
秀秀喝了两口水,慢慢打起精神,扑通一声跪下,苦苦哀求道:“红军爷!红军爷!请你救救吴希声吧,他是冤枉的啊!他是冤枉的啊!枫树坪的乡亲们,没有一个不说他是个好人哪!”
红军爷一直摇头:“来不及了!上头的指示电报都下来了:明天行刑!唉,可怜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