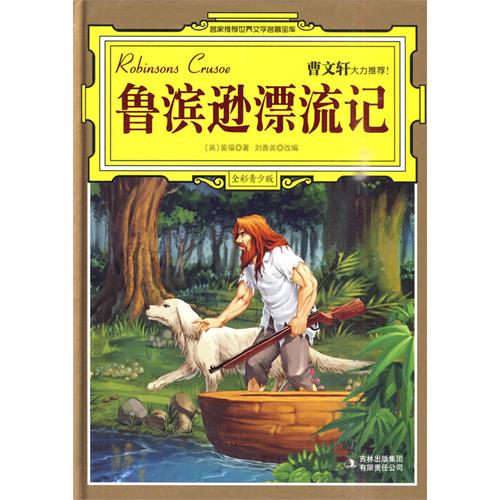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5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研究系是个依附北洋军阀的反动派系,在政治上,它有相当大的活动能量,在思想战线上,它控制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大报,如《晨报》和《时事新报》。在大革命期间爆发的多次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它所控制的舆论工具都作了充分的表演,充当了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的“诤友”和帮凶。然而,以研究系为代表的这类反动舆论,却往往被人所忽视,因此,鲁迅对它的揭露和批判,就更具有重大的思想意义,显示了他敏锐的政治眼光和疾恶如仇的革命精神!尽管他在批判研究系的文章中并没有公开点名,但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却是不止一次点明了研究系的,在这些信中,他明确表示了要“痛击”研究系的坚决态度。1926年10月20日的信中说:“研究系比狐狸还坏”此信即《两地书》中的第五十八信。《两地书》公开出版时这一段被删去了。文中所引见《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二册第六四页。。同年11月1日的信中说:“研究系应该痛击,但我想,我大约只能乱骂一通,因为我太不冷静。他们的东西一看就生气,所以看不完。结果就只好乱打一通了。”此信即《两地书》中的第六十六信。《两地书》公开出版时这一段被删去了。文中所引见《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二册第八○页。同月七日的信中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至多无非我不能到北京去,并不在意。”此信即《两地书》中的第六十九信。《两地书》公开出版时,此处有所修改,“研究系”三字被改为“绅士们”三字,参看《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二册第八六页。由此可见在当年的思想战线上,鲁迅是把研究系当作自己最主要的敌人。过去,由于我们对背景不够了解,没有弄清一些杂文的针对性,常常把鲁迅所反映的广阔的政治背景和横扫魑魅魍魉的斗争锋芒,仅仅局限在“现代评论”派及陈西滢之流的范围之内,这是非常不够的。这是这两本杂文深刻的多方面的思想意义长期没有被发掘出来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彷徨”到战斗
“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后,鲁迅进入了所谓彷徨时期。《新青年》时代的战友,“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这种变化,他在辛亥革命后已“经验了一回”,现在“又经验了一回”。每一回都使鲁迅处于暂时的沉默时期。特定历史时期革命阵线里的伙伴,决不会铁板一块,总是要起变化的。这是剧烈、复杂阶级斗争中的必然现象,是革命深入发展的一种表现。鲁迅后期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他指出:“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可是,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对于革命进程中发生的某些分化现象,却无法正确理解,因而产生了彷徨情绪,这是前进途中思想上经历激烈矛盾斗争的一种反映。
鲁迅的彷徨时期应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即五四运动后,当年的伙伴分道扬镳,北京文化界出现一种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景象。其时,鲁迅的彷徨属于重新战斗前的休整时期,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在思想上进行新的酝酿。这是鲁迅“五四”以后杂文创作最少的时期。他在《热风·题记》中说:“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散失的我们今天已经收集起来,数量确实不多,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彷徨而“不做”。后一阶段,即1925年以后,在大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浪涛的冲击下,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惊恐万状,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它们互相勾结,制造了一系列鲜血淋漓、灭绝人性的惨案,一次次地把中国人民推入血泊之中。然而,疯狂的镇压只能激起强烈的反抗。从1925年起,反帝反封建的烈火越烧越旺,现实生活中不断发生惊心动魄的流血事件,促使渴望战斗的鲁迅直接地投身到阶级斗争的激流中去。同时,对马列主义的更多接触和学习,对苏联情况的更多了解,为他清除思想里的“毒气和鬼气”《鲁迅书信集》上卷;第61页。提供了新的条件。在这些主、客观条件下,鲁迅逐渐摆脱前一阶段彷徨情绪的负累。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近来的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样颓唐。”《鲁迅书信集》上卷;第82~83页。后来在《海上通信》中总结自己的思想时又说:“从去年以来,我居然大大地变坏,或者是进步了。虽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经创伤,或者不再觉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并不觉着一点沉重了。”他公开宣布,从今以后要“蔑视他们,并且蔑视他们的蔑视了”。这里,战斗豪情已然取代了残存的彷徨情绪,标志着他将以新的姿态去迎接新的战斗!
《华盖集》及其“续编”的基调是昂扬的,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反映了他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冲锋陷阵的雄姿!它没有像散文诗《野草》某些篇章中存在的那种消极空虚的情绪,失望灰暗的色彩,因而使人产生某些重压之感。当然,这两本杂文还是打上了一点彷徨烙印的,主要是《华盖集》前半部,流露着封建势力猖獗、复古气氛浓厚,而新文化阵营却“量少力微”,在向封建文化思想进攻中,鲁迅感到还形不成联合战线,只能进行“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华盖集·通讯》。,从而产生孤军奋战的感觉。随着“女师大风潮”、“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的发生,血腥的现实,激烈的斗争,已经不允许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暴风雨中彷徨,他像一只海燕似的,在暴风雨中进行英勇的搏击!这两本杂文就是他大革命时期的战斗记录,反映了他坚持战斗、坚持前进的硬骨头精神!
只有革命者,才能享受战斗的欢乐,才会珍惜战斗的成果。鲁迅对这两本杂文是有深厚感情的。当时有人劝他不要写这样的杂文,他认为战斗时代需要战斗杂文,如果艺术之宫里竟然有这样麻烦的“禁令”,那就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摸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对这些杂文,鲁迅充满感情地说,我“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华盖集·题记》。。《热风》是“几个朋友”替他“编辑起来”《热风·题记》。的,《华盖集》及其“续编”是他自己主动而及时地编辑出版的,可见他的“偏爱”。然而,恰恰是这两本杂文“销路独少”,因为有些读者误以为其中反映的是个人的恩怨。因此,对这两本杂文作点探讨,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吧!
(原载《鲁迅研究文丛》第1期)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论鲁迅对《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的反拨(1)
本文拟从重新审视《二心集》型批评文体入手,深入描述鲁迅对苏式文论形式认同、模拟、扬弃的过程。文体并非纯粹的形式,乃是沉积着思想的“有意味的形式”。故以下研究不局限于单纯的语言表达式,将不可避免地不时折射形式背后的思想。
接受苏式文论对鲁迅而言,不仅意味着“以史底唯物论”穿透了“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同时也意味着为鲁迅提供了一种新的表达式。至《二心集》时期(大至涵盖了《三闲集》后期至《南腔北调集》这一阶段),鲁迅终于完成了批评文体的转换。不见了前期的隐晦曲折,而代之以一种观点鲜明、逻辑严密、明白晓畅的理论风格。
如何评价《二心集》型语言形式?很长一段时期,学界每每依据鲁迅自称“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更依据“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一类的指示,将其视作鲁迅批评文体发展的顶峰。即使是极具理论穿透力的李泽厚,在新时期初始也未能免俗,一度激赏其“明朗、坚定、酣畅和一往无前的磅礴气势”,并将它誉之为鲁迅“后期文笔的崇高风格”的代表。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461、467页。
历史垫高了今天的研究者,使我们能够避免为某种既定的价值观念所遮蔽,而在一种更开阔的视界中、以一种更从容的理论心态对《二心集》型批评文体进行剖析、辨证。
《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的特征之一便是论述方式的趋向理论化。如果说,鲁迅前期文艺思想的表述更多地借助于扑朔迷离的文学的符号,那么,苏式文论形式的引进便意味着鲁迅有了一个完整的概念系统作参照。它帮助鲁迅对那些离散性的朦胧的感觉印象进行整合,使他的语言形式凸显出一种理性化的简括明晰。
在鲁迅以苏式文论整合前期思想的过程中,阶级斗争理论与阶级分析方法无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二心集》时期,鲁迅正是抓住阶级斗争这条“指导性的线索”,将“暧昧难解”的对象世界有序地纳入了一个逻辑化的图式中;也正是借助于这条线索,使他所坚持的阶级斗争一翼的文艺思想、叛逆携贰的立场与二极对立的思维格式完成了颇具逻辑统一性的同构。
阶级斗争话语的袭用还赋予了《二心集》型批评文体一种前所未有的确定性、鲜明性。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已不允许鲁迅再“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而要求鲁迅跳出个人性的话语圈,成为阶级的代言人、成为“完全确定的倾向的传播者”。尽管勉为其难,然而鲁迅还是勉力地“遵命”了。于是,我们在《二心集》语言形式中,可以看到鲁迅的运思方式、批评风格由怀疑转为确信、由彷徨转为坚定、由拥抱两极转为执守一端等一系列耐人寻味的演变;其中,特别具有形式意义的是由充满悖论的语言形式向某种独断性文体的转换。
转换了的“完全确定的倾向的传播者”的角色使鲁迅的声音变得那么的肯定、强硬、不容置疑。因为即使此时鲁迅的内世界中仍未停止所引进的苏式理论与自我意识的“格斗”;但一旦他以阶级代言人的身份出现时,他不能不以强硬的“护心镜”遮盖住内心世界中的格斗,以免自露破绽;他不能不在一致对外的“盾牌”后维护左翼队伍的集体形象,不使敌手有隙可击。它要压倒一切,而绝不能被论敌所压倒;它要鼓舞士气,而绝不能动摇军心。由是促成了它的语言风格刀剑般的铿锵有力、斩钉截铁、势不可敌。
综上所述,对苏式文论形式的参照、模仿,使鲁迅文艺思想、文学批评的文体渐趋理论化、逻辑化,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鲜明性。必须强调,以上只是肯定《二心集》语言形式思辨层面上的拓展,而并没有将其视作极境。诚如一位学者所言,“一种选择必将带来一种新的局限。”选择的负面影响对犹处于模仿性接受阶段的《二心集》型批评文体而言也是有迹可寻的。
当鲁迅难以整合他对生命、对文学的离散性的、朦胧的印象体验时,他求助于苏式文论形式中的科学理性。这是必要的一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理性的引入必须以放逐情感性、诗性体验为代价,也不意味着某一理论模式的选定就能无所不包地囊括对所有文学现象的认识。须知,在科学理性所能照彻的领域之外,仍有着理性难以穷尽的非理性的波动、振颤;而文学思想的建构之所以区别于哲学、政治学,就因为它仍需要近乎直觉的审美体验,需要灵气、诗性。这便解释了,何以《二心集》时期,当鲁迅竭尽全力地将作品的意义朝某种既定的科学理论阐引而搁置了前期对文学、对生命的人本主义探询时,我们会感到那貌似炽烈的政治热情有时难以掩饰批评主体切身生命体悟的冰结;这也解释了,何以当生命、文学被鲁迅借苏式概念、形式剪裁了、抽纯了、界定了后,我们会觉得新的语言形式因过滤了生命的血色、文学的灵气似乎显得有点僵硬。
鲁迅所借鉴的苏式理论话语不仅先天地存在着忽视审美体验的狭隘;而且还带有将文学的阶级功能绝对化、阶级分析普泛化的局限。对于苏式文论的这一局限,鲁迅并非毫无觉察,尤其是因着太阳社、后期创造社某些成员的归谬性运用,放大了它的局限时,鲁迅一度也有所针砭;然而,与新月社、“第三种人”的论战、对“文化围剿”的回击却终于使鲁迅“竭力增强阶级性说”。
与此对应的,是《二心集》型语言形式中的二极对立思维格式。在苏式话语中,辩证法往往因阶级斗争的格局而被实用主义地简化、机械化了。鲜活复杂的现象世界被生硬地“一分为二”:非黑即白、非新即旧、非友即敌、非左即右……曾几何时,鲁迅自己也体验过、呈示过在二极对立的格局间,仍有一些非对立的格局所能涵括的混沌现象,例如“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又“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的不明不暗的“影”;然而至《二心集》时期,他却摈弃了上述切身生命体验,断然否认在左翼与右翼的对立间尚有“第三种人”及“第三种文学”存在的可能。他不无绝对地分析道:“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鲁迅全集》第4卷;第534页。如果说“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又“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的“影”一类的表达暗合了前期语言形式的诗性含混;那么,“非近于胖,就近于瘦”一类的话语恰可作为《二心集》时期鲁迅非此即彼思维格式的象征。
非此即彼的思维格式可谓是方法论上的独断。在势不可挡的逻辑动力感中,暗含着执守一端去压倒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