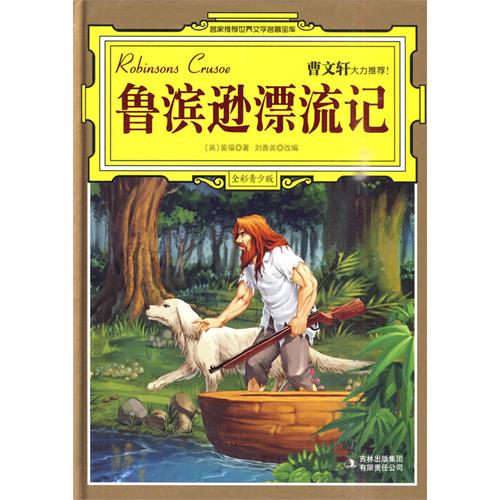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6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非此即彼的思维格式可谓是方法论上的独断。在势不可挡的逻辑动力感中,暗含着执守一端去压倒另一极端的阶级斗争的驱力。往往由于它的过于猛烈,在横扫一切、痛快淋漓之余,不仅淹没了异端的声音,同时也惯性运转地越过了鲁迅对“一翼”理论偏激的美学抑制。
《二心集》型语言形式或许不失为强化文学的阶级功能的刚性武器;但作为多元浑涵的文学思想、文学批评的载体而言,显然缺乏必要的弹性。然而,长时期以来,研究者却每每将其视若经典语言形式:止于激赏《二心集》文体中酣畅有力的逻辑动力感,而无视那气势相当程度上得力于非此即彼的思维格式;激赏那斩钉截铁、不容置疑、不容证伪的语气,而无视断语后隐隐可见的必然论的影响痕迹。正是由于《二心集》文体——“难以逾越的高峰”这一神话的笼罩,遂使《二心集》时期后鲁迅批评文体的转换一度成为研究的盲点。
对于一切“虚悬了一个‘极境’”的人们而言,鲁迅总是煞风景的。在他说了“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这句被某些研究者反复援引的话之后,偏偏又说“因为后来又有了新经验,不高兴做了。”致萧军、萧红的这封信对鲁迅批评文体转换的原因有所提示:执守“政治斗争的一翼”,语言鲜明地口诛笔伐、却难防友军暗箭的境遇,使鲁迅的话语立场由执守一端变为“横站”;遵循既定理论模式、二极对立地逻辑解析了现象世界、却难以统摄自身生命体验的困惑,使鲁迅的思维格式难以继续保持原有的理性化的单纯、明快,而呈示出一种感性体验与理性观念冲突、扭结的含混性。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语言形式的转换,虽不乏外在迫力的无奈,但也有内在的个性化文体意识的自觉。冯雪峰的回忆为我们透露了若干颇有意味的信息。冯雪峰称:鲁迅对瞿秋白文体的评价是“尖锐,明白,‘真有才华’。但他也表示过秋白同志的杂文深刻性不够、少含蓄,第二遍读起来就有‘一览无余’的感觉……”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30页。上述回忆乍看紊乱;细察却清晰可辨,正是因着对政治宣传功能与文学诗性魅力的不同侧重,导致了鲁迅文体要求的矛盾(一定意义上也可视作鲁迅自身形式追求的两难)。
如上所说,鲁迅对《二心集》型语言形式明快畅晓有余、“深刻性不够”之局限并非无所觉察,一度仍不得不用,乃是出于强化政治宣传功能的功利目的。一旦鲁迅颖悟“弄政治宣传,我到底是不行的”,一旦他不愿再被“纯粹利用”、指派为“导师”一类的话语角色之后,潜在的美感定势便自然会引领他重新寻求个性化的深刻言说。
促成鲁迅语言形式转换的因素并不止于上述这些,恰如王晓明所敏感到的,还可追溯到鲁迅晚年的生理、心理因素。
《无法直面的人生》一书突破了单纯社会学的阐释模式,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逼近鲁迅的文体;但作者也不无失察之处,如将《二心集》时期鲁迅“虽然笔锋依旧锐利,抨击依旧有力,但失去了幽默的底衬、气势也就弱了许多”的原因归咎于衰老、疾病,而没有看到这主要是偏执二极对立思维格式所致。更值得商榷的是,作者将鲁迅1934年以后的文体误判为文思枯涩、文气衰竭。参阅《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第228~230页。
为了避免主观臆断,我又一次沉潜于三本“且介亭”杂文集中。自然,由于预设的视角规定,所读主要侧重于承载鲁迅文学思想的那些篇章。从《论“旧形式的采用”》、《拿来主义》到《忆韦素园君》;从《〈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萧红作〈生死场〉序》、《“题未定”草(六至九)》至《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从《〈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写于深夜里》至《〈苏联版画集〉序》、《“这也是生活……”》凝神屏息地读着这一页页生命的“血书”,我不仅没有产生鲁迅文气衰竭的同感;却反而读出了作者生命激情的喷涌:与病魔的切身抗争、与死亡的近距离对视,不仅使鲁迅对生命存在的眷注、对人生意义的思索显得比任何时期都透彻、都紧切——一定程度上驱使鲁迅文艺思想的重心由认识论向人学倾斜;而且使鲁迅文体中的生命感显得比任何时候都凝重、都深沉。
以上分别从鲁迅的政治遭遇、美学个性、生命绝境等角度寻索鲁迅晚年批评文体转换的动因。耐人寻味的是,与鲁迅晚年语言形式的转换恰恰同步,“自1933年以后,他购读的文艺理论和哲学著作的重心已由马克思主义学说转向他早年重视的几位哲人身上。”参阅《现代西方哲学在鲁迅藏书和创作中的反映》(下),《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1期。——感谢姚锡佩先生独辟蹊径,以鲁迅藏书为线索,钩沉考订,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丰厚的实证!它不仅从又一角度印证了鲁迅晚年对苏式文论形式的反拨;而且有力地驳斥了鲁迅后期与尼采思想、尼采文风截然划清界线的臆断。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期,学界在涉及鲁迅与尼采等几位“敏感”的思想家的联系时,每每囿于前期批判吸取、最终抛弃的思维定势;事实上,鲁迅与尼采思想、尼采文体的联系远比某些研究者臆断的要深刻得多。它是“那样地扎根于鲁迅本来的性情和气质上的”,增田涉的体悟解释了,何以当鲁迅有意逸出苏式文体框架的拘束时,阅读重心会重新倾向尼采等西哲著作。与其说这是又一次对“他者话语”的“依附”,不如说是鲁迅试图借助尼采等西哲的提示,寻找、强化与尼采部分契合的“自己”。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论鲁迅对《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的反拨(2)
以下描述鲁迅晚年批评文体的转换并兼及鲁迅对尼采文体的遥感。
“在一切著作中,吾最爱者,惟用血写之著作。”尼采如是说。“血书”者,谓文本中活的感性、意志、直觉的渗透,谓血性的自由的生命的注入。尼采以此作为对一切缺乏生命感的形而上学的挑战。如果滤去尼采美学范畴中血性与理性决然对立的涵义;那么,“血书”恰可用以概括鲁迅晚年批评文体的某种特质。
诚然,鲁迅说过,“尼采爱看血写的书。但我想,血写的文章,怕未必有罢。文章总是墨写的,血写的倒不过是血迹。”但上述引文后鲁迅分明还如是说:“真的血写的书,当然不在此例。”《鲁迅全集》第4卷;第19、20页。恰如胡风所敏感的,鲁迅的文论便是“真的血写的书”。他的著述有一个大的特点,“那就是把‘心’、‘力’完全结合在一起。他笔尖底墨滴里面渗和着他的血液”参阅《胡风论鲁迅》,第8、9页。……
“血书”不仅是鲁迅语言气质的投射,更是他将文学创作、文学批评视作一种生命活动的表征。尽管《二心集》时期,未能内化为生命机能的苏式体系硬壳一度压抑了感性个体的切身体验;但,这只是一时的。鲁迅血性热烈的语言气质、他那与生命合一的文学观终将引领他突破理性硬壳。因而,与其说是此时购读的尼采、克尔凯廓尔等西哲著作中对科学、理性的尖锐否弃态度影响了鲁迅,不如说是突破既定理性硬壳的需求驱使鲁迅将目光投向了尼采、克尔凯廓尔。鲁迅没有一面倒地倾向非理性主义,他对理性不过是一堆僵硬的石头、辩证法不过是贫血的表现一类的偏颇作了“改译”。在鲁迅晚年的文艺思想中,不仅更急切地呼唤创作应成为“血书”:“作者的心血”应与反映的对象“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面前展开”,试图藉血性的情热、体验、直觉消融普洛文学口号理念的僵硬;不仅更集中地呼唤创作应表现生命力之美,自觉非自觉地以生命力的觉醒、激扬、勃发、反抗死亡、虚无、教条等一切对生命的羁束;而且对既定理论作直接闪击。他拒绝再将鲜活的人生诸相生硬地朝某种先行观念中阐引——倘若连吃西瓜也得朝“最中心之主题”提升,这样的“理性”岂非太绝对!他对科学的“普遍有效性”进行质疑——“敢请‘前进’的文学家和‘战斗’的勇士们不要生气”,那个复仇的“女吊”,虽“不合于科学”的知性标尺,但若以文学的情调性感悟度之,难道不比任何概念性的“复仇”更美、更强?
透过以上的描述,依稀可辨,在晚年鲁迅的心灵深处,似乎潜伏着某种“以流血的头撞击绝对理性铁门”的冲动。不是吗?从姚锡佩揭示的鲁迅晚年对舍斯托夫著作的钟情中,隐隐暗示着这一遥感。
与鲁迅晚年文艺思想的“血书”内容相契,他的语言形式也充满了“血书”意蕴。它特别注重独异的个人生命体验,更多地从感性个体的内在感受出发去拥抱对象。以心度心,以血试血。很难想像,倘若不凭藉自身死的抗争、生的挣扎的体验,他能如此简练地略去理性的推导、逻辑的切割,而浑然整体地呈示出沉钟社那“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的艺术精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鲁迅的这一哲思正是由日常场景与感性物象中顿悟;而那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鞭鞭见血的“精神底苦刑”的评述,也正是因着主体的感同身受、因着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两颗巨魂遥感地颤栗,而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理性归纳,俨然“血书”。
如上所述,鲁迅晚年文艺思想、文学批评的基本把握方式——体验是一种综合的近乎直觉的反应能力。与认识方式局部交叉,它也包含了透视力与判断力;然而,因着它与生命存在本身的切近,较之指向身外空间的认识,似更能直接地透视或呼应生命的震颤。
如同鲁迅的体验方式中,并不排除透视力与判断力;他晚年文艺思想、文学批评的基本表达式——情感性言说,也并不意味着摈弃思想。诗性主体投射到现象世界中去的方式每每是情感的方式,细察鲁迅晚年文艺思想的萌生,与其说是理性凝冻的产物,不如说是情感蒸腾的结晶——思想由情感而生发,然后又返回情感。如是呈示纯粹是为了清晰化而不得已采用了“慢镜头”。实质上,鲁迅晚年文艺思想的构成,已分不清什么是情感、什么是思想。它是一种哲理化了的情绪本体;或者说,是一种本能化、感官化了的思想。独异的个人气质、复杂的生命内蕴,使其有别于《二心集》表达式的清浅畅直;而更像是流动着的雄浑凝重的钢水。它奔迸着热烈的激情;凝聚着沉实的独立思考的分量;摈弃了液状的轻浮;也不再有金属的僵硬。它既是理念的“思想性”的沉潜;也意味着对一切“冷评气息”、“零度风格”的反拨。其中最具魅力的,是那种超技艺的、心灵深处最直接的生命涌动。
这种不驯的血性的生命力量,注定会与《二心集》时期所取的苏式体系框架冲突。于是,我们的视点便也自然由对鲁迅晚年语言精神的关注而移至考察它的文体结构。
如果说“血书”可谓鲁迅晚年批评文体之魂;那么,“非体系”则是鲁迅晚年批评文体的结构形式。若是注意到这一结构形式与由体系化转向非体系化的现代西方批评形式演进轨迹的不谋而合;注意到它与尼采、克尔凯廓尔否定构造体系的人生美学立场的相契,那么,我们便不会轻率地将它仅仅归结于鲁迅不擅系统思维这一个性原因,还可能联想到似乎兼有“不屑”这一颇耐人寻味的因素。
鲁迅晚年不再勉力撰写系统、严密的苏式论文以坐实既成观念,而宁取松散、超迈的格言、断想、印象批评体表达自己的情思睿识。这是美感定势的复归,抑或还有形式外的意味?与前期不同,此时中国左翼文坛上毕竟已舶来了大而全的苏式体系宫殿。不像同时代左翼理论家那样引经据典、坐享其成;偏从体系宫殿中走出,借格言、断想、印象批评体以保持自己自由的精神空间。这难道能说是纯属偶然?是的,与其为求一统而牺牲切身的体验,牺牲独立的思考、探索;与其为求“普遍,永久,完全”而滤干思想的血肉,抑制心灵深处的生命涌动,不如拒绝对既定体系的依附,放弃构筑体系的奢愿,而如其本然地将思想播撒于情感链、生命链上。——这便是鲁迅“非体系”选择的动因。
一旦鲁迅从体系宫殿中走出,一旦他更多地借重体验、更多地采取情感性言说的方式,其语言的变换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了。我们可以以诗性一词界定鲁迅晚年文艺思想、文学批评的语言特征。需要强调的是,“诗性”在此决不等同于用美文的辞藻掩饰思想的贫乏,更有别于革命浪漫蒂克式的抒情、煽情。它既是鲁迅晚年那颇具张力的人本主义眷注与科学主义思考的诗美延伸;又可视作他对《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确定、明快特征的语言反拨。
《二心集》语言的明快、确定,一定程度上是以迁就现成的苏式符号系统为代价的。在它看似清晰有序的背后,恰恰隐藏着对不可知区间的回避,对无序因素的含混。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们理解了鲁迅晚年语言形式中那诗性的超常、晦涩、含混。并非如王晓明臆断的因缺乏生命力的润滑油而造成“涩的感觉”;相反,一定意义上正是因着生命力的奔涌不羁,致使鲁迅“不安分”地超越了既定视角,从而面对了一个难于言说——至少不能用现成的苏式文论话语去领会、去表达的领域。在那里,过于普泛的概念只会使对象落入“一般性”的窠臼;过于流畅的倾诉只可能淹没对象的特质。要摆脱流行话语的定势,要使那难以言说的变得可以言说,惟有选择诗性语言。而“诗”之所以不等同于“流行曲”,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力于语言的超常、“越规”。于是,在鲁迅笔下便出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