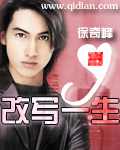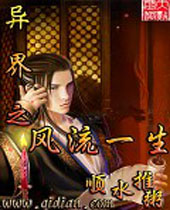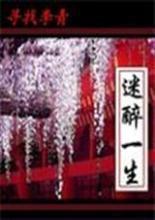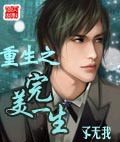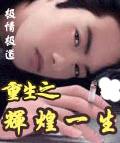一生必须看爱的艺术-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造成病态的爱的根源是“相爱的”一方或双方都顽固地依赖父亲或母亲的形象,并把他以前对父亲或母亲怀有的感情、期待和恐惧在成年后都转移到“爱人”身上。这些人从来没有超越儿童时代,成年后还在寻找童稚的感情要求。在这些情形下,虽然他们在智力和社会交际方面有符合他们的实际年龄的表现,这些人在感情上却始终停留在二岁、五岁或十二岁的阶段。在较为严重的情况下,感情上的这种不成熟状态会导致其社会能力发生障碍;在不那么严重的情况下这一冲突只限于个人亲密关系的范围之内。
回顾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父亲中心人格或母亲中心人格,下面我们所举的经常在生活中出现的病态爱情关系的例子,指的就是男子在感情发育过程中始终停留在婴儿依恋母亲的阶段上。这些男子还没有断奶。他们这些人始终感到自己还是孩子;他们需要母亲的保护、爱、温暖、关怀和夸奖;他们需要母亲无条件的爱;得到这种无条件的爱只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需要这种爱,他们是母亲的孩子,他们弱小无助。这些人在企图赢得一个女子的爱时,或者甚至在他们获得这种爱之后,他们往往和蔼可亲,风度翩翩。但他们同这个女子的关系(实际上同对所有的人的关系一样)都是表面的、肤浅的,而且是不负责任的。他们的目标是被人爱,而不是去爱别人。在这种类型的人身上往往可以看到很强的虚荣心和或多或少隐藏起来的高过云天的想法。如果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女人,他们就会感到信心十足,处在世界之颠;这时他们对其他人也会表现得和蔼可亲,温文尔雅,这也是这些人富于迷惑性的原因。但在过了一段时间,当这个女人不再符合他迷梦般的期望时,就会出现冲突和矛盾。如果他的女人不是始终如一地欣赏他,如果她要求有自己的生活,想得到爱和保护,如果她——在极端的情况下——不打算原谅他有外遇(或者甚至仅仅是不赞赏他们这种外遇行为),这时他就会感到受到深深的伤害和失望。一般来说他还会用“妻子不爱他、自私或者专横”的说法把他的这种感情合理化。任何不符合母亲对娇儿的关爱的些微疏忽,都被看作是缺乏爱的证据。这些男子一般来说把他们的文雅举止和取悦别人的愿望同真正的爱混淆起来,并因此得出他们结论说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自以为是伟大的恋人,并对对方的忘恩负义而大肆抱怨。
只有在少数的情况下一个以母亲为中心的人才能无障碍地正常生活。如果他的母亲是以一种过分保护的方式“爱”他(这种爱可能是专横的,但并不是破坏性),如果他找到了跟这种类型的母亲相似的妻子,如果他拥有奇异的天赋和才能让他可以施展他的魅力并为人所赞赏(有些成功的政治家就是这种情形),那么,他就可以在没有达到更为成熟的水平的情况下成为一种在社会意义上“合作良好”的人。但是,在不那么有利的情形下——这才是更为常见的自然状态——如果没有社会生活的话,他的爱情生活也将大失所望;这种类型的人在独处的时候,冲突矛盾、重重焦虑和厌世都将朝他袭来。
从病理学上说,有一种更为严重的情况,对母亲的眷恋更深,也更加不理性。到这种程度,用象征的意义说,不是回到母亲保护的双臂,也不是回到母亲滋养人的胸膛,而是回到母亲全面接受——也是全面毁坏——的子宫。如果说心智健康的本质是从子宫走出、进入世界,那么严重心理疾病的本质就是被子宫所吸引,向子宫回归——这实际上也就是抛弃生命。这种偏执的眷恋经常发生在那种以吞噬—破坏的方式跟自己的孩子发生联系的母亲对孩子的关系上。有时候以爱的名义,有时候以义务的名义,这些母亲想把孩子、少年以及成人留在自己身体当中。除了通过她们,这些孩子是不应该能够自己呼吸的;也不能去爱,除了在肤浅的性爱的水平——而这是在侮辱所有其他的女性;他不应该有能力去独立自主,而应该永远是一个跛子或罪犯。
母亲的这方面,即破坏、包罗的这方面,是母亲形象消极性的一面。母亲能给生命,也能收回生命。她是接受者,也是破坏者;她能创造爱的奇迹——但是,她也比任何其他人更能伤害爱情。在宗教形象(如印度教中的女神卡莉)中以及梦幻的象征中,母亲的这两个方面的形象都能找得到。
精神病态爱情的另外一种类型可以在偏执的恋父中见到。
与此相关的一个例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有一个冷淡无情的母亲和一个将自己所有的感情和注意力都投入到自己儿子身上的父亲。他是一个“好父亲",但他同样也是专制的。当他对儿子的行为满意时,父亲就表扬儿子,送他礼物,满含深情;当儿子不能使他满意的时候,他就收回他的爱,并对儿子进行斥责。对儿子来说,父亲的爱就是他的所有,因而他也就以一种奴性的方式依恋父亲。他生命中的主要目标就是取悦父亲——当成功地取悦父亲时,他就感到开心、安全、满意。但是,当他做错了事,考试没及格或者没能成功地取悦父亲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受挫,父亲不再爱他了,自己被驱逐了。在以后的生活中,这样一个人就会努力寻找一个他能以类似的方式去依恋的父亲的形象。他的整个生命就变成了一系列的沉浮升降,这些沉浮取决于他是否能够成功地取得父亲的赞赏。这样一类人在他们的社会事业中通常都是非常成功的。他们尽责、可靠、上进——假如他们所选择的父亲形象知道如何对付他们这样类型的人。但是在他们跟女人的关系上,他们冷淡而疏远。对他们来说,女人没有核心的意义;他们通常对女人有一种不明显的蔑视,但是对小女孩父亲般的关照掩饰了这种蔑视。他们阳性品质往往能在开始打动女人,但是他们却逐渐变得令人失望。因为他们的妻子发现,在任何时候,比起那个父亲形象,丈夫对她的感情永远是处在第二位的。情况只能这样,除非这位妻子碰巧也依恋自己的父亲,这样的话,她就会对跟一个将自己当作一个任性的小女孩的丈夫在一起感到幸福。
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神经性障碍疾病。这种类型的病症根源于另外一种类型的父母状况。父母双方彼此并不相爱,但是他们彼此克制,并不争吵,也不公开流露任何不满。同时,距离也让他们在跟孩子的关系中表现得很不自然。小女孩经历的就是一个所谓“正常”的氛围,这个氛围不允许她跟父亲或母亲有亲密的接触,因此这个女孩很困惑,也很害怕。她对父母亲到底想些什么、感觉些什么一点把握都没有;在这种气氛中,始终贯穿着未知与疑惑的因素。结果就是,女孩退回到了她自己的世界,回到白日梦的状态,仍旧疏远;在她以后的爱情生活中,她也保持同样的态度。
第三章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爱及其蜕变(3)
还有,这种退缩导致了一种强烈焦虑的发展,一种在这个世界上并不牢靠的感觉;而且通常会导致将受虐作为惟一的体验强烈兴奋的方式。通常这样的女子更喜欢她的丈夫当众发脾气、咆哮,而不是喜欢她的丈夫保持一种更为正常和理智的行为;因为,她的丈夫这样做至少可以去掉她们身上紧张和恐惧的负担。在有的情况下,她们甚至无意识地挑起丈夫这样的行为,为的是结束那种情感上中立的令人痛苦的悬念。
以下我们将描述病态爱的几种其他较为常见的形式。但是,我们不再分析在他们孩子时代奠定这些行为基础的一些特定因素:
有一种假爱的形式并非少见。这种爱经常被体验者(在电影或小说中,这种爱出现得更为频繁)认为是“伟大的爱”,就是偶像崇拜式的爱。如果一个人没有一种根植于自己创造性力量发挥的自我认同,以及对自我的意识,他通常会趋向于将他所爱的人“偶像化”。他同他自己的力量异化了,将自己的力量投射到所爱的人身上。他将他所爱的人视为所有的善,所有的爱,所有的光,所有的福的化身。在这个过程中,他丧失了对自己所有力量的认识,消失在自己所爱的人里面,而不是发现了自己。既然从长期看没有一个偶像可以不辜负他的(或她的)崇拜者的期望,所以失望注定要发生。作为补偿,接着去寻找另外一个偶像,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无休无止的循环。这种偶像崇拜式的爱情的特征是在其开始之初爱的体验非常强烈、也非常突然。这种偶像崇拜式的爱情也被人描绘为真正的、伟大的爱。但是,虽然人们有意想勾画的这种爱的强度和深度,但是这种勾画只是证明了崇拜者对爱的饥渴与绝望。无须赘言,有不少情况表明,恋爱双方在相互的偶像崇拜中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但是,这种相互之间的偶像崇拜在极端的情况下有时候代表了一种叫做“Folie à deux”(感通)的精神疾病。
假爱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我们称为“伤感之爱”的那种。伤感之爱的本质在于:爱只能在幻想中体验到,在此时此地的现实人物中是无法体会得到的。这种类型的爱最为广泛的形式是由那些观看电视、杂志上的爱情故事以及听爱情歌曲的那些人所体验到的幻想式爱情。所有未被满足的对爱、融合、亲近的欲望都在消费这些娱乐品中找到了满足。一对男女在现实中不能穿透彼此的隔膜,却会被荧屏上的爱情故事的悲欢离合感动得热泪盈眶。对许多夫妇来说,观看荧屏上的爱情故事是体验爱情的惟一机会——不是彼此之间的爱,而是共同地作为别人“爱情”的观察者来体验爱情。只要爱情还是个白日梦,他们就还是会投入到别人的故事中去的;但是,只要回到两个人现实的关系中来,他们的关系立即就会化为寒冰。
伤感之爱的另外一个特点是随时间而出现的爱情的抽象化。一对夫妇可能会被他们往日的爱情回忆所深深打动。但是,即便在当时,他们也没有体会到什么爱情。当然,他们也会被他们未来的爱情幻想所深深打动。有多少订婚的或新婚的夫妇在憧憬着未来爱情的幸福,但现在,他们却已经厌烦了彼此的相处呢?这种趋势实际上是符合现代人的一般态度特征的。他生活在过去或者未来,但就是不生活在现在。他伤感地回忆起他的童年和他的母亲——或者是计划着美好的未来。不管是只能在欣赏小说式的爱情故事中来投入爱情,还是将爱情从现在转移到了过去或未来,爱情的这些抽象和异化的形式都只是起到了鸦片的作用;这些鸦片可以疗救现实的苦痛,减轻个人的疏离感和孤独感。
还有一种神经病态的爱。患者使用投射机制来避免自己的问题,却对爱人的缺点与过失斤斤计较。这种个人的行为方式非常像团体、民族和宗教的行事方式。他们很能识别别人的哪怕很微小的一点缺点,满含喜悦地走在前头,却忘记了自己的问题。他们总是想去指责别人,甚至想去改造别人。如果两个人都是这样的人——情况经常就是这样——两个人之间爱的关系就转化成了相互对立的关系。如果我本人独断,或者优柔寡断,或者贪得无厌,我就会指责对方也是如此;而且,按我的性格,我不是要对方悔改,就是要施以惩罚。对方也同样待我。所以,双方都成功地忽略了自己的问题,因此都没有在促进自己发展的路子上迈进一步。
还有一种投射是将自己的问题投射在孩子身上。首先,这种投射经常发生在对自己孩子的希望上。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发生在对孩子非同寻常的期望。当一个感到他没有能力使自己的生活变的有意义的时候,他就会努力在孩子身上找到生活的意义。但是,这个人注定要在自己和孩子身上双重失败。之所以说在自己身上的努力会失败是因为他自己存在的问题只能由他自己来解决,而不能靠委托自己的孩子而解决;之所以说他在孩子身上会失败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去引导自己的孩子探索生活的答案。在风雨飘摇的婚姻中,孩子也会被当作投射目的而遭殃。不幸婚姻中的双方之所以不愿离婚的主要论据就是说他们不愿意剥夺孩子享受完整家庭的幸福。但是,细致研究的结果表明,这样一种勉强维持的“完整家庭”中的紧张和不幸对孩子的坏处要比离婚大得多——至少离婚可以教给孩子通过勇敢决定来结束无法容忍的状态的一种行为方式。
这里我们还得提到一种人们所经常犯的错误。有一种幻想认为爱就意味着必然没有任何冲突矛盾。就像人们习惯成自然所认为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痛苦与悲伤都应该避免;爱就意味着完全没有冲突矛盾。理由是,他们之间产生的矛盾都一律会导向毁灭,结果对谁都没有好处。但是,大多数人冲突的真正原因是企图避免“真正的”冲突。他们在琐碎事情上表面看意见不一,而这些琐事本身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两人之间的真正冲突并不是破坏性的。真正的冲突不会用来掩盖或投射问题,真正的冲突与矛盾是在他们所属的内在实在的深度上的体验。这种矛盾会导致清晰化,会导致宣泄。而双方都会从中得到更多的了解和力量。这又回到了我们原来所说的话题。
仅仅当两个人从他们存在的中心进行沟通的时候,仅仅当他们从自己存在的中心体验自己的时候,爱才是可能的。人的实在,人的生命力,爱的基础都只存在于这种“中心体验”。这样体验的爱是一种持久的挑战;它并不是一个休息的场所,而是一起运动,一起成长,一起工作。相对于两个人从存在的本质体验他们自己,相对于他们彼此为一、而不是彼此拒斥的情形来说,所谓和谐还是冲突,欢乐还是悲伤等问题都退居其次了。是否有爱只有一个尺度:两个人关系的深度,两个人生命力以及力量的深度;通过这些爱情的果实我们自能辨认出是否有爱。
就像机器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