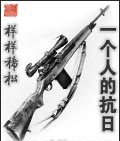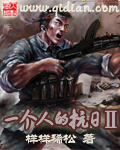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董事长为胡适,总编辑为徐志摩,总经理为张嘉铸(徐前妻之兄)主管财务和发行工作。人们应该注意到,徐志摩是哥伦比亚经济学硕士,正好运用他训练有素的经济头脑。
创造社、新月社等民办文化企业到位的资金并不太多,但是由于新式印刷设备在上海大量引进,民间又兴办了许多小型专业印刷车间,为招揽生意,普遍实行“三节算帐制度”。中国民间所谓三节是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两个大节日之间有三四个月的周期;一个大节以后印制出版的图书,除了交付少量押金以外,作为成本的排版、纸张、印制、装订等费用,都由印刷厂垫付,到下一个大节再结帐。这样只要较少的流动资金,便能出版书刊。
因此,20年代在上海的各种短期文学刊物、小型民办书店、民办出版社如雨后春笋,造成文化事业的欣欣向荣。这样,初步摆脱了官府权势和商业羁绊的新兴知识阶层,投入了文化自由市场。这种趋势,如“一石击破水底天”一样,层层波澜由上海开始一圈又一圈扩充到许多城镇,迅速而又强有力地推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柔石——中国左翼自由撰稿人的典型
中国现代文化的自由撰稿人的历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血泪史。他们的征途上充满了荆棘——鲁迅所说的“无花的蔷薇”,为新文化事业献出了青春、鲜血甚至生命。这些文学青年的卓越代表之一,是柔石。
近几年发现和公布的烈士遗迹——《柔石日记》和《柔石书信》,以及许多前辈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柔石的最新史料。我试图整理和分析这些确切的第一手史料,描述以柔石为代表的我国现代文学第一批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生活状况。跟他同类的左翼文学青年,有丁玲、胡也频、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叶紫、殷夫、沙汀、艾芜、萧军、萧红等。
柔石姓赵名平福,后改名平复。1902年9月生于浙江省宁海县市门头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原为农民,后做小生意,开一经营鲜咸海货的店铺“赵源泉号”。因家境困难,赵平复十岁时才开始读书。1917年夏,赵平复从宁海县正学小学毕业。秋天就学于台州浙江省立第六中学,中途退学自修。1918年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免学费,食宿便宜,同学多为贫苦子弟。1920年因父亲之命与吴素英结婚。次年5月生育大儿,不到二岁时因病夭折。1921年5月发起组织了“宁海同学旅杭同学会”,1922年左右在杭州第一师范结识低班同学潘漠华、冯雪峰(赵为四年级生、冯为一年级生),并参加青年文学团体杭州晨光社。
1923年他从杭州第一师范毕业,本想升学,7月到南京报考东南大学,但需学费六十银洋(合今人民币2千4百元)不能减免,终因家境困难而未入学。9月应聘到杭州留法博士应溥泉家,为两个小孩担任家庭教师,报酬未见记载。到1924年春,又想帮助妻子读书,不得已就在慈溪县普迪小学做教师。当时一般初任小学教员的月薪为30-40银洋(合今人民币1千2百-1千6百元)。当年得一子取名帝江。在这期间他写了一部小说《疯人》于1925年元旦在宁波自费出版,准备卖书回收钱款,但不能如愿。
1924-25年间他因爱好文学,购买图书报刊,花费很大。不得已帮助经营父亲的“赵源泉号”,想增加一点收入;但经营不善,负债达一百几十银洋(见《柔石日记》第152页)
1925年2月中,柔石到北京大学旁听哲学、英文二科,也旁听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程。由父母寄钱给他(一说由大哥寄给他2百银洋,参看赵文雄《回忆我的哥哥柔石》),与好友潘漠华同住在北大红楼附近的学生公寓孟家大院通和公寓(柔石致陈昌标信),每月食宿费约20-30圆,购书的钱至少10圆。北京大学于2月22日开学,柔石听课一学期。9月收到父亲的信,希望他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可以减免学费食宿费,继续学业。柔石回信说:“复岂不愿读书,实以家中之故,六年长期,断难遂愿而毕!”(载《柔石日记》第141页)
熬到1925年12月中旬,他终于因病而且财力不济而离开北京回乡(现存柔石12月4日从北京寄出的信)。
1926年春夏之间柔石为谋生而奔走于沪杭道上,曾计划在杭州创办一所私立中学,拟找十友人(王方仁等)集资开办费1千银圆(合今人民币3万5千元),每人出资1百银圆,但未成功。秋天回乡养病,当年得一女取名小薇。12月去上海,一无所获。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三部分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3)
1927年1月回家过春节,不久因朋友王方仁介绍,到镇海中学任教。春天,北伐军到达杭州,浙江省全部光复,柔石回到宁海担任中学教员,不久升任宁海县教育局长,同时每周到宁海中学兼课。收入不详。
1927年3月由父母决定,将家产分给赵平西、赵平复兄弟二人。兄长继承父亲开设的“赵源泉号”,平复分得5百银洋(约合今人民币1万7千5百元)作为股金存入该号(引自《柔石日记》第45页注,第168页注)。柔石当时没有支取现金,但从此可以向兄长要求经济援助。
1928年5月初宁海农民起义失败,涉及宁海中学师生。柔石单身出走,逃到上海,借住在闸北一个亲戚家里。夏天他写信给老家,说是正在学习德文,想出国留学,希望父母扶持。 父母将他存放在咸货店的5百银圆寄给他。不久,柔石又写信给老家,如果要出国留学的话,5百银圆还不够盘缠(几乎同时的李金发、艾青等人出国去巴黎工读,至少要准备1千银圆,合今人民币3万5千元),没有办法,只能望洋兴叹,圆不了去德国的美梦了。柔石在通信中说:“眼前到外国去,钱从何处来,外国最少一年要一千圆用,来回路费每次要二百。……到外国去的心,等一两年再谈了。”(参看《柔石日记》第152页)
[附录]“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
——20年代留法半工半读的生活
1919年,岁的李金发从上海乘船到法国勤工俭学,准备300块大洋(银圆)置装费和旅费。乘坐的是英国货轮统舱,条件恶劣,每人收费100银圆。
到法国后进入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市立中学攻读法文,每月学费100法郎(合10块银圆或国币),同学有林凤眠等;后来在巴黎学习雕塑。一间简陋的房子月租150法郎(合10圆国币);一顿比较好的中餐5法郎(合5角钱)。1920年开始写诗,将《微雨》《食客与凶年》寄回国内。
1929年春,岁的艾青(当时名蒋海澄)从父亲那里得到一千块银圆,从上海乘坐法国邮船(三等舱),经过一个多月的旅程,到巴黎学习美术。同行的有杭州国立艺术院水彩画教师孙福熙和他的哥哥孙伏园等。蒋海澄在巴黎第六区伏斯拉尔大街里斯本旅社租了一个小房间,因为室内有一个下水管道,所以房租便宜得很,每月50法郎。(这个旅社到1982年还在,参看《艾青谈诗》214-215页)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三部分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4)
他找到一家美国老板开办的工艺作坊,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每天上午做工,下午学后期印象派的绘画。他的工作是用中国漆把买主的签名描绘在打火机或香烟盒上,一上午可以描绘20个签名,收入20法郎。
在巴黎餐馆一顿普通的饭要付5法郎。为了节省,他去学生食堂就餐,一张饭票只要3法郎。这位穷留学生对朋友却很慷慨。他跟李又然在学生食堂初次认识的时候,看李付不起饭费,就一次送给李10张饭票外加50法郎。(引自李又然《诗人艾青》一文。)
丁玲的经济生活
丁玲原名蒋冰之,1904年10月12日生于湖南省临澧县,长于常德县。她属于一个传统的封建门第,大家族院墙里有二百多间房屋。但是父亲死后,家道衰落。母亲守寡。1911年春,常德女子师范开学,母亲进入师范班,7岁的女儿跟着进了幼稚班。次年,母亲又带她去稻田第一女子师范念小学一年级。
1918年夏季,13足岁的蒋冰之小学毕业,考入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入学后,食宿费、学杂费、书籍文具费都由政府供给,只需要预付10银圆做保证金。母亲用一个金戒指代替了保证金。此外蒋冰之还领取3块银圆作为零用,她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多的钱,就一直把银圆藏在衣箱底下,只有放假回家时才取出几角钱作为路费。
母亲担任小学教员,负担女儿的日常费用。据说在很长时间内,每月寄给丁玲20银圆。
1921年她到上海进平民女校,次年转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然后用20银圆作为旅费,乘坐火车来到北京。
丁玲在北京认识了胡也频(1903年生于福州)、沈从文(1902年生于湖南)和冯雪峰(190年生于浙江)等。这几个人的恩恩怨怨,后来一直成为文学史上的话题,引起了无穷的回味。
1925年秋天,21岁的丁玲跟22岁的胡也频,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下一个农村同居。丁玲后来回忆说,她曾经花费7块银圆买了两段棉布、两斤棉花,亲手替胡也频缝制了一件新棉袍。但是做得嫌小了,只好送到当铺换了4块钱,重又买1块钱新棉花,拆开胡也频的一件旧夹袍塞进棉花,缝补以后,凑合着熬过了一个寒冬。有次他们身边只剩下1块银圆,正好来了客人,就用这1块银圆办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第二天丁玲、胡也频两手空空地步行40里路,进城里找朋友借钱。
1926-1927年间,胡也频和丁玲担任《民众文艺》等刊物的编辑。他们这些“文学青年”只想要每月挣得20-30圆的稿酬。就连这样的初步目标也难以实现。丁玲回忆说:当时困处北平,只有在《晨报》《现代评论》上发表一些小文章,得到6、7块钱稿费,加上母亲每月寄给她的20圆,维持生活。在很冷的天气,只好经常在外面晒太阳取暖,只到了晚上才生一次火炉。几乎每天吃面条白菜。
丁玲说胡也频喜欢进当铺。他没有钱,但花钱却很大方,先后把丁玲母亲送的绸衣、棉袍,亲友送的银质餐具,都拿去当了。……
丁玲回忆说:“大革命失败后(1927下半年)上海文坛反倒热闹起来了。各种派别的文化人都聚集在这里,我正开始发表文章,也搬到了上海。原来我对创造社的人也是十分崇敬的,1922年我初到上海,曾和几个朋友以朝圣的心情找到民厚里,拜见了郭沫若先生……1926年我回湖南,路过上海,又特意跑到北四川路购买了一张创造社发行的股票。虽然只花了5圆,但对我来说已是相当可观的数目了。”(参看《鲁迅先生于我》一文)
1928年丁玲、胡也频在杭州西湖住了一个短时期。出了《阿毛姑娘》得到70圆稿费,又回到上海。生活拮据,只能暂住月租金8圆的亭子间。胡也频的老家还要求他给家中弟弟每月20圆接济(付了三个月,实在无法继续,就停止了。)
不久,因为沈从文的关系,沈、胡、丁三人联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每月编辑费共有2百圆,各分得70圆左右,另外还有稿酬。三人共同租赁上海市萨坡赛路(今淡水路)204号楼房,丁玲接来母亲住2楼,沈从文及其母、妹住3楼。各自支付月租金20圆,水电费10圆,加上伙食、衣物,每月开支1百圆左右。除了办刊物外,他们几乎将所有的时间用于写作。
为《中央日报》副刊编辑了两三个月以后,丁玲说:“也想模仿当时上海的小出版社,自己搞出版工作。小本生意,只图维持生活,兼能出点好书。这时正好也频父亲来上海,答应设法帮我们转借一千圆,每月三分利息。”(引自丁玲回忆录《胡也频》一文)就于1929年1月筹办红黑出版社。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三部分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5)
但最初与胡也频一起编《红黑》月刊的沈从文回忆说:“我记不起也频有回福建去筹款的事;我还听说,是丁玲的妈妈给的钱。”不过,实际上这时丁玲的母亲已经失去工作、很少收入,无法再接济他们了。所以丁玲本人的回忆可能是真实的。
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借款一千圆来创办《红黑》月刊和红黑出版社,终以失败而告终。《红黑》月刊于1929年7月10日出版了第7期以后停刊,胡也频于秋季离开上海,到济南市的山东省立高中教书。又因在学校中宣传革命,被通缉。于1930年夏天[据丁玲回忆是5月]胡也频、丁玲夫妇经青岛乘船逃亡上海。
丁玲回忆说:“红黑出版社存在的半年多里,出版过6期月刊,7本书。……出版社关门后,剩下的事便是还债。沈从文给了三百来圆,也频把在山东教书的工资拿了出来,还缺三百五十圆,最后由我向母亲要了来,才把本利一并还清。”不久,丁玲、胡也频参加左联,认识鲁迅,进入30年代。
大学生的文艺刊物
1933年初,在沙滩北京大学文学院,诞生了一个小型文学旬刊《牧野》。说它小,一是它的开本小,是小32开,每期16页,一大张白报纸正好印一份。二是它的印数少,每期印500份。三是定价低,每份2分钱。四是它的编辑和撰稿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这个刊物可以算是他们进行文学笔耕的一小片处女地,共出12期。后来,他们成了我国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