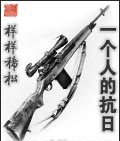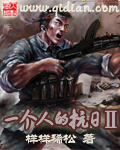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齐如山回忆中所说的“当十钱”也就是光绪二十三年间“当十”铜币,每枚贬值为相当于“制钱”两文(两钱重)。也就是说,“当十钱”98枚相当于“制钱”二百枚,即两吊。又据《中国货币史》第843页,光绪二十三年(1897)白银一两合制钱1364文,合银洋约1。4圆,这就是说,当时银洋1圆折合制钱大约1千文,又可兑换新式的“当十铜元”1百枚。当十钱两吊,合铜元20枚,相当于今人民币14元。(后来,银价上涨,铜钱又逐年贬值。)根据齐如山先生的回忆,同文馆学生四个人聚餐小酌,一桌子简单的打卤面酒水总共只花了铜元20枚、即银圆2角,折合今人民币14元。而他每月的生活津贴可达10块银圆(7两),折合今人民币700元左右。由此可见当时同文馆学生的经济生活水平。
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在洋务学堂的生活
关于19世纪末年的情况,周作人在回忆录中写道——
先君虽未曾研究所谓西学,而意见甚为通达,尝谓先母曰,“我们有四个儿子,我想将来可以将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留学。”这个说话,总之是在癸已至丙申(1893…1896)之间,可以说是很有远见了。那时人家子弟第一总是读书赶考,希望做官;看看这个做不到,不得已而思其次,也是学幕做师爷;又其次是进钱店与当铺,而普通的工商业不与焉,至于到外国去进学堂,更是没有想到的事了。先君去世以后,儿子们要谋职业,先母便陆续让他们出去,不但去进洋学堂,简直搞那当兵的勾当,无怪族人们要冷笑。……
鲁迅原名周樟寿,号豫才。戊戌(1898)年鲁迅十八岁,要往南京去进学堂,不便使用原名,故改名为周树人。那时全国实行科举制度,读书人从小在“私塾”、“家馆”熟读《四书》《五经》,练习八股文和试帖诗,辛苦应试,侥幸取得秀才、举人的头衔,以提高社会地位。所谓“出路”就是读书做官。传统教育主要是“州学”“府学”“县学”以及“书院”;新式的洋务学堂寥寥无几,只有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武昌的自强学堂、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和陆师学堂、福州的福建船政学堂等处,都是官费供给。
周豫才想出外求学,家里却出不起钱,只能进公费的洋务学堂。正好来了个机会,南京水师学堂有一位本家叔祖,在那里当“管轮堂”监督(即轮机科舍监)。周豫才到南京去投奔他,暂住在他的后房。可是这位监督有点顽固,他虽然以举人资格担任了这个差使,但总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因此就给他改了名字树人,出于“百年树人”的典故。后来他从水师学堂退学,改入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仍用“周树人”这个名字。
周树人于戊戌(1898)年闰三月经过杭州往南京,十七日到达,目的是进江南水师学堂。四月中考取了试读生,三个月后正式补了三班。据《朝花夕拾》上所说,每月可得津贴银二两,叫做“赡银”。水师学堂系用英文教授,需要九年才得毕业,前后分作三段,称为三班,每三年升一级,由二班以至头班。周树人在那里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来,“现在是发现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
这就是说,周树人18岁时,即戊戌变法(1898)以后不久,往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除了学宿费全免以外,每月可得津贴“赡银”二两,约合今人民币200元。这比首都的京师大学堂或同文馆待遇要低一些。
1901年,周作人也步大哥的后尘,经杭州往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他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是这样叙述的——
各班学生除膳宿、衣靴、书籍仪器,悉由公家供给外,每月各给津贴,称为赡银。副额是起码的一级,月给银一两,照例折发银洋1圆加制钱361文。我自(阴历)九月初一日进堂上课,至(阴历)十二月十三挂牌准补副额,凡12人,逐成为正式学生。洋汉功课照常进行,兵操打靶等,则等到了次年壬寅(1902)年三月,发下操衣马靴来,这才开始我这里说“洋汉功课”,用的系是原来的术语。因为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洋文汉文两大类,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课,一天上汉文课。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课程,以至驾驶管轮各该专门知识,因为都用的是英文,所以总名如此。各班由一个教习专任,从早上8时到午后4时,接连五天。汉文则另行分班,也由各教习专教一班,不过每周只有一天,就要省力得多了。就那里计算,校内教习计洋文6人,汉文4人,兵操体操各1人,学生总数说不清,大概是在100至120人之间吧。
周作人15岁进江南水师学堂的时候,除学宿费全免以外,起初每月只得最低的津贴“赡银”一两,约合今人民币100元。这比他长兄当年的待遇又低一半。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一部分启蒙的起点:清末洋务学堂(4)
洋务派学堂的规模和局限
西文、西艺两类新式学堂,是为“洋务运动”的政治服务;专业设置狭窄,思想没有解放。仅仅为了大清帝国外交的实用目的,而学习外国语;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富国强兵”的实用目的,而进行军事和技术的职业教育。这就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即使规模较大的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今外交部)于1862年创设的京师同文馆,在1866年以前也只限于学习英、法、俄、等外国语课程。1866年后才附加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课程,然而水平不高,学员的兴趣也不大;成就与影响甚微。
这些都属于“洋务派”的实用专科学堂,尚缺乏现代化的文、史、哲、政、法等社会人文科学的先进观念,也缺乏现代化的数、理、化、生物、地学等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系统方法。但它们毕竟成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启蒙运动的起点,揭开了我国现代化的扉页,尽管还仅是脆弱的一页。
梁启超对于官立洋务学堂的洋教习,曾指出:“半属无赖之工匠,不学之教士”,训练出来的学生“未尝有非常之才,以效用于天下”,至多“仅为洋人广蓄买办之才”而已。
梁启超认为:“国家岁费巨万之帑,而养无量数至粗极陋之西人”乃是“数十年来变法之所以无效”的原因之一。(引自梁启超《学校余论》及《论师范》,《饮冰室合集》第一册。)
当时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人丁韪良说,京师同文馆的名气很大,总教习的官衔也不小,但初期学生只有十个人,都是满族大臣的子弟,好像几只调皮贪玩的小猫,外国教习真有点儿不想教不去,不过是混混日子,捞一笔可观的俸银。
当然,同文馆并非一事无成,它曾为洋务派所办的机构,输送了一批外文翻译和官吏。而洋务派后来的要员,如户部尚书董恂、刑部尚书谭廷襄等,乃是同文馆毕业生。此外,同文馆的“译员班”在三十年间陆续地翻译出版了二十余种书籍,介绍了一些西学知识。
但是“西学”的历程,进步极其迟缓。据统计,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1868年创立到1897年,三十年间仅售出各类译著13000部(参看梁启超《戊戍政变记》,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卷一,第22页),平均每年不过400部,分到全国,大约每五县才有一本“西书”。对照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的1866年,仅福泽谕吉译著的《西洋事情》一书,刚出版就销售达25万册。老大中华帝国对于西学的引进,比之日本,相差何止百倍?
1895年甲午战败后,丧权辱国被迫签约,满清朝廷向日本帝国的赔款和赎金白银 2。3 万万两,年利5厘,规定3年还清。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更蒙受奇耻大辱,满清朝廷又欠八国“庚子赔款”连本带息9万万多两白银,预期限39年还清;而当时的满清政府每年财政总收入为 0。8 万万两白银。也就是说:甲午战争的赔款赎金为清朝每年财政总收入的3倍,而“庚子赔款”为清朝每年财政总收入的11倍!从此,“大清国”丧了元气,洋务派也一蹶不振。维新派奋起,严复呼吁救亡,而救亡必须启蒙。从救亡启蒙运动中,一些觉悟的“文人”成长为我国第一批“文化人”。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一部分清末四所大学的状况(1)
(二)清末四所大学的状况
甲午战争的惨败,证实了洋务派的无能和腐朽;也促成了维新派的崛起。我国“文化人”应运而生,登上社会舞台,并在教育事业方面打开了新的局面,带来了启蒙的生机。
鲁迅在《重三感旧——1933年忆光绪朝末》一文中说——
我想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这恐怕并不是“骸骨的迷恋”。……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新党”。甲午战败,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但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看《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的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现在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丛书”出现,就如目下的《描写字典》《基本英语》一样,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他托缪荃孙代做的《书目答问》也竭力添进各种译本去,可见这“维新”风潮之烈了。……
“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
鲁迅所赞美的清末变法维新的“老新党”们,也就是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代“文化人”。他们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爱国思想的激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实际利益的需要。
19世纪末,在我国创办的最早的大学有:圣约翰书院大学部、天津北洋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上院、京师大学堂。
甲午战后中国的“西文热”
接受西学必须以外语为先导。梁启超在《时务报》第42册上发表《大同译书局叙例》说:
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天下识时之士,日日论变法……今不速译书,
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
维新派和有识之士创办了大同译书局、中东翻译局等机构,译述、介绍西方书籍以推进维新运动,或代人翻译中外往来函件以适应社会需要。
此外,当时中国已有几十家报社,其中规模较大者如《申报》(1872年创办)《字林西报》(1882年创办)《新闻报》(1893年创办);特别是以梁启超为主笔的上海《时务报》(1896年创办)和以严复为主笔的天津《国闻报》(1897年创办),成了维新派的南北两大舆论阵地。它们通常需要聘请英文、法文、日文三种翻译人员,以摘译外文报纸上的文章和时新消息。“西学”的兴起,开风气之先,促进了国人学习外语的热潮。
1895年后,由于深受甲午战争刺激,京师和各大通商口岸,创办了一批仿照外国学制的新式学校;同时,各地对旧书院加以改造,增添“西学”内容。这些新式学校和被改造的书院,中西并重,一些规格较高的学校,如南洋公学,规定招生条件是:
学以中学成才,兼通西学、西文为上;以中学成才略通西学、不通西文,或略通西文、不通西学为次, 中学未成者虽通西学、西文不录。(引自《申报》1897年3月2日《太常寺少堂盛招考师范学生示》一文)
另一方面,从中外贸易经商和实业的角度看来,通洋文“始能为洋行买办,始能赴洋行写货。与西人交易,每岁所入,或数万、或数千数百,以视中国为商则奚啻天壤,此人之所以欲习西国之语言文字也。”从功名利禄的角度看来,过去“十年寒窗、白首穷经”的士大夫阶级发出感叹:“若中学则须老成宿儒、品学兼优之辈,而每月修金不过十余圆”,但是一些懂西文的学生,刚刚毕业,其薪金待遇就“少则十余圆,多则数十圆。当世之鲜衣华服、乘舆策马者,无不从洋务中来,其在官场,则翻译焉、随员焉。”(以上引自《申报》1896年12月29日《论习西学当以工艺为急务》一文)
甲午战后,外国在华企业骤然增加,急需大量翻译、买办。同时来华游历的外国人士较多,也需要华人翻译作向导。为此,在中国的洋人通过各种渠道,招聘懂外语的华人为他们服务,甚至有些驻华外国使馆直接出面、代本国旅华人士招聘华人翻译。例如,1898年11月10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在《中外日报》上登载《聘请上等英文翻译》的广告:“今有英人三位,由上海至云南,计应行半年有余,取道四川成都,仍回上海,愿请能说官话之翻译一位,偕同前往。诸君乐偕行者,乞于日内移至上海大英国总领事署面商一切。”
当时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和各通商口岸,特别是外国租界地区,除了进入官场和个人经商外,当洋行买办或以其他方式替外人服务,是致富的重要途径。
这种形势,也促进了西学的引进和传播。
“圣约翰”——从书院到大学
从19世纪后半期以来,欧美各类教会团体在中国设立了许多教育机构,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和专科学校等等,统称为“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一个差会独家经营的,东吴大学是美国监理会独办的。所谓差会(Mission)是西方国家负责集资、派遣人员到国外传教布道的机构。由差会派遣的人员,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如传教的牧师,医院的医生、护士、学校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