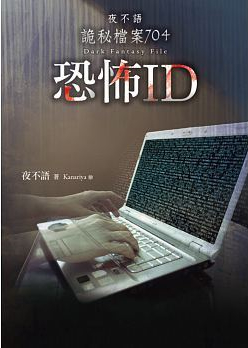2204-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或豪放,或娓娓道来,当其出自真心,即本色。
基蒂·凯利《南希外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回忆的片断,欲望的火焰,痛苦时的迷失、愤怒、豪叫
在纸媒上有可能直接吸引眼球的,简单就是“秘密”二字。因此人物传记中若无独家爆料几乎难于成篇——当然,读者允许那些形形色色、千姿百态、五颜六色的“秘密”内容质地各不相同。
美国著名记者索尔滋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到延安时期因为生活艰苦工作繁忙,毛泽东严重便秘。这个消息当时延安上下都知道。很多细心的人想方设法为主席想办法、找偏方。情况少有改善,窑洞内外顿时雀跃口耳相传:主席通便了!
如此“秘密”放在一个有关重大事件的“传记”中,读来令人倍感亲切。
在书中,索氏甚至写到了毛泽东的初恋。这段“初恋”国内两个译本译笔稍有差异。一个译本将其译作“就在这一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时有了自己的恋人——杨开慧”;而另一个译本则译为“这一年,他一手拥抱了马克思,一手拥抱了杨开慧”……两个译句以虚实不同的风格传播出一个领袖的青春秘密。如此秘密让一个已被尊奉为神的领袖忽然血肉迸现。
《长征》,或说索氏的“揭示秘密法”让人明白,对几乎所有人性的提示而言,秘密就是力量。换言之,健康的隐私就是力量!而所谓不仅“隐私”,还要“健康”,我的理解是它应该有助于揭示人性,而不是展览无聊。
人物传记难道不写人么?偏巧有些字字句句都在写着一个人生平事迹的人物传记就是不是“人”的传记。简单说,它像一页中学生的期末操行评语?它像一款求职者的个人简历?它像一本事无巨细、拣到篮里就是菜的流水豆腐帐?
其实,在那类仿佛“照相写实主义”的罗列中,丢掉个把细节并非硬伤。重要的,是人物传记中那种铺陈简历式的一一还原,看似丰富多彩,实则一地鸡毛。它忽略了传主的灵魂,磨蚀了传主本真的人性……对于一本人物传记而言,这是致命的拣芝麻、丢西瓜。
《杜拉斯传》(漓江版)的写作亦远离如此窠臼。作者的立传法,是希望从传主的作品中剥离出一个“真人”的故事——因为杜拉斯喜欢在自己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反复描写自己生活的某一片段——如此事实为还原的努力提供了可能。 “回忆的片断,欲望的火焰,痛苦时的迷失、愤怒、豪叫、等待和沉默,在杜拉斯笔下都可以成为一本书不容置疑的源泉和内容。作品和生活是一种奇遇的两张面孔。在奇遇中,生活认可作品,作品也认可生活……”(P1)。
套用“作品和生活是一种奇遇的两张面孔”这样的断语,其实,传记和传主也是一种奇遇的两张面孔。当传主融入传记、传记还原传主的情形诞生,除去是一种奇遇外,还算是一种奇迹吧?
统领秘密或者隐私的,会是某种理念。而辛苦也在所难免。挖掘秘密的宝藏,上下其手,颠沛风尘自是家常便饭。
《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的自由撰稿人基蒂·凯利在七次写信给里根夫人南希均未获答复后,在遍访南希的朋友、熟人、亲戚、同学、演员同事、邻居、雇员后,在累计电话采访达1002次之后,才敢落笔写出《南希外传》的第一段:“在南希·里根的出生证明里,只有两项是正确的——性别和肤色。其他各项几乎全是编造的。实际上,这份出生证明本身就制造了两代人的谎言。”(P1)。
几米《地下铁》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因天真而受伤,因受伤而忧郁,因忧郁而恍惚
很多年前,我常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看到署名几米的插图。那时的“几米插图”跟后来大红大紫的几米很不一样——那时的几米画的插图都是一些有身体有四肢、有头颅但没五官的怪家伙。
后来,就像大家都已经看到的那样,几米在生了一场大病后,开始放弃插图作业,改画自己的“绘本”。在我看来,在几米绘本的品质构成中,其最重要的元素为“天真”。他笔下的人物因皆因天真而受伤,因受伤而忧郁,因忧郁而恍惚——《向左转,向右转》中的那对孤男寡女,正是被赋予了“天真”属性两个符号。街心花园水池边那个短暂的浪漫给他们彼此留下永远的伤逝。那伤逝之愉有如一种美丽的灼痛,从反向强化着他们的“天真”……读几米的时候,我老是想起画家冷冰川为天真说过的一个定义,他说:“天真就是希望雨落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怎么会?
于是,几米绘本中所呈现出来的“天真”已成为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里的稀有物——现在不是天真的太多,而是相反——聪明人太多了——你想想看,整天熙熙攘攘结队而来的,尽是一帮从头到脚聪明得一塌糊涂的家伙,这个世界可爱?
也正因为如此,几米绘本中的“天真”已成为这个过于亢奋、过于机警、过于聒噪、过于沸反盈天的城市生活的一种补偿——一种优雅的催眠剂——在《地下铁》那位在幻觉中行走的小姑娘的身上,人们或许会重睹失去的天真?我又不敢说。
第二部分 《不过如此》第21节 《牛棚日记》
中央党校出版社
真实的记住,要郑重,要沉郁
在本书里,季羡林顺手写到“文革”诸事,但它依旧不能算是“文革回忆录”——因为其叙述中心不是“文革”,是“我”。其中,作者试图抵抗的遗忘、试图打捞的记忆事实上并未超出一个耄耋长者晚年信手拈来、漫记琐事的范畴——这样的“漫忆”对于“文革”这样的历史性灾难而言,虽聊胜于无,但未免太轻。太轻!你知道。
而更郑重也更沉郁的记录和书写又相当稀少。少。如《100个人的十年》。面对“文革”这样的巨大灾难,我期望看到更多沉郁与郑重。
足本《100个人的十年》一书中新增加冯骥才“终结文革”一文。冯说:“终结文革的方式,惟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冯所谓“真实的记住”,即郑重,即沉郁。
蒋原伦《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
中央编译出版社
面对一丝不挂,我们有话要说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所采取用的叙事策略一是通吃,一是泛化。“通吃”的意思是说,在麦氏看来,一切均为媒介——从开吉普的张艺谋,到拍摄艳照的章子怡,从刊载“反盗版声明”的余秋雨,到出版“西行25度”的潘石屹,无一幸免。而“泛化”之意则为麦氏所一直强调的所谓媒介即信息——从吉普,到艳照,从手表、汽车、手机,到个人网站…
…麦氏的这一理论事实上相当抽象,蒋原伦新著《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即以对麦氏理论的阐释为开篇:“由于媒介是人们与外界打交道的惟一渠道,因此不同的媒介可以看成是人体的不同感官的延伸,而媒介的方式决定了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有什么样的媒介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模式,所以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深刻影响的是媒介的构成方式而不是媒介所承载的信息”……
蒋扼要、平易的阐释多少化简了麦氏理论的抽象。而当这两种意见扭结到一起后,我们开始拥有重新审视周边信息环境的一个新视角:恍然之间,我似乎看见名导冯小刚已站至信息之颠的“天安门”城楼。面对俯视中万千大众“我们要看贺岁片我们要看贺岁片”的震地之呼,他说了一句经典台词:人民万岁!而这时恰在广场西侧六部口一带遛弯儿的小崔正想心事。他对广场上发生的一切略知一二,却并不详尽。他随口咕哝了几句。尽管那几句咕哝旋即被放大到媒体,成为无数头条上的“炮轰”,但被无垠喧嚣误解、迅速淹没,依旧是它的命运……在如上被我虚拟而成的这个幻觉中,广场、城楼、人群、欢呼、咕哝、冯、崔等等均为信息之外,那番运动般的喧嚣其实也是媒介。而有关后者,在阅读蒋之新作前,我们并不明了。此前,关于媒介或信息,我们的观念还停留在一张报或一篇文、一个电视栏目或一首主题歌……至于阅读与观赏间化学反应般的互动乃至由此引发两伊战争般的无穷混乱,除了把人搞晕,所剩仅止困惑——甚至在那些知识精英看来,一个专讲男人乱搞女人撒泼的商业片票房高达5000万,令人垂涎之外,也是百思不解。
显而,但不易见。由冯小刚一手制造的“贺岁片神话”远非“票房神话”、“喜剧神话”简单相加那么简单。如果仔细推敲,它其实是由“消解神话”(王朔遗风)、明星神话(葛优+×女星)、自我神话(离婚+再婚+对前妻的悔过=新好男人)、投资神话(在国产影片普遍缺少投资的语境中,冯是一个异数)等诸多神话联袂而成的一个“超级神话”——在这个超级神话中,每一细部的“神话”间相互衔接、纠缠、重叠,错综复杂,一个普通观众乃至知识精英要将这一切搞清楚,自然难上加难。与之相似,事实上正如张艺谋的“大片神话”绝非“巩俐神话”那么简单一样,“潘石屹神话”亦非“穷小子梦想成真”老故事那么笔直。
同理,“余秋雨神话”哪里就是“一个文化人勤劳致富”一句话就能解释清?而“章子怡神话”也并非用“谋女郎”或“神似巩俐”之类便可了结……
因此,“百思不解”的真正原因在于,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尤其面对此起彼伏诸多“流行神话”,与之相应的理论建设其实一直荒芜。也正是在这一情境中,蒋之新著尤显宝贵。它提示出,一个针对繁多“流行神话”而展开的“基建”工程已然“开工”。与近年间开始成为热门选题的诸多引进版“大传”专著比,蒋之新著立足本土经验,本土语境,更扎实,更中国,也更当下,宛如那种一镐一锹的“基建”……而如此“基建”其实也是“拓荒”。
在当下以“神话”为基本元素构建而成的日常生活中,“摆脱神话”已是最大的神话。为此,一镐一锹的扎实远比“全盘照搬”或“视而不见”更接近破解神话。以是观之,崔永元式“嘀嘀咕咕”的“文艺批评”基本没什么用,甚至只是适得其反。而沿着蒋原伦的“镐”
起“锹”落,冯小刚乃至其贺岁片神话的底牌倒有可能水落石出。
在《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一书中,蒋着重建立所谓“媒体价值观”概念,并对其详尽阐释、探究。它为我们观察“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创造出了一个新尺度,其衡量标尺上诸如“时尚性”、“感官性”、“暂时性”、“安全性”、“ 偶然性”、“拼贴性”、“盲目性”等刻度不仅清晰,而且确切。而在此之前,面对消费时代一波波此起彼伏的“诸多神话”
,我们要么束手无策,要么便常常在一场篮球赛热火朝天的当口一再吹响足球比赛时的罚规口哨。正如面对张艺谋引发大面积争议的影片《英雄》,尽管媒体批评、专业批评一个也不少但依旧显效不彰一样,“标准”的缺失与“标准”错乱必然导致批评的混沌与失据。以评价余秋雨系列畅销大著时所发生的情形为例,当论者以传统学术之尺衡量它时,不是太长就是太短;而当论者用传统文学之尺去衡量它时,则又必然生发局促或紧张——而正是在如此尴尬中,余乘隙成为赢家。余的聪明恰好是在一种错乱的尴尬中浮现而出。他在传统学术与传统文学的那个缝隙里为自己重新打造出了一个非此非彼的新空间。有关于此,我们认定为造物弄人的那件事,在余教授看来或许正是时势造英雄?我的意思是说,假使是在今天,其实余教授的成名史或大或小其实均可拆解与剖析……打比方说,在《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前,面对啥也没穿的那位皇帝,我们多半只是一帮混沌沉默的家伙,而现在,面对一丝不挂,我们已大致可能白话出一星半点有点意思的子丑寅卯。
第二部分 《不过如此》第22节 《白镜头》
解玺璋《白镜头》
同心出版社
还有很多晒伤我们看不见
对那种编辑、印刷、出版得比报纸还快的“新闻书”我一向出言谨慎。它们通常拣到篮里就是菜、快吃罗卜不洗泥。面对他们我赞美的最高形态仅只一个“快”字。谁都知道我在耍滑头——因为事实上“快”实在不是一个多么高级的标准……“SARS”病毒的传染不正以“快”著称?
不过,以“SARS”之灾为背景的《白镜头》一书超出了我的经验预期。在众多聚焦“非典”
主题读物中,这本100多面的画册精美而外,也传递着一种难于用语言表达的东西:有感动吗?有。
有伤心吗?有。有无奈吗?有。而如上解释或解读,其实终究拙劣。我甚至至此才再次理解所谓“读图时代”降临的万劫不复——简单说,图像信息与文字信息确已不可彼此取代。尤其图像信息,它很难转述、复述或阐释。正如那个著名的例证所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固然有可能被拍成拙劣的电视散文,可陈凯歌、张艺谋他们也很难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拍得尽如人意。
《白镜头》中全部照片均以“SARS”为主题。它们被分成记忆、状态、心情、民间、行为、爱情、时尚等十个部分。在那数百幅图片中,贯穿始终的细节是口罩——这也是该书名为“白镜头”的原因。而当口罩与记忆、状态、心情乃至贩夫走卒、时尚美人、北京土著或北漂老外紧紧贴合到一起后,一种怪异的“哲学风景”也便随之诞生:无论那只口罩十二层、二十四层、三十六层,它都如一条醒目警戒线,消弭亲密乃至过度亲密,催眠热爱乃至无限热爱,并直接破灭掉人与人、人与空间、人与动物、人与舟船车马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