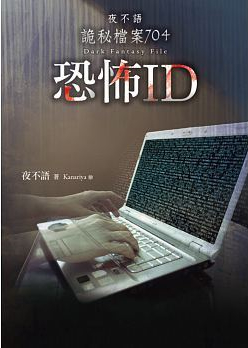2204-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户牖之下好?
在如此心理动因驱使下,我对书籍的饕餮心态,其实变态。可相对那个巨大恐惧而言,如此变态又大致健康?至少亚健康?
尚杰《解构的文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解码也许比编码更缓慢,更快乐
本书以不同的哲学家作为自己的阅读专题,依次收拢零散、琐屑阅读感想、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对于诸位哲学大师的解读体系,诚恳之至,坚实之至。
与众多蜻蜓点水式的评论和一目十行式的快速阅读相反,尚的阅读属“慢速阅读”。
尚自己解释说,慢速阅读其实拥有更多的快乐——“哲学之乐原来是就是‘破译之乐’,每种文本的密码不同,乐趣亦不尽相同,其风格、角度、方式是杂多的,从而快乐亦多多……
“在如此慢速阅读中,一个人的思想便不会轻易成为他者思想的跑马场。
尚说:“我不模仿作者,这是我的笔记,如此而已。
第四部分 《乔伊斯与娜拉》第40节 《弹指非典》
邵尔《弹指非典》
北京出版社
上帝不喜欢说吃就端
在众多“非典”主题书中本书属“时令菜”。过去,北京人幽默多在嘴上,现在,嘴上之外,又多了一个灵活的大拇指——短信——这本书中不全是短信,但以短信为主。这是一本编辑于非常时期、出版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书——它从非典期间大众喜闻乐见的数百条“短消息”选取素材,编辑、裁剪而成。这种大规模采集原本不过自产自销、自娱自乐主题单一短消息的文本样式,以前还不多见。如你所知,仅就语境而言论,那个非常时期事实上没有“非常快乐”可言。但正是在那个灾难降临的四月,幽默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饱满也更盛行。也许,再过很多年后,当人们再次翻阅这本时尚小书时,尚可清晰还原出一个让人感慨丛生的二○○三年四月。正如这本小册子的副标题所言,那些妙趣各异的短信确如一个又一个“幽默派”,可其实,组成那一组组“幽默派”的男女老少各色人等表情暧昧,情感酸甜苦辣,绝无类同——在那一只只蘑菇般肉乎乎的口罩后面,遮蔽着不同眼泪,不同惶恐,不同的焦虑、希望或不安……绝对复杂。
北京人一向以幽默善侃见长。很多比较京味文化的专家总会抓住这一点死也不放。不过,他们少有论及的,是如此幽默善侃,一定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的意思是说,正如那些处于高暴露、高压抑、高风险一线的医护人员的高抗压能力绝非二○○三年四月才临时抱修得一样,一个幽默的人或一个人的幽默感,亦非临时烧香便可奏效。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上帝,没人说得清。我能说的仅仅是,就算有,那么,上帝也多半不欣赏那种说吃就端的主。而说到幽默或幽默感,“sars”之后,我想很多人会赞赏马克·吐温的一个说法。他说:“幽默的真正来源不是喜悦而是悲伤。”
舍尔德勒韦尔《F的历史》
要承认,很多时候一个语词就能搞糟我们的生活
为一个单字出版一本书要胆识,也要眼光。《F字:所有粗鲁和不同用途的完整历史》一书对英国语言中最著名的、最全球化、最难登大雅之堂的粗言“Fuck”进行全面解剖。
舍尔德勒韦尔在书中考证称:“Fuck”一词早在十五世纪已出现,而众多委婉语亦尾随其后陆续出现。真正公开在书面提到这个单词的,是一八二八年美国一篇佚名日记。很多出色的文学作品对这个字眼并不避忌。在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乃至乔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等名著中,均使用到本词。
面对此词,相关司法机构的态度审慎而暧昧。一九六三年,芝加哥法庭审理某宗风化案,为免于提及“Fuck”一词,只好将它解释为“一个以‘F’开头、‘K’收尾,读音类似‘Truck’的字”。
《纽约时报》一九九八年报道克林顿与莱温斯基性丑闻时,只在引述斯塔尔报告时间接地提及本词:“莱温斯基说她希望总统两样东西,首先是忏悔:他需要承认他搞糟我的生活(Fuckupmylife)。”
作者舍尔德勒韦尔说,无论这个字用了多个世纪,“它仍然是英语中最粗鄙和侮辱的言词”
……这是作者的结论。
沈昌文《阁楼人语》
作家出版社
其实,可以不读书,也可以不读《读书》
本书其实更像是一部“旧”书,因为其中大部分文字早已成为尤其中年读者过往十余年阅读生活的一部分。据悉,在做《读书》杂志“主持人”期间,沈曾为读书杂志戏拟过一个推广口号,说“你可以不读书,但你不可以不读《读书》”……这口号的实际效用当然无从考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大多数读者其实根本读不完每期十余万字的杂志《读书》,而浏览“阁楼人语”,却从“不困难”,到“不遗漏”——不困难是说它短小,不遗漏是说它有趣——那个通常以拉家常、扯闲篇为语言风格的“人语”亲切平易不说,甚至连“抱怨”、“诉苦”、“哭穷”等等,也一概亲切自然。其实,更需要留意或破解的是“人语”中狡黠委曲的一面,而在当初,一期千把字的匀速乃至琐碎,遮蔽了一切。而今天,当它被连缀成一个二十万字文本、二十年时空的岁月绳索后,其中所记录下的一个时代的蜗行乃至一代知识者思想解放之轨迹,忽然令人心惊。似乎或确切地说,这应该不是预谋。
沈的文字独树一帜。而这个类似“操行评语”的现成语由于过于现成,因此需格外限制或规矩——他抱怨:不仅订数下降、纸张涨价、刊物拖期、错别字陡增自然都在抱怨之例,可令人诧异的是,甚至就连“整整二百个月份,月月在‘是’、‘非’中翻筋斗,讨生活。寻是生非,习非为是,以是为非,非中见是,今是昨非,彼是此非,是是非非,非非是是(P275)”也在沈的抱怨主题之下。而有了这后一个“抱怨”,一个思想评论类杂志主持人的尴尬与窘态、慧眼与鬼马也便被和盘托出;他表扬:不仅樊纲、盛斌、郭小平、赵一凡、申慧辉、吴岳添、周启超、刘承军、葛兆光、吴方、陈平原、夏晓虹、胡晓明、徐建融等一干思想才俊尽在其千字文中被隆重赞扬(P178),甚至就连远在澳大利亚的学者桑晔先生附函称用自己所得稿费为那些无力长年订阅读书杂志的读者订阅《读书》杂志,也会赢得沈之“悲欣交集”(P176)……所以,用诸如文化雅量或编辑襟怀之类,确难包容如是作为。我真正想知道其实是,在“沈昌文”“总经理”“主持人”“社会活动家”“饭局张罗者”等繁多身份间,其更本质的社会角色究竟何为?
如你所知,沈是一个爱热闹的人。每次见面,除去翻看他那个记满京城数百家特色菜馆电话号码的“PDA”外,就是聆听他口无遮拦恁多格言隽语——而那所有格言隽语,无不以牢骚怪话放浪自贬格式喷薄而出。沈最著名的一个口号被称之为“十六字令”,其中“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云云不仅广为圈内男女耳熟能详,而且颇合后来他自制标签所谓“不良老年”之定义。但其实,如此“玩笑”最需仔细揣摩认真打量——而当我将“情爱”云云置换为对学者耕耘的知会、将“情报”云云置换为对文化生态的预报、将“盗窃”云云置换为对学术资源的整合后,忽然发现,沈最恰切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思想经济人”。这个最初想起来大大不恭的“冒犯”竟被我自己越想越真切。笼罩其中,沈的恁多“抱怨”或“表扬”竟一一演变为一个思想经营者的“市场”策略:它貌似嬉皮笑脸,但内藏诚恳;它确乎玩世不恭,可其实行端坐正谨严不苟。该书出笼后,有关它的评论其实已是多多复多多,但提示沈之所为“雅痞风致”与“慧眼仁心”其实互为表里相互牵动者,尚不多。
如此这般,文首劈头盖脸《阁楼人语》其实更像“旧书”云云,其实已无冒昧之虞,而全为真切褒奖——因为毕竟说,在我们这个年出书超过十万种、日出书超过八百种的国度,“新”比“旧”其实是一个更冒险的评价。而且,尤其当我们将《阁楼人语》一书中的恁多闲言碎语唠唠叨叨换位为“当代学术思潮史索引”或“中国当代思想广告史”等视角去解读时,一个更大的“发现”也便轰然呈现:学者专家难道不需要广告?思想学术难道不需要推介?
而面对如此提问小心翼翼揣摩之余,也就发现,事实上能像沈那样与专家学者思想新锐吃川菜、品新茶、谈爱情,然后据此审时度势大力鼓噪之赞美之传播之弘扬之的人在全中国又有几个?所以我说,沈其实稀罕而外,也是无可替代。
截至二○○四年,沈已年届七旬。我个人感受是,这位德高望重的“不良老年”整日介风尘仆仆从饭局到饭局,不是在咖啡馆就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所为无非是传播新进提携才俊。他整个心肠乃至于《阁楼人语》中且坏且怪且酸且甜东拉西扯的平白文字都如空气般围绕着我们,它实在比我们想像的珍贵更有甚之——因为“空气”我们虽然感觉不到,可却无日可离。
第四部分 《乔伊斯与娜拉》第41节 《再见了,可鲁》
石黑谦吾《再见了,可鲁》
南海出版公司
喂,你好
畅销书《谁动了我的奶酪》所传播的,是所谓“应对变化”的简单理念——而推出并包装如此“理念”的符号,却是一帮有名有姓古怪精灵的小耗子;跟随其后,畅销书《你今天心情不好吗》推出的是一种心理按摩式的“自助桑拿”,它告诉你,凡事要想开,就算厄运当头,也别只会鼻涕一把泪一把——而承载如许平民哲学的,依旧是动物——从北极熊,到企鹅,从沙皮狗,到袋鼠;而二○○三年的畅销书则基本锁定两只小猪和一条导盲犬:麦兜,麦唛和可鲁……谁说赵忠祥的“动物世界”已淡出市场?其实,它不过悄然转身,应时转场:从电媒移师纸媒?
上述所谓,确有说笑。不过,不说笑的是,尤其近一二年,在大众读物市场,“动物”成为主角、成为载体、成为蔚然成风的流行话题、时尚风暴,确属事实。如此局面形成,原因又复杂,又简单。复杂的是,其实无论“奶酪”,还是“心情”,无论“麦兜”,还是“可鲁”,都因其各自的鲜明个性俘获知音;而简单的则是,它们同样选择了“动物”作为其叙述符号——并且,它们一概都不是、至少最开始并不打算写给幼儿园撒尿和泥黄口小儿们看。
于是,这些写给大人们看的大众读物风靡书市,其心理原因,并不完全因为吃麦当劳、看卡通片长大的一代成为阅读主流人群,同时还因为,无论是那种一个男人与数个女人的故事,还是那种酒后施暴、继父强奸、少年行凶、手机爆炸之类血淋淋的社会新闻故事,不仅不好玩、不可爱、不可靠、不干净,甚至,它直接就是一种类似于“恐怖主义”的精神垃圾。
如此颇堪玩味,用“麦兜”作者之一谢立文先生也曾言及——在“麦唛:宁静的声音”后记中,谢立文写:“幼儿园同学,我碰到一个幼儿园时的同学!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的幼儿园同学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临别时,胡子拉碴的脸上,我们都露了个幼儿的微笑”
……也许,面对令人失语、无语、胡子拉碴的现实,“一个幼儿的微笑”至少可能给我们一点勉强的安慰?
于是,动物世界里的鸡、鸭、狗、猪、小猫、小羊开始重新成为成人阅读中的主角,也就大致算一种历史必然:人心思和、人心向善、人心渴稳——尤其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格局中,它无疑异常脆弱,但同时,它也异常强烈。于是,在麦兜和可鲁们的肩膀上,不仅扛起了安全、和平、忠诚的旗子,也肩负着在一种极度脆弱、绝少信任感语境中的假想性幸福:当婚姻情感成为“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的伪善与冷漠,一头小猪便远比一个亲密爱人更能赠予我们温暖与爱意;而当“互不谅解、互相轻视、互存敌意,越走越远”(谢立文语)成为势力、残酷的陌生人社会的人际景况,麦兜和可鲁们的责任也自然不仅仅是开心、解闷那样简单,而成为一页可能随时翻开的“心理咨询”,一个可以随时拨打可供倾诉的电话……
斯宾塞·约翰逊《谁动了我的奶酪》
中信出版社
用一条白毛巾擦去镜子上的污迹,从容不迫
广告文案称,该书是一本“同时引起首席执行官和12岁少年兴趣的书”。如此说法的“国内版”则称,有人发现在公交车上,一些下岗大嫂也兴味盎然捧读该书……这后一个版本其实只是玩笑?当然,这玩笑匠心独运。
不过,如此“玩笑”倒正是该书深度畅销的一个脚注。一个只有92页、不少页码仅止两行提示、即便慢条斯理阅读也可在半个钟头阅读完毕的小册子风魔成这般模样,其中一定有某种道理……哪怕那道理其实不是道理——不是道理,常常也是道理呢。
说起来,“奶酪”其书居然难于归类——在Amazon网站,它被划入工商类,而在内地卓越网站,它被划在“励志人生”义项之下,在该书中文版版权页,它被标明为“个人修养、通俗读物”,而在旌旗网站,它又被划进“企业管理”类。甚至在当当书店网站,该书主页面显示称,凡购买这坨“奶酪”的用户,还会购买《孟子旁通》、《中国诗史》或《禅宗与道家》……
如此怪异的传播实况,意味颇多。它至少说明,“奶酪”在普遍的误读中延伸着自己的读者半径,并最终成为无法预测和控制的超级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