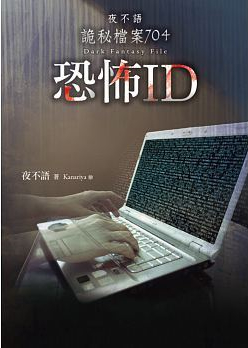2204-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此怪异的传播实况,意味颇多。它至少说明,“奶酪”在普遍的误读中延伸着自己的读者半径,并最终成为无法预测和控制的超级畅销书。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它必须经得起误读。在一个商业社会,“经得起误读”这种“无聊”,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品质。以“奶酪”而言,它可以被概括为“应付动荡与变化的良方”
,也可以被减约为“快速跳槽的直觉训练”;可以被解释为“人生励志的另类思维”,也可以被阐释为“工商管理的人性化视角”,它可以被附会为“中国加入WTO心理准备指南”,也可能被说成“安慰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软心理(正常人的心理困惑)现象的一叠快餐式配方”……如此这般,知识背景相距悬殊的各色读者纷纷捧读这块怪异“奶酪”,无非是各自切下完全不同的一块,并同时添加自我人生经验作料,以期调配出适合自己的酸、甜、苦、辣……它就像那些已被普遍改良的川菜一样——有人要5棵辣椒还嫌不爽,而有的人,一棵也不要。
于是,围绕该书,各种针锋相对的见解多如牛毛也就全在预计之中——与其它畅销书一样,“争议”从来是最好的助燃剂。连作者约翰逊自己都说,有不少读者“对这本书恨之入骨”。一个书虫在Amazon网站上说:该书“一文不值,胡说八道”,是一本“糊弄小孩的简单玩艺儿”。一位加州的读者更是直接断言说:“如果你想进一步证明我们这个社会已经不可救药了,这就是证据。”
中国记者王洪梅说:“我喜欢这本书,因为它是一个可爱的故事,轻松愉快地便澄明了混沌的生活。当一位被变化所困惑的人坐在一面肮脏的镜子前,希望看清自己的真面目而不得时,《谁动了我的奶酪?》就像一位智者,用一条白毛巾从容不迫地擦去镜子上的污迹,让困惑者真正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负责营销的董事达纳·威廉斯(DanaWilliams)说:“我把这本书给了12岁的女儿,她很快就读懂了。这本书不仅行文简单,而且寓意也很简单,简单有什么不好吗?人生主题其实刚好要这种简单——对超载的信息进行筛选,从中精选出少数几样真正重要的东西。”如此眼花缭乱让人明白,正如家居装修忽就盛行“极简”一样,对于日益不堪重负的现代人来说,“简单”正在成为一种十分凑效的商业原则——情感如此,生意如此,恋爱结婚跳槽下岗穿衣吃饭旅游泡吧等等,莫不如此。我们或许根本无须判断其是其非,因为它的“有效”已被“回款”证明。
斯蒂芬·金《凯丽》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最大恐惧在于他们是人,是同胞
作者遭遇车祸那年,传媒再次将他炒作为“新闻人物”。而斯蒂芬·金在美国,其实更像“长效新闻”——他的一举一动总会引发金迷关注。年过半百的斯蒂芬·金一九七四年写出成名作《凯丽》时年仅二十七岁。
至今作者已写出接近四十多部畅销小说。美国《福布斯》杂志说,金是全世界收入最丰厚的作家——自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七年,他的收入高达约8400万美元。在“金迷”人数尚嫌寒酸的国内,也已先后有了《凯丽》、《黑暗的另一半》、《死亡区域》、《神秘火焰》、《厄兆》、《危情十日》、《末日逼近》、《闪灵》、《撒冷镇》等十余部。
在关于斯蒂芬·金作品的介绍文字中常见诸如“一个黑漆漆的城镇、一片邪恶、沉重的安静、一声令人窒息的爆炸、一团尖利的、甜甜的、邪恶的笑声”之类的“商业文案”,可其实,斯蒂芬·金笔下真正令人恐怖的是人性的凶险——因为那种种凶残与卑劣,均非妖魔所为,其制造者是人,是和我们一样五官俱在的同类。
宋铁军《e童安安旅行篇》
21世纪出版社
后来,小蝌蚪发现妈妈改嫁了
作者原来当记者。其叙事方法尤其贴近现实。网络是这部童话传播的载体,也是其叙事主题。它不参照传统童话文本中诸如“小蝌蚪找妈妈”、“小花小草咪咪笑”之类的思维惯性,而用一种扁平的深度去谐调“童话文本”中“烟火气”与“信息过滤”等颇费捏拿的紧张与分寸感,在童真与世俗之间构建出一种平衡,让叙事自给自足,饱满圆润。
第四部分 《乔伊斯与娜拉》第42节 《疾病的隐喻》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上海译文出版社
隐喻是另一套逻辑严谨的恐怖故事
作者的文字由“冷隽的情绪”和“翔实的资料”这两种力量相互推动着往下走。前一种所谓情绪力量被桑塔格控制得相当节制;而后一种力量却以视野阔大取胜。此二者像拧麻绳一样将出自文学作品、社会思潮、医学认知、名家言论之中与疾病隐喻相关的繁多信息秩序井然地扭结在一起,制作出一中叙与议相互牵引也相互激荡的讨论式语感。以至于她的句子,尤其那种给出判断或结论的句子常常拥有一种谶语般的肃穆与绝望,如:“正如《魔山》中的一个人物解释的那样:‘疾病的症状不是别的,而是爱的力量变相的显现;所有疾病都只不过是变相的爱。’正如当初结核病被认为是源自太多的热情,折磨着那些不计后果、耽于情感的人,现在很多人相信,癌症是一种激情匮乏的病,折磨着那些性压抑的、克制的、无冲动的、无力发泄火气的人。这些看起来似乎彼此对立的诊断,实际上是同一种观点的大同小异的翻版(在我看来,它们同样为人们所深信不疑)。这是因为,对几的这两种心理上的描述全都强调活力的不足或障碍。”(P20)……在这段文字中,作者的结论因为资讯的密集性援引而获取了强大的力量。全书首篇“引子”部分即第一自然段亦如此:“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护照,但或早或迟,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P5)”……这段寥寥数语的开篇语旨在提示人类自古至今绵延不绝的对于疾病真相、疾病事实的“选择性遗忘”,但其形象生动已是可触可摸。由“王国”二字引发而出的全部结论亦尽为“隐喻”。当然,其所“隐”之意不在刻意制造晦涩,而在于让观念的呈现更丰满,更自由。
可见“资料”的力量在桑塔格的文字中变成一种真正的力量。阅读者常常不难领略桑塔格“思想”之锐,“观念”之魅,但却很容易忽略其“观”其“念”其“思”其“想”从资料、资讯之巨中渐次剥离与蜕变的过程。显然,这种忽视情有可缘。在本书中,仅“文学”这个作者的本行,其人物、细节之类信息的援引已近海量。而面对海量信息的剥离之功,也正显现出作者的过人之处。对桑塔格而言,萨特《恶心》中的罗昆廷、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加缪小《局外人》中的默尔索乃至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小爱娃等等,一一脱去原有的身份外衣而被还原为“病人”。桑塔格以一名“大夫”兼“批评家”的眼光打量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悯之外,更多冷峻。那冷峻之光甚至将整个文化史中密密麻麻车载斗量的“病案”一一过滤:那些通常会被我们忽略的细节、那些个性鲜明的作者自述、那些常常只被我们当作名人嘴边无非炫耀智力优越感的博喻、妙喻之类,统统在桑塔格的显微镜下被放大,被刷新。康德说:“对纯粹实践理性来说,激情无异于癌症,而且通常无药可医”
(P41)——康德的话原本不过是将“癌症”一词当作一种修辞手段,但桑塔格却从中听出了“癌症=情感过度”的隐喻之音;卡夫卡说:“我的头和肺在我不知晓的情况下达成了一个协定”(P38)——卡夫卡的话不过抱怨自己的身体背叛了自己,但在桑塔格看来,它却是在传播一种危险的判断,即所谓疾病其实是“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由此,疾病已大可约等于所谓“天罚”;雪莱安慰济慈说:“痨病是一种偏爱像你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P31)雪莱的话其实只是一种对于友人的抚慰之语,可在桑塔格的解析中,它被还原出了“刻意将疾病诗化”的底牌。而最终,这种种来自文化遗产中被遮蔽部位点点滴滴的渗透和遗忘被桑塔格双手合十,一一接住,并最终汇聚成一片以疾病为主题的隐喻之海……其间波涛汹涌险象环生。面对此海,我们忽然发现,疾病之于生命之危,至少不在人类自身锲而不舍将疾病性灵化、伤感化、妖魔化的危险之上。人类自己亦正亲自动手、一针一线继续编织、传递着与疾病本身基本无关的无数隐喻的“真理”。
问题被桑塔格锁定于“语文”——但无论如何,庞杂“语文”证例哪怕如山如海,终究也还只是冰山一角。或者,根本说,其实桑塔格仅仅是选择“语文”作为自己探究之旅的出发点:她尤其看重诸如“梅毒”、“癌症”这些从名词变成形容词的“比喻”:“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每个人的骨头里都有梅毒——我们全都被民主化了,被梅毒化了”(P54)……在波德莱尔的这段名言中,名词“梅毒”被当作形容词,用以形容反民主人士对“平等时代渎神行为”愤懑之情。桑塔格抓住这个普遍存在的“名词”“形容词”之变——在这个普遍存在的脱胎换骨中,桑塔格听见了那种将“性和政治的恐惧投射到这种疾病上”的危险习惯。因为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一书中,也一再提到“梅毒”。在如此语境中,“梅毒”或“癌症”等已成为一根属性迥异的猴皮筋,当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焦虑、恐惧投射到其中后,它又作为一种肮脏或羞辱反抽回疾病本身。
这样,在桑塔格眼中,大而言之所谓“语文”、小而言之所谓“语词”,在成为一座桥的同时,也成为一柄剑;在成为一列火车的同时,也成为一只鞭:它不断将对于疾病本身的恐惧和无助移植到更为广泛的现实生活情境之中,使之成为比喻或意义的弹跳点,同时,它也顺手幻化成皮鞭,将“疾病”之躯上上下下重新鞭挞出诸如羞辱、不洁、疯狂等精神性伤害——而那不过是一些莫须有的羞辱,来历含混的不洁和貌似清晰的疯狂。“没有隐喻,一个人就不能进行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些我们宁可避而不用或者试图废置的隐喻。这就像所有的思考当然都是阐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阐释’就一定不正确。”(P83)——在这段直言不讳、有关“隐喻”和“阐释”的告白中,“避而不用”与“试图废置”这样的话虽说得平心静气,但它既是一个细腻标准、精确态度,也是一个挑剔的主张:“我们关于癌症的看法,以及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P77)……在这里,“语文”或“语词”的“暴力”助手角色被清晰定义而出——它们当然不是“屠夫”、“杀手”或“刽子手”,而是一群一直以来被我们忽略不计的“刺客“。
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提及的疾病达数十种之多。肺痨,癌症,麻风病,艾滋病,小儿麻痹症,霍乱,梅毒,心脏病……假使如许可总括为“瘟疫”的疾病对患者本人来说已宛如伤口,那么,“隐喻”不仅是撒向那伤口的盐,还是一只将那伤口逐渐撕扯开来的手——这里的“撕开”相对于实际情形而言,是夸张,也是“隐喻”,即事实发生的情形并非如此。被文化承传滋养而成的有关疾病的庞杂“隐喻”谱系虽以“刺客”为本质,但它始终被遮蔽在无数几无破绽娇好自然面孔之下。它有俨然的正义之眼,匀称的道德腮红,虚幻的健康肌肤,乃至被上述种种整合而成的一种天赋权力之舌。而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的全部努力即在于“摆脱这些隐喻”(P161)在桑塔格条分缕析地揭露了“隐喻”的凶残之至,细究了“隐喻”的隐蔽之深,穷尽了“隐喻”的伪装之妙。而在此之前,关于隐喻,一无所知之外,我们深受其害。扼要地说,即在“隐喻”俨然面孔之后,其实掩藏着诸如“健康=德行”
、“洁净=德行”等无数隐蔽的公式。而天下患者却大都被隐喻撵进了那些看似堂皇公式的反面——在被冠以“高危群体”的标签后,他们的命运自动成为“疾病=堕落”公式的里最受欢迎的填充物:他们要么象征着普遍的放纵,要么呈现着道德的松懈乃至政治的衰败。它们汇同集体想象,为天下患者凭空捏造了一个新身份。这个新身份使天下患者“不仅有性命之虞,而且有失人格”(P113),不仅疾病本身成为一种“对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惩罚”(P101),而且疾病之外那个庞大隐喻谱系更像一整套“恐怖故事”(P103),在天下患者的心灵上插无数不流血的软刀。我甚至想鲁迅笔下的贺老六的媳妇祥林嫂。这个联想让人心惊。它让人明白,在我们这里,隐喻其实有着更为复杂的格式和更为悠远的传统。相比桑塔格所谓“穷尽之”的坚定而言,“揭露”或“批判”还远远谈不上。我们自己也还正与“刺客”共舞。
索甲仁波切《西藏生死之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用哲学轻抚亡灵
本书被西方评论家称之为展现了“西藏佛学智慧的精髓”。而另一个评论则称之为“当代最伟大的生死学巨著,一本最实用的临终关